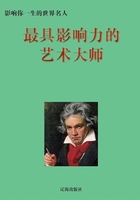《致橡树》?第一句落下的瞬间我能感到台下人的骚动,他在做什么?我一直低着的头抬起,灯光笼罩下,那个少年浅浅地笑着,侧着站着,就这样凝视着我,他一直看着我。原来,原来。
他从来都是站在这个位子上的。他从来不多说,只是默默地站在那,看着我笑,看着我胡闹,这本来,就是一种守候,而我从来就没有坚定过,因为惧怕,因为怕他最后发现他的海洋并不是我,他会离开我的,所以我先离开了。他这样看着我,仿佛我只要一伸手,就能触碰到。“爱,就在这里。”他改了诗句,落下最后一句,然后说,“所以,叶潞,我在这里。”
全场寂静无声。我看着他,就这样看着他,忘记了他结束后我还要唱歌,忘记了我是那样跟自己说不能再去干扰他的人生,忘记了我说一到夏天就忘记他。
似乎很久很久,他就这样微笑地看着我,一如半年前,他第一次在校门口被我堵住,只是嘴角含笑让同伴先走,然后扯着书包带饶有兴致地看着涨红了脸的我。
我伸出手去,等待那个人牵起,轻轻地笑出了声,眼泪却落了下来,舞台的灯光,我一直觉得太过刺眼,这次,却是温暖的,灼热了谁的眼眶。
以前我总是将喜欢挂在嘴边,曾经发牢骚他怎么只是笑。他说不多说,可能只是因为很喜欢很喜欢,所以不用挂在嘴边,就可以听得到。
“你怎么肯定我听得见,听不见我就离开你了呀。”“你听得到的,一定。”只记得他当时只是笑。
“我听见了,向林森。”迟到七个月的告白,幸好,我在这里,他也在这里,年华尚好。
向林森,你有没有听过《残酷月光》?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可我总是忘了后半句,“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
向林森,你见到你的海洋了吗?向林森,我忘了和你说,我流浪这么久,只是为了见到海洋。
——你就是我的海洋。
如你行云
吴蓉
何泽在很久以前会背着画夹骑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去寻找一棵生长笔直的树,她嚼一种很黏牙的橡皮糖,握牢铅笔画下一片片笔挺精致的阴影,未知的温度在眼神里孕育着某场爆发或者寂灭,然后她遇见了江城,在云影参差的江边。
那天沿海有台风登陆,于是何泽在很久以后都会错觉这是一场形容迫切的预言。
江城坐在江岸抽一种很呛人的烟草,肩头的夕阳光影欲燎原,侧脸深刻得像照着蜡烛的浮雕,明明是落拓而不可一世的男子,却让何泽仿佛仰望一棵树般艳羡而温柔。何泽把汽水放在男人面前,专注地看着男人略显冷漠的五官。
男人转过头看了眼何泽,似笑非笑,我不喝汽水,我喝酒,你有酒吗?何泽摇摇头。
那就等你拿了酒再来。你还在这儿吗?晚上六点后,差不多都在。你叫?
江城。何泽跨上单车沿岸慢慢往家骑,头顶的天空几净得仿佛一鉴方塘,大幅暖金色云层混淆了灰烬蔓延开来,让何泽想起层层叠叠的鱼鳞。鱼群游弋贯穿丰厚的云堆,最后翻翻白眼一齐在屋檐下倒挂。在何泽充斥着咸腥江风的记忆里面,渔区中数代人雷同的命运一样逃不了卑微挣扎的生存方式,在狭小破败的房子里蜷缩,在混乱的市场赚零散皱巴的纸币,每个人都习惯了浑身腥臭的生活,何泽也是。然而何泽也在习惯的过程中不能自抑地衍生出一种深深的厌恶。
何泽用大量香皂和花露水,她抬眼看向挂有整齐咸鱼干的屋檐,那里偶有大朵的云影投下。蒙有水汽的镜子里映出自己模糊雪白的胴体,她突然又想到了那个在江边抽烟的年轻男人,他有好看的手指和寂寞的眼,他喝酒不喝汽水,他似笑非笑的模样实在迷人得过分。
他就像一棵立于城市之外的树,背离烟尘人声,不规则地生发芽叶。如此安好。
何泽把二十几分的物理试卷草草塞进口袋,傍晚的光线穿透学校铁青色的空气,使得主干道上的人流通通变成慢镜头下的胶片,一格一格地滑过眼前。她去便利店买了两听啤酒,骑上单车直驱江岸。
江城不在。心里忽然失重掉落,隐隐遗憾起来。一个人坐在江边做好了等候的姿势,两听啤酒被任意搁在一旁。
何泽想起那个把自己的物理试卷揉成一团恨恨丢在脚下的班主任,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臃肿妇女,成天穿着自以为知性的套装A字裙招摇过市,打量何泽时会先用余光瞄她一眼然后轻蔑地把目光停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这让何泽毫不怀疑班主任其实压根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
她面带讥讽地说,我闭着眼睛蒙都不至于考这么混账的分数!何泽始终想不通蒙答案又何必要闭着眼睛,当她发现这位师太的逻辑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后就变得非常现实起来,她不卑不亢地从地上拾起险些被撕烂的卷子,重新折好后塞进口袋,快步走出办公室。
耳边响起易拉罐被拉开的声音,啤酒泡沫的香味立刻浸透周遭的风,一个瘦长身影挨着潋滟霞光在何泽身边坐了下来,何泽一惊,扭头看到江城脸上仍旧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现在小孩子简直不得了了,不好好读书成天瞎逛。
何泽抿嘴一笑,反正在学校待得大家都有脾气,成绩实在太烂了。江城说,不会吧?连书都念不好,你说你这人还有屁用!
何泽不服气地说,那你呢?不见得比我强多少吧?江城摆摆手,我跟你才不一样,我上高中那会儿哪科成绩不是好得操蛋,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我考九十九,就没人敢考一百。何泽瞪大了眼睛,物理也是?
废话!何泽语塞半晌,最终不相信地摇摇头,骗人!
江城笑笑,随你信不信吧。老实说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读书真是世上最他妈容易的事。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民工。江城指了指附近一座正在建造的花园小区,简洁地说,一百块钱一天。我想不通。你成绩这么好怎么没有上大学。
我没参加高考。哎?
江城仰头灌下一大口啤酒,目光镇静地穿过结了雾霭的江面,修长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敲击膝盖,那个时候我突然对自己按部就班的生活感到很困惑,我对自己的未来实在太清楚,这让我害怕,所以我逃掉了。这样你能理解吧。
何泽不说话。江城继续说,你知道,有些东西,一定要去某个特定的地方,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才能把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你知道吗?何泽摇摇头。
江城笑了笑,手中的易拉罐被抛出好远,最终直落江中。他使劲揉了揉何泽的头发说,谢谢你的啤酒,再见吧。何泽花了一整个晚自习画了江城的肖像,她仔细端详着这副落在铅灰色阴影背后的眉目,落拓而喧嚣的声息穿透纸背,并带着她所不熟知的伤痛。何泽至今仍会不时想起江城把易拉罐抛向江中的画面。
“啪!”
激起一朵不耐时年的水花。
江城的故事是何泽后来才晓得的,从小到大一直聪明乖巧,读父母为其挑选的兴趣班,应父母要求去考级,念父母期望的中学并一直稳居全年第一,并为父母所设定的大学目标而做着准备,就是这样的孩子,在中国铺天盖地的竞争攀比中发展出相当规模的特殊群体,承担着不属于自己的梦想,迎接着莫名其妙的挑战,建立出一套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价值观,然而在面对真正的自己时会感到无比脆弱而畏惧。江城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此锋利,危险到不容我们选择。
江城在高三这一年突然接到父母通知,说是两个人已经协议离婚,江城与母亲过。
母亲严肃地告诉江城,既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以后就要格外听话。十几年来一向温顺的江城第一次冷冷迎上母亲的眼神说,凭什么要求我听话?凭什么你们说什么做什么从来不需要与我商量考虑我的感受,而我所可以做的唯一的事就只是服从你们的决定你们的命令?是不是表面上我可以接受一切不合理的要求让你们错觉我很强大很甘心可以一直做你们眼里优秀到到处拿来做谈资的儿子?可要是我说你错了呢?要是你错了呢?
江城,你听我说……不用了。江城长长地舒了口气,静静地停了一会儿,然后说,因为已经晚了。江城是坐夜间火车奔来南方的,当初只是随便拣个中途站下车,在这里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做过酒吧驻唱,后来惹来混混被打得出血,也因此没了工作,之后又帮人家搬过家,粉刷房子,捡过垃圾,在地铁站卖唱,最惨四天未进一口食,何泽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建筑工地做了两个多月的小工。
其实你早就想逃了吧。何泽拿刀把苹果皮一圈一圈地削下来,头也不抬地说,父母离婚什么的都是借口,不然为什么吃了这么多苦你还不肯回去。
江城伸开两条长腿抽着烟,不置可否地笑笑。何泽把去了皮的苹果递给江城,长长的果皮被抛向江中,像是在自言自语,就骨子来说,谁不想呢?江城使劲揉了揉何泽的头发,说你一小破孩瞎想什么,断奶之前先给我安分点。江城总喜欢把何泽看成小孩子,何泽自然不肯,抗议说那江城为什么不肯安分,你都高三了为什么反而不安分了,你物理考那么下流的分数还不肯安分,我物理都这样了凭什么还要叫我安分?
江城叹了口气,伸开臂弯对何泽说你过来,何泽猫进江城的怀抱里,耳边风声远极,覆满灰烬的上空能看到几星微弱的火光明明灭灭,江城低低地说我还没告诉你我有多辛苦,可我没有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不甘心。
何泽在那个时候看到自己站成一棵树的姿态在很远的地方向一个有炊烟升起的房子招手告别,房子的屋檐下挂着一溜翻着白眼的鱼,散发出何泽自小便深恶痛绝的腥臭。她以为是江城身上那种落魄而自由的气息召唤着自己离开,撕烂永远也及格不了的物理试卷,背着空空如也的巨大双肩包义无反顾。
她呼吸着江城怀抱里呛人的烟草味,忽而伤感起来。江城?
嗯。路那么远,对吗?
江城只是收紧怀抱,算作回答。
母亲从厨房出来,何泽闷头喝着稀饭一声不吭,母亲却不咸不淡地开口道,你们班主任打电话过来了,昨晚没上自习,大半夜跑去哪儿了?
何泽顿了一顿,淡淡地说,考试考得不好,出去随便转转。母亲冷笑一声,你又不是头回考得不好,有什么好转的。你们班主任说了,这次物理考得比上次还过分,只有二十几分。何泽不说话。
考成这个样子了还不好好上学,我跟你爸辛辛苦苦卖鱼供你读书,就靠你将来让咱们家翻身,你不争气也就算了,现在还学逃课旷课鬼混过日子,你到底学不学好?
屋檐下的鱼翻着白眼一脸讥笑地瞪着何泽。何泽烦躁地把稀饭几口喝干,淡淡丢下句我上学去了就抓起书包站起身,却在看到母亲脸的一瞬间僵住了动作。母亲浑身发抖地坐在桌子边,大滴眼泪往外滚了又滚,嘴唇哆哆嗦嗦地张合: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何泽的手指因为攥得太紧而发白,屋檐外的天空晴得就像泼了一整片青色油彩,厚重得简直要滴落下来,为什么没有云?何泽又想起树一样的江城,伸展茂盛枝叶招摇过往云朵。她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倦怠,静静地注视了母亲一会儿,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
这种噬咬性的伤害因为日久年深而变得出奇钝重,磨耗着生命里晴空的颜色,任其剥落生锈。何泽印象里的十几年光景就像一朵压在山头烧得滚烫的云彩,迟缓地等候一场末日来袭般的分崩离析。
你是厌倦,还是害怕?江城这样问何泽。何泽抱紧膝盖摇摇头,江风里有烟草特殊的焦味,江面的颜色含混不清。江城好看的手指抓牢何泽的一边肩膀,何泽低着头,看不到对方的表情,但仍能想象到他树一般昂扬执着的模样。江城的声音很沉,他说何泽,我要换工地了,我想我要走了,虽然直到现在我也没办法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能我们需要的压根不是远离而是成长。何泽,有一天你长大了,我们还能认出彼此,我想要听你告诉我你是怎样长大的。何泽,何泽。
何泽看不清眼前这棵美丽的树的形象,她丢下江城拼命跑开,她想天果然是要黑了,带着难以逃避的灾难气息压城而至,她咬紧嘴唇不断奔跑,带着口袋里那张不及格的物理试卷。她望见远处遥遥升起的炊烟,终于认命般猛然停下脚步。
双手遮住脸,泪水滑落不暇。何泽想,我们怎样长大。怎样长大。
初告白
王宇昆
没有理会昨天晚上发来的七八条未读简讯。径直走向卫生间,镜子中的自己,面色暗黄,鼻翼两侧泛着油光,新长出了两粒粉刺,黑眼圈更重,头发也有些糟乱。可能是因为没有睡好的缘故吧,一觉醒来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从学会用轻巧的胸衣束住日渐圆润的身体开始,自认为平凡到无可救药的自己,根本不可能拥有那种心脏悬挂在喉咙间的窒息感。
暗淡平凡如自己由父母姓氏拼凑在一起的姓名。日记里曾根据无数部漫画剧和小说里夺目的男主角勾勒出一个自己憧憬的身影,有着樱木花道的执着坚韧和路飞的天真可爱。那个他被擅长素描的她重描了无数遍,略微飞扬跋扈的眉毛和尖锐的下巴更加明显。
从脑垂体下方无限喷涌出来的渴望,让她渐渐拥有了同异性问好时绯红的脸颊。静静生长在血液里的懵懂,好似一双深夜里警觉的猫眼。
新学期第一天,照例要分发接下来学段要使用的课本。个子经过暑期的突飞猛长后一下子超过了班里最高的男生,为了不挡住后面的同学被要求调换至最后一排。一个人搬至教室末尾那个很久无人问津而布满灰尘的桌子。
稍稍一用力桌子就会剧烈颤动。“喏!”女生被一本厚厚的习题册砸在桌子上的声音吓了一跳。男生粗鲁的行为让她在心底唏嘘了一声。桌脚垫纸也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自己蹲在地上调试高度,自然伏在地上的手指却突然又被用力地踩了一下。
——随之而来的尖叫引来了五十多双原本背对自己的目光。哎,连尖叫声都这么粗粝。“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忙着发书没有看到。”男生急忙停下手中的活向女生道歉,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湿巾,递了过去,“先擦擦手吧,剩下的交给我。”疼痛下竟然没有拒绝,接过男生的湿巾后从座位上走出来。
——比男生整整高了一个头。
因为自己的不礼貌在最后男生又道歉了几遍。可准备发完剩余的课本时,却发现刚才放在桌上的书不见了。
“真不好意思,恰好你没有,那干脆把我的先给你吧,等补领时再还给你。”男生重复了刚才递纸巾的动作,只是纸巾换成了自己崭新的课本。
双手恭敬地递过来,皮肤是小麦色,和路飞的皮肤颜色接近吻合,手臂修长,和樱木花道的手形状相近,血管突起分布着像一条蜿蜒的蚯蚓。
简直天衣无缝地再现了日记本中的那双正在投掷橄榄球的手。晚睡前的女生又一次端详了一遍男生的课本。
都说十六七岁少女的心事像蜜一样稠浓,仅仅一个善意的微笑、优雅的道歉都会被扩大无数倍,这种满足感在体内无限地发酵,却又有不能见光的晦涩。接过男生的湿巾时暂时忽略的心跳,过去后再次想起,虽已是淡淡的痕迹,也可以被女生用温和的心思打磨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