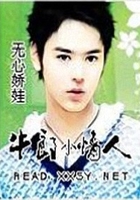她突然转过身去,一直向前走,不知因何,千辛万苦找来了,见到他了又不想过去了。
有时候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复杂。
走着走着,忽然一个浪头打来,打湿了头发。突如其来的凉意,从头顶透至足底,整个人似僵住了。
欧阳紧跟在后面,拉住她的手说:“已经见到了,那就过去打个招呼吧。”他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可是分不清是什么滋味。
她其实很想,可是决定了要过去,回头望去,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回到旅馆,在大堂又撞见夏微寒,原来两人都下塌在“两个世界”。
他的帽沿戴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整张脸。陈宽、李奔随他左右,他们都站在那拥有百年历史的L字型铁栅栏老式电梯外,客客气气地谦让对方。
小若说:“你们人多,你们先进去吧。”
欧阳点头附合道:“夏总先请。”
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一直不吭声,只把帽子遮住脸,仿佛做了有辱面子的事那样,羞于见人。
陈宽将轮椅推了进去,电梯上升,夏微寒一直没有把帽子拿开。
随后小若乘上电梯到达房间,巧得很,两人又住在隔壁。
不知是否游客增多的原因,旅馆爆满,她和欧阳共处一室,不大的空间分隔出双区域,小若睡床,欧阳睡地。
睡到半夜,她突然听到那边“咚咚咚”响,像是谁的拳头击在硬物上。来不及多想,和衣而睡的她跳下床直奔过去,隔着门板,那是夏微寒的声音,压抑的沉重的叫嚣的。
千遍万律只重复一个字:“滚!”
里边陈宽和李奔似在揪住他胳膊,制住他不许乱动,陈宽正在劝慰:“疼一阵子就好了,夏总你忍着点,忍着点。”
她从陈宽那里知道,夏微寒去攀美国西部的高山寻草药,被蛇咬到了,伤到了腿。当时流的血褐红,疼得走不了路……
门动了一下,慢慢向后退开。
小若这才回过神来,急忙要走,李奔叫了声:“杜小姐。”
尔后是夏微寒讥诮的嗓音:“我是老虎吗?”带了点沙哑。
她脚步停了下,一言不发,匆匆回房锁门。欧阳已经醒来,趴在地上问:“他怎么了?叫得整幢旅馆都差点听见了。”
“疼死他。”小若悻悻地说,被子一蒙睡觉去。
次晨上楼顶天台取晾干的衣服,见到夏微寒的轮椅单独在那里,手里拿着K金雪茄剪,剪开一根褐红的COHIBA雪茄烟头。
桌子那头放着火柴,他伸手去够,不巧风吹来小若手中的衣服一拂,那火柴盒结结实实掉到地上去了。
他的手就那样伸着,保持着手中空无一物的姿势,那样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