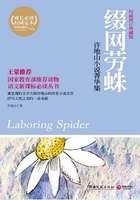水沏淡淡一笑道:“今儿天色已晚,来人,将证物送至宗正寺库房,紫英,你带人守住贾府,不许人进出,不许相互串供,明早本王请了圣意传齐人证再审不迟。”
冯紫英高声称是,哄猪赶羊一般的将贾府之人赶回各自的房间里去,贾母这一生虽然经事很多,可也从没遇到抄家的情形,已经吓得浑身哆嗦上气不接下气,鸳鸯琥珀两个丫头扶着她,好不容易才将她扶回房去,贾母倒在床上双眼瞪圆了直喘气,看着好不吓人。
鸳鸯上前服侍了一回,贾母好不容易才顺过气来,两行老泪落下,贾母哭道:“国公爷呀,妾身对不起您……”
鸳鸯忙又劝了一回,贾母忽然想起宝玉,忙拉着鸳鸯问道:“鸳鸯,刚才怎么没看见宝玉?”
鸳鸯已经知道宝玉被送到浣衣局服苦役了,可是她不敢再刺激贾母,便谎称宝玉一早出了门,许是有什么事绊住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贾母听了这话,长长出口气道:“但愿宝玉机灵些,今晚不要回来,他若是能去找他舅舅,许能平安无事。将来还指着他重振贾家……”
贾母念叨了一阵,便躺倒在床上,无力的摆手道:“鸳鸯,你到外间去吧,我要歇一歇。”
鸳鸯给贾母盖好被子退了出去,贾母忽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她喃喃道:“看来贾家在劫难逃,不得不用那支力量了,唉,早知有此日,断不该叫他逃去狄族,若他在,还有个传信的人。罢了,国公爷,贾家危急,妾身只能起用那个人了。”贾母轻轻起身下床,到妆台前取了一点胭脂,在一条雪白丝帛上写下好多异族文字,写好之后将这丝帛卷起来掖到一只错金九转镂空雕花小香薰的夹层中,又向床头暗格里找出指甲盖大小的香块放到小香薰中,一股淡淡的奇异香气便缓缓弥漫开去。这香只燃了半个时辰,一条细小的黑影便从窗外射进来,直冲到贾母面前。那是一条通体幽黑手指粗细三角头绿眼睛的小蛇,它吐着信子围着小香薰转了几圈,然后将蛇尾勾起小香薰的镂空之处,又嗖的一下冲破窗纸,不知往何方而去。这小蛇来去无声,贾母将消息送了出去,整个贾府还无一人知道。
太子查抄贾府,用的是外松内紧之策,不论朝堂重臣还是京城百姓,都无人知道气派轩敞的贾府已经将内驻精兵,贾府之人已经没了自由。
凤姐回到自己的房中,不停的暗自祷告道:“二爷,今晚千万要在二叔家留宿,一定不要回来……”贾琏去王府与王子腾商量做生意的事情,王子腾留他吃酒,见贾琏有了酒意,便留贾琏住下,因此让贾琏暂逃一劫。平儿走到凤姐身边,拍着胸口轻声道:“多亏奶奶有先见之明,放出去的银子都收回来了,太太让放的也把印子纸交还给她,否则真牵连起来,这一家子都有罪。”
凤姐轻叹道:“这都是当日林妹妹提醒我的,若没有她,我现在还给太太当枪使。亏得我们收手的早,否则被关到刑部大牢的便不是周瑞家的,而是我。这半年来我已经将咱们这一房摘干净了,便是查起来也不怕,最多是被牵连抄没财产,那也没什么,平儿你别怕,日后我们虽不能再过这样富贵的日子,可是衣食无忧却是没有问题的。”平儿忙道:“奶奶您快别这么说,便是吃糠咽菜,平儿也跟着奶奶。”
李纨在自己的屋子里搂着幼小的贾兰,眼泪不住的往下掉,她出身诗书大家,最看重的便是清白名声,白日里这样闹了一场,李纨只觉得差愧欲死,将王夫人恨到了骨子里去。哭了一场,李纨起身打开妆盒,将逢年过节王夫人赏的不多的几件首饰取了出来用帕子包好,打算明天一早便交出去,也好保住自己的清白。包好之后李纨又想了想,忙去找出压在箱子底的几张银票,拆了自己和贾兰的一身小衣,将银票缝到夹层中去,缝好之后给贾兰换上小衣,李纨低声道:“兰儿一定要记住,这衣裳万万不可脱下来。”贾兰虽不懂这是为何,却也明白出大事了,只扑到李纨怀中,母子两个又是一场抱头痛哭。
贾赦房里更是忙乱,贾赦气一阵骂一阵打一阵子,刑夫人吓得远远躲到门边上,一步都不敢上前,贾赦骂累了才喝道:“蠢妇,还不滚过来。”
刑夫人小心翼翼的挪到贾赦跟前,贾赦低喝道:“快不快把银票找出来,看样子明儿要大抄家,能藏一分是一分。”
刑夫人委屈的低泣道:“可是家里也没有多少银子,老爷您新买了四个丫头,如今怕是连一万两银票也没有的。”
贾赦气得狠狠抽了刑夫人一耳光,喝道:“胡说,你当我不知道你有私房银子,还不快拿出来。”
刑夫人一头撞到贾赦怀中,大哭道:“我哪里有私房银子,家里家外都是老爷做主,我一个月总共二十两银子的月钱,除了个这什么都没有,您让我拿什么出来……”
贾赦慌忙堵住刑夫人的罪,低声骂道:“你做死呀,还敢大声囔囔……”见刑夫人不再哭喊,贾赦将她甩到一旁,自去翻刑夫人的妆奁。将个妆盒翻的底朝天,也没找出什么银票来,那些头面首饰虽然值不少银子,可是贾赦也没法子将那些首饰立地变成银票,只能恨恨的跺着脚,进内室找小妾泄火去了。
等贾赦走去,刑夫人轻手轻脚的走到妆台前,将一枚极不起眼的骨簪捡了出来,藏到里衣的暗袋之中。贾赦走了眼,不知道这种骨簪是中空的,里面放上两张银票毫无问题。刑夫人自嫁与贾赦做填房,便时时居安思危,偷偷存了不少钱,到如今已有万余两,刑夫人悄悄将银子存在钱庄里,兑付的银票便藏在她的骨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