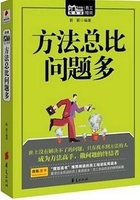在我3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决定终生以写小说为职业,想做个弗兰克·瑞斯洛、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充满了信心,在欧洲住了两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用美元在欧洲生活,开销算是很小的。我在那儿过了两年,从事我的创作。我把那本书题名为《大风雪》,这个题目取得真好,因为所有出版家对它的态度都冷得像呼啸而刮的大风雪一样。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不值一文,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和才能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我茫然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哪怕他用棒子当头敲我,也不会让我更感到吃惊,我简直是呆住了。我发现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必须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转呢?几个礼拜之后,我才从这种茫然中醒来。在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过“给你的忧虑订下‘到此为止’的限制”的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我把费尽心血写那本小说的那两年时间看作是一次可贵的经验,然后从那里继续前进。我回到组织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空的时候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籍。
我是不是很高兴自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呢?现在每逢我想起那件事情,就得意地想在街上跳舞,我可以很诚实地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哪一天或哪一个钟点后悔我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沿着沃登湖畔的树林里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自己做的墨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称之为生活的总值,需要当场或长时期内进行交换。”
换个方式来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付出代价,而付出得太多了的话,我们就是傻子。这也正是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悲哀: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快乐的歌词和歌谱,可是完全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快乐。他们写过很多令世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脾气。他们为了一张地毯的价钱而争吵多年。苏利文为他们的剧院买了一张新的地毯,当吉尔伯特看到账单的时候,大为恼火。这件事甚至闹至公堂,从此两个人至死都没有再交谈过。苏利文替新歌剧写完曲子之后,就把它寄给吉尔伯特,而吉尔伯特填上歌词之后,再把它们寄回给苏利文。有一次,他们一定要一起到台上谢幕,于是他们站在台的两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可以不必看见对方。他们就不懂得应该在彼此的不快里订下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做到了这一点。
有一次,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觉比我要多,也许我这种感觉太少了吧;可是我向来以为这样很不值得。一个人实在没有时间把他的半辈子都花在争吵上,要是那个人不再攻击我,我就再也不会记他的仇。”
我真希望我的老姑妈——爱迪丝姑妈也有林肯这样的宽恕精神。她和弗兰克姑父住在一栋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土质很差,灌溉不良,收成又不好。他们的日子很难过,每时每刻都得省吃俭用。可是爱迪丝姑妈却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其他的小东西来装饰家里。她向密苏里州马利维里的一家小杂货铺赊账买这些东西。弗兰克姑父很担心他们的债务,他很注重个人的信誉,不愿意欠债。所以他偷偷地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要再赊账给姑妈。当她听说这件事之后,大发脾气——那时到现在差不多有50年了,她还在大发脾气。我曾经听她说这件事情——不止一次,而是好多好多次。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70多快80岁了。我对她说:“爱迪丝姑妈,弗兰克姑父这样羞辱你是不对的,可是难道你真的不觉得,从那件事发生之后,你差不多埋怨了半个世纪,比他所做的事情还要坏得多吗?”
爱迪丝姑妈对她这些不快的记忆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贵了,她付出的是她自己半生的内心平静。
富兰克林小的时候,犯了一次他70年来一直没有忘记的错误。当他7岁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支哨子,于是他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他所有的零钱放在柜台上,也不问问价钱就把那支哨子买了下来。“然后我回到家里,”70年后他写信告诉他朋友说,“吹着哨子在整个屋子里转着,对我买的这支哨子非常得意。”可是等到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付了钱之后,大家都来取笑他。而他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懊恼地痛哭了一场。”
很多年之后,富兰克林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做了美国驻法国的大使。他还记得因为他买哨子多付了钱,使他得到的痛苦多过了哨子所给他的快乐。
富兰克林在这个教训里所学到的道理非常简单。“当我长大以后,”他说,“我见识到许多人类的行为,我认为我碰到很多人买哨子都付了太多的钱。简而言之,我相信,人类的苦难部分产生于他们对事物的价值做了错误的估计,也就是他们买哨子多付了钱。”
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对他们的哨子多付了钱,我的爱迪丝姑妈也一样,我个人也一样——在很多情况下。还有不朽的托尔斯泰,也就是两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可能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人物”。在他逝世前的那20年,崇拜他的人不断到他家里去,希望能见他一面,听到他的声音,甚至于只摸一摸他衣服的一角。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就像那是一句“圣谕”一样。可是在生活上,托尔斯泰在70岁的时候,还不及富兰克林在7岁的时候聪明,他简直一点脑筋也没有。我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托尔斯泰娶了一个他非常爱的女子。事实上,他们在一起非常快乐,他们常常跪下来,向上帝祈祷,让他们继续过这种神仙眷侣的生活。可是托尔斯泰所娶的那个女子天性善妒,她常扮成乡下姑娘,去打探他的行动,甚至于溜到森林里去看他。他们发生了很多很可怕的争吵,她甚至嫉妒她亲生的儿女,曾经抓起一把枪来,把她女儿的照片打了一个洞。她会在地板上打滚,拿着一瓶鸦片对着嘴巴,威胁着说要自杀,害得她的孩子们缩在屋子的角落里,吓得尖声大叫。
结果托尔斯泰怎么做呢?如果他跳起来,把家具打得稀烂,我倒不怪他——因为他有理由这样生气。可是他做的事比这个要坏多了,他记了一本私人日记!在那里面,他把一切都怪在太太身上,这个就是他的“哨子”。他下定决心要下一代能够原谅他,而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他太太身上。而他太太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这种作法呢?这还用问,她当然是把他的日记撕下来烧掉了。她自己也写了一本日记,在日记里把错都推在托尔斯泰身上。她甚至还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叫做《谁的错》。在那本小说里,她把她的丈夫描写成一个破坏家庭的人,而她自己是一个烈士。
所有的事情结果如何呢?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把他们惟一的家变成托尔斯泰称谓的“一座疯人院”呢?很显然,有几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极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不错,他们所最担心的就是别人的意见。我们会不会在乎应该怪谁呢?不会的,我们只会注意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会浪费一分钟去想托尔斯泰家里的事。这两个无聊的人为他们的“哨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50年的光阴都住在一个可怕的地狱里,只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一个有脑筋会说“不要再吵了”,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足够的价值判断力,并能够说:“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马上告一段落,我们是在浪费生命,让我们现在就说‘够了’吧。”
不错,我非常相信,这是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秘密之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我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定出一种个人的标准来——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起来,什么样的事情才值得的标准,我们的忧虑有50%可以立刻消除。
所以,要在忧虑摧毁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任何时候,我们想拿出钱来买的东西和生活比较起来不合算的话,让我们先停下来,问问自己下面的三个问题:
1我现在正在担心的问题,到底和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
2在这件令我忧虑的事情上,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设定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然后把它整个忘掉?
3我到底应该付这支“哨子”多少钱?我是否已经付出了超过它价值的钱呢?
适应不可避免的事实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密苏里州西北部的一间荒废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当我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上戴着一个戒指。当我跳下去的时候,那个戒指钩住了一根钉子,把我整根手指拉脱了下来。
我尖声地叫着,吓坏了,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为这个烦恼过。再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现在,我几乎根本就不会去想,我的左手只有四个手指头。
几年前,我碰到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里开货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齐腕砍断了。我问他少了那只手会不会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要穿针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件事情来。”
令人惊讶的是,在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下,我们差不多都能很快接受任何一种情形,以使自己适应,或者整个忘了它。
我常常想起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座15世纪的老教堂,它的废墟上留有一行字:
事情既然如此,就不会另有他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你我一定会碰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况,它们既是这样,就不可能是他样。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或者我们可以用忧虑来毁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可能会弄得精神崩溃。
下面是我最喜欢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提出的忠告:要乐于接受必然发生的情况,接受所发生的事实,是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丽萨白·康奈利,却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一点。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我接到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又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生命对我多么美好,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努力带大了这个侄儿。在我看来,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有很好的收获……然后却收到了这些电报,我的整个世界都粉碎了,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活下去。我开始忽视自己的工作,忽视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淡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疼爱的侄儿会离我而去?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生活——就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痛欲绝,决定放弃工作,离开我的家乡,把自己藏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封我已经忘了的信——一封从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那里寄来的信。是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来给我的一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不过我知道你会撑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就能让你撑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你教我的美丽的真理:不论活在哪里,不论我们分离得有多么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承受所发生的一切。”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向我说话。他好像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撑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藏在微笑底下,继续过下去。”
于是,我重新回去开始工作。我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对我自己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给别人的儿子们。晚上,我参加成人教育班——要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我不再为已经永远过去的那些事悲伤,我现在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奈利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要学到的东西,那就是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这不是很容易学会的一课。就连那些在位的皇帝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这样去做。已故的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的墙壁上挂着下面的这几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错事后悔。
同样的这个想法,叔本华是这样说的:能够顺从,这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我们对周遭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
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战胜它们。我们也许以为自己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肯于加以利用,就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这样说:“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种不幸偏偏降临了,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低头看地上的地毯,发觉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证实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金顿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灾难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运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时时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完全失明以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哪怕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无论我们是否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