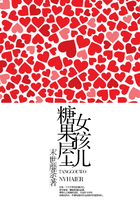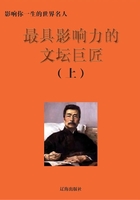弟兄仨,父亲又是个农民,想想也很可怕的。宋海涛中考成绩在他们乡名列第二,顺利的考上这所荛山市高中。据宋海涛说,如果他那年考不上,父亲一定不会让他复读。“家里供不起。”
他们仨人之所以要好,大概也因为他们同属班里的“第三世界”。他们这个班,家庭情况好的大有人在。父亲是小老板的就有好几个。他们吃喝穿戴,都讲究名牌,出手都很阔气。好几个都带有手机、小灵通。他们仨个不行,偶尔聚聚餐也是在街上小摊,吃碗炒肉面。奢侈一下,也就是要瓶啤酒,买盘小葱拌豆腐,花生豆什么的,而且还搞AA制,穷酸得可怜。
裴小军的爸爸,据说发了点小财,但他那边又有了孩子,那个后妈又抠门得厉害。裴小军从未在父亲那边吃过一顿饭。爸爸对他也似乎很冷淡,给零花钱也不过二三十块,到是经常没来由的呵斥他两句。
裴小军想休息一会,手都快冻肿了,关窗跳下来,刚跳在地上,正巧,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起身去接电话。还是朱刚,朱刚说:“他打不通施芸家的电话,没人接。”因为明天没办法打电话,拜托裴小军明日向施芸祝贺新年。
裴小军又气又笑,就说:“打不通就打不通吧。初六就开学了,开学你再向她祝贺呀!”朱刚在那边很认真地说:“那时祝贺就晚了。”裴小军就笑了,心里想,朱刚这人还真不赖,挺守信用,难怪。班里施芸对他“一往情深,”上课看他脑袋,下课还要不远万里去找他聊天。
“我也祝你节日快乐。”裴小军对电话里的朱刚说,朱刚在那边苦笑了笑。“快乐不快乐,无所谓。”然后,就挂了电话。
朱刚确实没心思春节的快乐。小时候过年,最大的快乐是放鞭炮,这大概是每个男孩子的快乐。然而,这个快乐,18周岁的朱刚已没了兴致。相反,还开始讨厌这此起彼伏,没完没了的炮声。穿新衣服也是过去的一大乐事。现在的他也无所谓了,那他还有什么快乐呢。或许与初中那些已失学的同学聚会,能让他郁闷压抑的心情变得放松,但父亲却严禁他与昔日的同学接触。父亲的态度很明确。“跟他们在一起能学到什么好,那些人都混成了痞子。”
初中的同学,只有他们可怜的几个人考上高中。其他的大都开始打工。有人到工厂做工,有人在火车站装卸,还有的下井挖煤。当然,也有个别人应征入伍。这些人只在社会上混迹了两三年,就变得异常成熟和老道。几乎每个人都留了长发,每个人都学会了抽烟喝酒。一开口就是满嘴脏话粗话,连最亲近的人都是先骂一声:“你妈的。”
朱刚不顾父亲的反对,悄悄约了两个同学。尽管他们在小饭馆设宴款待他,逼着他喝掉两杯白酒,他还是在他们身上,难以挽回昔日他们之间纯洁美好的友谊。
他们不愿意回忆过去,谈论的都是当今社会上黑道方面的事情。当然,他们也羡慕他,说他是未来的大学生,前途无量。但朱刚还是满肚子的忧伤。为他们往昔的纯情,为今日这些朋友的坠落,还有自己即将面临的难以预料的求学。也许,半年之后的他,也会变成他们的这个样子,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找地方打工。然后,浑浑噩噩地用喝酒来麻醉,来找乐。他们似乎也看到了自己黯淡的未来,没有正当固定的职业,找一个和自己命运差不多的女孩子,去过父辈那种平淡无趣的生活。
朱刚期望从他们这儿获得一点快乐。结果,快乐没有找到。反而,让他更加感到沉郁。是的,他在初中时候,如果没有努力,势必就成了他们其中的一员。这天晚上,他的确喝多了,在学校时,他和裴小军等人喝过啤酒,但那只不过出于好奇,出于寻找乐子,浅尝而已。今天,确实被老同学们灌醉了。
他的醉态太明显了,跌跌撞撞,不是老同学送他,他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头脑完全失控。父亲正巧下班刚回到家,一看他跌东晃西的样子,当时就火冒三丈。不仅不去扶他,反而,大手一推,将他推倒在地,然后他感觉到父亲的鞋在他臀部重重踢了一下。
父亲破口大骂,训斥他的荒唐,他的堕落。朱刚的那两个同学早已吓跑。朱刚被母亲拖上床去,头脑已略微清醒。他等待父亲痛彻肺腑地斥责。父亲本是个话不多的男人,今天却象决了堤坝的洪水,滔滔不绝,唾沫四溅。从朱刚七八岁的顽皮,一直骂到他今日的酗酒。最后,父亲决绝地说:“今年考不上,你就给我下煤窑去。我没那么多钱供你。”
家里确实出现了经济危机。朱刚的奶奶去年患病住院,花去七八千元,最后还是不治。今年爷爷又中风病倒在炕。煤矿又濒临破产,每月仅支付百分之六十的工资。父亲辛苦一个月,仅能挣到八百多元。母亲没有工作,早先在矿上的小公司干临时工,后来也因不景气被裁了。大姐残疾,一直在家。二姐在矿上卫生队做工,一月工资仅二百元。而他朱刚在荛山高中上学,一年就需三千多元。
父亲对他的训斥不是没有道理。他大概太让父亲失望了。那年父亲去学校开家长会,为了省6块钱乘车费,年近五十的他硬是骑车八十里赶到学校。他在学校门口等父亲来,父亲一下自行车就摔到在地上。他刚下了一天井哪。朱刚当时心里酸涩的几乎要流泪。那天父亲给他带了五个苹果。他吃不下,硬是让父亲又带了回去给病中的奶奶。
父亲苍老得厉害,他早已谢顶,那天又在烈日下骑了三个小时的车,赶到学校时面容十分憔悴,又很黝黑。一个同学悄悄地问他,朱刚,来开会的是你爷爷吧。他立刻就火冒三丈。第一次开口骂人:“滚你妈的,是你爷爷。”
自己确实对不起父亲。父亲早就威胁过他,不好好学习你就去下井。到井下受几天,你就知道该不该好好学习了。其实,即使他不下井去,他也知道井下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从小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煤矿上的孩子怎么不知道下井是受什么苦?仅在井口看看出井人那张面孔,那身如同乞丐般的衣服,就知道,煤窑底下是怎样一种生活。
井下还经常死人,每年学校都会增加几个工亡子弟。朱刚上初二时,一天就有四个同学失去了父亲。出于好奇,朱刚去矿上太平房看过那种凄惨的遗体告别场面,一个同学的父亲的脸被冒顶摔下来的石头砸扁了,那张没有修复的面孔真是惨不忍睹。
父亲从小就对他哼哼教导:“千万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要下煤窑。”那是父亲发自心底的愿望。然而,今天,父亲却决绝的说:“考不上大学就马上回来下井。”父亲太伤心了。
直到第二天,父亲也没给他好脸色。为了他学习,父亲不让他干一点家务活。他回家的第二天,过年的柴禾不多,主动去劈柴,父亲出井刚回家,就从他手上夺过斧头:“看你的书去吧!”家里的一切活计都不让他做。母亲有时在厨房喊他帮一把手,父亲都呵斥母亲,“你们自己不会干,叫小刚做啥!”
父亲深爱着他,父亲对他一直抱着殷切的期望,他不是个感觉迟钝的男孩。他不怪父亲,可是父亲却并不真的懂他。除了学习,他应该有别的快乐。而且,他也有自己的苦恼,他也想有个宣泄的渠道。
放假这几天,他确实想休息休息。在学校,他几乎整天都昏头昏脑。他知道自己智商并不高,之所以还能混迹在班内前十五名,是因为自己比其他同学付出了更多的辛苦。自己心里那根弦绷得太紧了。他害怕那一天,这根弦就会绷裂。他平时常有些幻觉,正做着题,眼前古怪地出现海市蜃楼的东西,要么就是一片黑云,迷雾。
他想休息,可是父亲却不准他休息,似乎只想看到他在书桌上刻苦的拼搏。今天,他是偷跑出来的,父亲下井去了,临去时,对他下了不准出门的禁令,并且让大姐看着他。但他还是跑出来了,他答应给几个同学拜年。他是个个性特殊的男孩,他不想让他的同学讥讽他“小气。”舍不得掏电话费。他是他们班为数不多的家里没电话的学生,这已经让他自卑,他不想在同学中间太掉份。他准备用母亲给他的二十元钱全给同学打了电话。
大年初一,邮局放假。他没法打长途,只能在今天打。但是,很不巧,许多同学不在家。特别是施芸没在家。他最想打给的也就是“四人帮”的成员。从心里说,他最想念他们,虽然放假仅过了三天。他尤其想念施芸,他和她同桌一年。他觉得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当然,他知道自己不配。施芸家境非常优越,父亲是市财政局副局长,母亲是医院内科主任。他是什么呀,他什么都不是,一个癞蛤蟆。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她的想念。
想念,仅仅是想念。他不配爱她。他也不敢谈恋爱。没能跟她通话,太遗憾了。让裴小军转达他对她的祝福吧!
下雪了,阴霾的天空,零零星星的飘起了银色的雪花,朱刚仰望天空大喊了一声,连自己也被吓了一大跳。下雪太好了。他想,至少可以净化一下这龌龊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