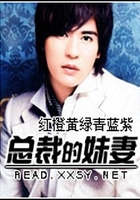第二天一大早,老太爷就把二老爷叫到书房,先是训斥一番,说他堕了读书人的脸面,污了姚家的门风,最后说要将二房分出去。姚老太爷本来耳背,加上心情愤慨,二老爷只觉得一个个响雷炸在耳朵里。更糟的是,透过窗户大开的书房,几乎半个姚府都听到了老太爷对二老爷的咆哮。
有了聪明绝顶的三老爷的衬托,二老爷自小就是挨着骂长大的,被骂上几句不痛不痒,他也只当尽孝,但若是要将他分出去,却是万万不妥的。不过二三年他赚个盆满钵满,出去走商顺风顺水,靠的不过是姚府的名头,若是被分出了,还有谁上杆子跟他个白身做生意。二老爷跪在地上绞尽脑汁,想着传出消息让周氏想辙。老太爷有四个小厮,还有个管事,都是一等一的忠心,难以打点,不过还有扫院子的仆从,却是只认银子不认人的。老太爷骂人的时候,二老爷悄悄望了一个一贯在他跟前卖乖又有几分机灵的,到这奴才领悟了他的意思才转过心思应付他老子。
“父亲教训了儿子这许久,儿子都听在心里。不如父亲喝口茶歇口气,听儿子说两句。父亲说商贾轻贱,可圣上都说天下无商不富,从国库拨出银子铺路修桥为通商便利,不说远的,就说宜城境内,哪家没个行商之人?”
“别家是别家,我姚家是靠读书进学的人家。你也别拿圣上压我,他管着天下事,也管不了我教训儿子。”
“儿子也想读好书像大哥一般进士及第封官授爵,只是儿子没那天赋,在读书这条路上走不通。原先三弟在时都说儿子不是读书的料,劝着儿子另寻别路。”
老太爷坐在椅子上,喝了口茶,减了声音说道:“继续说吧,看你怎么狡辩。”
二老爷心酸了一下,老三就是死了,他说的话也比他个大活人管用。心里不自在,二老爷却还要缓着性子解释:“男子汉大丈夫,总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本事,儿子娶妻生子,总不能一辈子靠着府里,好歹要有能力养活妻儿。”
“养活妻儿也不止那与民争利奸猾狡诈的商贾一途,看你一手的金银珠宝,就怕人不知道你大哥贪污多少银子供一大家子人挥霍。”
二老爷更心酸了,死了的可以不计较,活生生的人就由不得人不嫉妒。老大一年的俸禄还不够他自己花的,就算贪了他也没见着一分,倒是他赚的银子要拿出一部分交给老大上下打点。算了,谁叫他不成器呢,只能做个商贾,老子不疼又有什么办法?“圣人都说因材施教,儿子只在这一途有个天分,就是天南海北费力与人周旋为了跑货三五天不休息都不觉得辛苦。父亲若看不惯这一身打扮,儿子换了就是,总不会带累大哥的名声堕了姚府的脸面。”
这边二老爷与老太爷周旋,二太太从小厮那里得了消息,急得跳脚。她不把四房放在眼里,即使四房得老太太宠,只因为二老爷给府里赚了不少银子,连管家的大太太都给她三分面子,更因为姚府里真正做主的是老太爷。二太太从来没想过要分出去只做个姚府旁支的宗族,跟武安侯府更是隔了十万里远。旁支的妯娌巴结,出去参加宴会有人逢迎,回娘家也没个人给她没脸,全是因为她是姚府族长一支,连着武安侯府。这宜城地界上,姚府到哪里都要五分脸面,那些想着攀上来的,莫不逢迎着她姚二太太。若是分出去了,哪还有往日的风光?
不行,不行,儿子还没长大呢,怎么能分出去呢?二太太像没头苍蝇一般走来走去,嘴里念叨个不停。二太太也不是个笨到要死的,不一会儿就分析清了形势:能够劝着老太爷的不过老太太和大太太,老太太恨不得她们立刻消失在眼前,但大太太爱财,肯定舍不得他们出去的。
二太太狠了狠心,蹲下身从床底掏出一个铁匣,将系在腰间的钥匙取出将铁匣打开,又将面上一层金子放在梳妆台上,从底下一叠银票中取出一张,犹豫了一下,又取出一张,才将东西收好放回原处。
大太太歪坐在楠木镂空雕花椅上稳坐着闭目养神,直到二等的丫鬟木香喊了一声“太太,二太太来了。”才挣开眼,对着一直在旁边伺候的丫鬟木莲说道:“你去跟二太太说一声,我正忙着,要让她等一会儿,好好招呼二太太,千万别怠慢了。”
既做了当家主妇的丫鬟,总有几分本事,木莲自是知道大太太只是在拿乔,要让二太太大出血。她一边儿沏着刘氏最爱的大红袍,一边脆生生答道:“二太太那里许多新花样,奴婢要好好讨教呢,太太只管放心。”
木莲到了外边,先是给周氏到了好茶,万分歉意说道大太太正忙,极力劝说周氏先回去。
“既然大嫂正忙,我不如在这等会儿。”
“二太太若不急着回去,正好木莲有事请教呢。”木莲心中得意,请了二太太上座,又拿出上太太赏的花样,拉着她说话。
二太太心里着急,听着木莲问东问西不容她说话,怎么都笑不出来,干巴巴点着头,脑袋却止不住往刘氏的方向望去。木莲心里暗笑,态度却不松懈,仍然拉着二太太不放手,直到听到刘氏的咳嗽声,才道恼:“奴婢真是该死,耽搁了二太太的时间,真是爱煞了前儿个的孔雀牡丹绣样才失礼,还请二太太不要责怪。”
能够踩在二房太太头上,木莲到底得意太过,眼里的喜悦太多,叫周氏看出了苗头。她正眼瞧着木莲,看得木莲歇了继续得了便宜还想卖乖的心思,才转身去找刘氏。周氏若没几分心思,也不能以个庶子媳妇的身份在姚府几番得意,木莲这般作为,明显是绊住她,到叫她知道了刘氏的心思,无非是刘氏知道她着急在等着狮子大开口。不过周氏最是分得清主次,不管花了多少银子,她总要买了刘氏的口去求老太爷。既然想通了,周氏心中的着急也去了,不过是银子的事而已,又算是什么大事。
刘氏看到周氏端着步子走进来,心里懊悔了,看来是弄巧成拙了。府里是大房当家,丈夫儿子都争气,刘氏觉得自己没什么地方可求着周氏,一点点懊悔立刻没了,笑着招呼周氏,直接问道:“弟妹这个时候找我不知什么事?若是我便宜,总不袖手旁观。”
“正是有事求大嫂帮忙。老太爷正在冲我们老爷发火,烦请大嫂过去劝劝,大嫂向来得老太爷看中,说一句话比别人一百句都管用。”
“弟妹抬举了。不过事情紧急,我就跟着弟妹去上房看看,不管老太爷听不听,我总要尽力劝上两句,我们婤娌得宜,我是舍不得弟妹的,再者高堂康健若是分家无得叫人揣测。”
“大嫂说的正是。不过总不要大嫂白出力,这是些许酬劳,还请大嫂别嫌弃。”周氏拿出一千两银票。
“弟妹多心了,不费力气的事,当不得弟妹的酬劳。”
“不过是借个名头给大姑娘添些嫁妆,大嫂千万别推辞。”
既然周氏知道她的打算,刘氏也不矫情了,痛快收了银子。
耽误了这许久,等到刘氏赶到的时候,二老爷将脑袋磕成血骷髅,幸亏老太爷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吼了一通正坐在太师椅上喘息,否则凭着老太爷的怒气,早一鼓作气叫二房搬出了姚府。
“老大媳妇来的正好,你帮着二房将东西理一理,择日让他们搬出府里另过。”
刘氏立刻跪在地上,“请老太爷责罚,此事媳妇万万不敢答应,相公最是看中几个弟弟,若叫他知道我让二房一家搬出府,定要将我休回家里。”
“老大回来了我跟他说,你照办就是。”
“就算相公不怪罪,媳妇也不忍看他心里也不痛快。相公对几个弟弟一般的用心,尽力为弟弟们考虑。三弟聪慧,读书上进,相公让出自己的名师,三弟进京赶考,相公打点地妥妥当当,反倒误了自己述职的事。二弟跑商,相公也是同意的,只因二弟擅长庶务,又想找个养活妻儿的正事,也是好男儿的作为。”
姚府里到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姚老太爷最看重的是英年早逝的姚三爷。姚二爷原先也靠着这点让老太爷消了几分气,只是他到底不忿老太爷将老三看作金疙瘩,老大看作银疙瘩,夹在中间的他却像脚下的泥被任意踩踏,冲动之下发了牢骚,才被训斥地直磕头。大太太一番话却比二老爷高明,不仅说出了因材施教的道理,而且为大老爷树立了光辉的形象,同时将老大老二老三三兄弟绑在一起。
老太爷果然神色松动了,不过提起已逝的三子,他神色总免不了带了痛惜。大太太是他故友之女,又在姚府当家这么多年未出差错,他也是看重的,给了十足面子。他叹了口气说道:“你起来吧,老二也别磕头了,别的好说,商贾贱业姚府是容不得的。”
大太太继续说道:“老太爷深明大义,商贾确是被人看低。只是二弟并不自己出面,只让管事们上下跑到,这是各家作贯的,到底关碍不大。再者,我们府里的支出也大。京城最近流出先帝下旨修订的《元平大典》,需五十两银子,运到宜城要不下一百两。再有相公在信中说想将书架子全换成楠木,能防虫蛀。若没有二弟的能耐,府里倒要捉襟见肘了。”
姚府有个观书阁,是姚家几辈子的产业,在江南一带也享有名气,武安侯府里十分看重,每年都拨了银子修缮,算是姚氏族中产业,老太爷对此不得不慎重。
老太爷听了沉思了一下,才说道:“即是你大嫂替你求情,我就饶了你这回,只以后要收敛,不要弄出土财主的样子来,也不准到处丢人现眼,若叫我青天白日看见你蝇营狗苟,定打断你双腿。”他年纪大,闹了这么长时间,实在累了,挥了挥手,打发了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