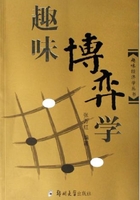躲避到香港的通商银行董事长杜月笙,在香港遥控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1938年4月24日,他致函该行总行常务董事会,告知该行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汇银行两行在香港组设通讯处,对外用三行联合名义,内部则各自记账,于4月5日起在港办公,并派业务部副经理陈国华暂行驻港,就近秉承董事长之命处理该通讯处事务。由此,香港通讯处取代了上海总行的一些功能。
1941年秋,中国通商银行奉国民政府财政部谕令,在重庆筹备总行内迁事宜。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沿海与大后方交通阻断,总行内迁之事搁浅。
1942年5月12日,通商银行重庆分行被财政部指定为内地管辖行,在总行未迁入内地以前,内地各行处受该管辖行指导监督。
随着内地分支行处的增设和业务的拓展,该行在内地之中枢管理机构亟须加强。尤其是日伪在上海对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家官商合办银行(即“小四行”)的劫夺,已使中国通商银行在沪总行形同虚设。为此,中国通商银行决定将总行由沪迁渝。
1943年2月11日,杜月笙向财政部呈请该行总行内迁,被批准备案。该行总经理胡以庸因病不能至重庆任事,经财政部批准,杜月笙兼代总经理之职。
1943年6月10日,中国通商银行总行正式在重庆成立,同时,通商银行函告各同业行庄,原上海总行机构及重庆内地管辖行同时撤销。8月13日,该重庆总行致函上海分行,令其于本月15日撤销,所有该分行经办事务归总行接办。
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内迁重庆的同时,战事导致前方人口、机关、学校、工厂的大量内迁,内地对金融业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为增进业务,中国通商银行在内地陆续广设分支机构。
抗战期间,中国通商银行先后在重庆、兰州、西安、宝鸡、洛阳、成都、自流井、东关、威远、平凉、天水、桂林、衡阳等地设立分支行处。
与总行的内迁相伴随的,是资金的内移。
中国通商银行在大后方未设分支行处时,曾因重庆地区放款获利丰厚,于1941年7月拨款50万元,委托代理人试办。因试办情形尚佳,是年10月初,通商银行又增拨50万元。
这两笔款项共计100万元,存在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的账户上,专做这一时期放款之用,作为主要的运营资金。这是通商银行资金内迁的开始,1942年重庆分行成立时,总行还曾汇去31万元筹备经费,也是资金内移的一部分。
通商银行在内地设立分行、支行、办事处时,总行拨付的营运基金,实际上也是通商银行资金的内移。
1942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的《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办法》中规定,商业银行实收资本50万元,方得设立分支行处,每超过25万元,得增设一处。对通商银行1943年1月30日呈请在贵阳、桂林、衡阳、曲江四地设立分支行处之事,财政部当年2月25日批示,要求该行连同此前在重庆、兰州、西安、宝鸡、洛阳、成都六地成立之分支行处,共增拨250万元资金。
对此,杜月笙在是年5月5日的呈文中表示,本行资本额400万元,对于此250万元当无问题。不过,当时内地各商业银行为应付政府的此项规定,虽然每增加一分支行处加拨25万元,但常常只是在账面上划转,中国通商银行也不例外。
实际上,与当时上海其他一些商业银行内迁一样,中国通商银行战时虽有资金内移,但运营资金主要靠就地筹措。
当时,中国通商银行在内地吸收存款可谓是突飞猛进,这得益于当时一种畸形的业内现象,时称“堆花”——由于中国通商银行官商合办的性质及董事长杜月笙的影响力,抗战时期,中国通商银行内地各分支行、办事处开业时,每每能获得同业的大量存款,其中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的支持和捧场为主。
譬如,通商银行西安分行开幕之日,来宾达2万人,存款达12708万余元,其中同业存款计6653万余元,占52%;宝鸡办事处开业时,同业存款8640万元,在存款总额12156万余元,占71%;自流井办事处开业时,收存款7170万余元,其中同业存款4248万余元,达59%;平凉办事处开业时,收存款3700万元,内计同业存款2200万元,达59%。
当然,“堆花”也仅是形式上争面子而已,并非有现款的真正支持,这点从该行天水办事处和西安分行的存款账目可以看出——该办事处开业时,收进存款21030万余元,大部分为同业存款,现款仅约5000万余元。
而且,此种存款属于临时性质,一旦达到了挣面子的目的,即完成了使命,故该行各分支行处之存款额往往在开业之后不久即锐减。例如,西安分行1943年3月10开幕时账面上的存款额为12708万余元,但到4月底锐减至6479万余元。
傅宗耀之死
抗战期间,尽管中国通商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辛苦经营,但是损失与波折依然是无法避免。
上海沦陷后,1937年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在浦东成立了伪“上海市大道政府”。通过一系列亲日人物的介绍,松井通过盛宣怀的孙婿周文瑞(系台湾银行买办,日本通),找到了野心不死的傅宗耀。
傅宗耀自从被撵出中国通商银行以后,霞飞路(今淮海西路)傅家堂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跟他往来的人大多是绅商闻人、北洋政府旧官僚。这批人都鼓动傅宗耀卷土重来,其中最起劲的就是周文瑞。
松井正在物色有名望的人物来当伪“上海市市长”,一听说傅曾是盛宣怀的心腹总管,又当过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市商会会长,立即派员到傅家数度联系。这正中傅宗耀的下怀,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傅宗耀征得日方的同意,将伪“上海市市政府”由浦东搬到江湾。松井就让伪维新政府伪维新政府: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为日本于中日战争期间成立的傀儡政权。后来于1940年3月和华北临时政府并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编者注任命傅宗耀为伪“上海市市政府市长”。傅宗耀叛国投敌,于1938年10月16日上任,成为众人唾弃的汉奸。
傅宗耀委任一派人物担任伪政府各局局长,还公然以市长身份出入租界,与各国使节交涉,要求接收国民政府在公共租界的政府机构、财产、权利,甚至通函要求租界上的居民户、商店一律不得悬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要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
傅宗耀的汉奸行径引起义愤,不断有汉奸在租界被人狙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在南京路上被人狙击(未死),伪市政府的几个局长也被人狙击(未死)。傅宗耀本人亦遭遇狙击,侥幸逃脱。
日本人此时也正在极力扶持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在日本轮船的护卫下,由越南河内返回国内,在上海虹口码头登陆。日本军部指定江湾重光堂为汪精卫的行馆。傅宗耀以伪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忙于迎接。
1940年3月29日,伪维新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解散,接着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成立后,对日本军部所豢养的伪上海市市长傅宗耀极其僚属一律加委,不敢撤换。
一时得势的傅宗耀,再次图谋夺回中国通商银行。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中国通商银行劫去了现钞10万元,离开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与其他银行设立联合通讯处。杜月笙还将中国通商银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多元携往香港,寄存在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同时将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在上海美国花旗银行,另外抽出150万元现金转移到重庆,存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杜月笙离沪时,就把中国通商银行全权交给胡梅庵(以庸)负责。胡梅庵害怕傅宗耀对他不利,非常恐惧,称病不出,把权移交给经理李祖基(胡梅庵内弟)承担。
傅宗耀任伪上海市市长以后,对杜月笙抢走他的地盘耿耿于怀,除图谋破坏中国通商银行外,还阴谋破坏中汇银行(杜月笙为该行董事长)。杜月笙得知此阴谋后,亲自打电报警告傅宗耀,傅不得不暂时作罢。
傅宗耀一贯主张,有政权在手,不能不办银行,银行之利近而厚,欲以政权与银行并举。傅与周文瑞商讨,先在苏州市设立“苏民银行”,又在杭州市设立“浙民银行”,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中亚银行”。这三家银行在傅宗耀的策划下,大权交给周文瑞,分布在苏杭两地,和上海连成一气,成为日伪渗入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据点。
傅宗耀的汉奸行径,终于在1940年10月10日得到了报应。这天晚上,傅宗耀在虹口官邸熟睡之际,被他最亲信的厨师、“两代义仆”朱升源用菜刀把脑袋砍了下来。买通朱升源的,正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战时损失
抗战初期,中国通商银行东南各行处资产遭受重大损失,主要是放款难以收回,房产遭受掠夺损坏,导致利润的两大主要来源利息和房租严重损失。
1939年7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中央各部会所属机关、学校及国营事业上报财产损失。据中国通商银行在1940年3月4日上报之资产损失,自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至1939年年底,该行在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汉口、厦门、宁波、定海等地之各行处所在地,或被日军侵占,或遭日机轰炸,或因郊外战事致受资产损失,共计直接损失3049万余元,间接损失1.7万余元。
这些损失数字,皆为该行上海分行向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和内地交通隔绝,消息久断,此后该行在沦陷区之损失详情,无法查报。后来日伪在沦陷区又强行接收该行上海分行,致使调查更为困难。
为减少资产的损失,中国通商银行曾于1938年9月29日将业务部库存留取少数作零用,其余整数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等移放上海本埠美国花旗银行库房,托其暂为保管。同时,将公债票据742余万元交李骏耀、陈国华带往香港交给杜月笙,杜月笙将其交给大通银行保管。
次年2月,该行将此项公债运回上海240余万元,余下之500余万元仍寄存大通银行。1942年5月间,该行将其从大通银行取出,准备携带至重庆,终因路途不便,敌人搜检甚严,又悉数改存香港东亚银行。
一年之后,该行担心此项公债被日伪掠夺,呈请财政部将其声明作废,若战后侥幸免于损失,则该行仍应享有持票人权益。至于留存上海之公债,则进行作废处理。
以上为因战争破坏而遭受的损失,而由于中国通商银行官商合办的性质,该行在沦陷区各行处还遭受日伪的强行改组和劫夺。
早在1942年冬,就盛传汪伪政府将对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小四行”进行改组。
后来,国民政府探悉汪伪政府已着手准备接收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三行,其中,内定邰树华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只等伪财政部长周佛海访问伪满洲国归来,即对该三行正式接收。
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43年5月10日致函该三行,令其在获悉敌伪确有强迫接收行为时,应立即通饬后方各分支行处对沦陷区一律停止收解,并将沦陷区行处之资产、负债及财产状况详细报部备案,并由该三行总行联合公告中外,通知各分支行处及往来之中外行号,以揭露敌伪阴谋并保护股东及存户之权益。
1943年6月26日,汪伪政府悍然对沦陷区之“小四行”实行改组,对四行资本、资财、人员、性质、机构、业务等方面作出规定。
关于资本,四行各为伪“中储券”伪“中央储备银行”是汪伪政权在日本扶持下设立的金融机构,该行所发行的伪“中储券”是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编者著400万元,一次收足,以各行在沦陷区之纯资产缴充。四行旧股东应于六个月内向伪财政部申请登记,经鉴定为无“敌性关系”或已断绝“敌性关系”者,始得按照旧股票面值换给新股票,六个月内未申请登记者,以弃权论。四行官股及与重庆方有关之商股,由伪国民政府接收,于适当时机出售于商民。四行财产中资产、负债,经伪方鉴定为有“敌性关系”者,移交伪敌产管理委员会管理。
关于人员,四行行员以无重庆方色彩者为主,并由伪财政部斟酌人选,其监察人选,亦由伪财政部指定,且监察人中,至少须有一人由伪中央储备银行职员充任。
关于性质,四行在伪中央储备银行统制下,经营纯商业银行业务。关于机构,四行应暂在上海设立总行、支行或办事处,必要时得逐渐在其他各地设立分支行处。
关于业务,四行于营业上有必要时,得向伪中央储备银行通融低利资金,改组前过渡时期之一切业务,仍照常由各该行重要职员负责处理。汪伪政府拟具各行董事监察人名单,其中,张文焕被指定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被日伪强行改组后,其在沦陷区之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汉口、厦门等地各分支行也随之被劫夺。
为应对日伪的劫夺,中国通商银行除将总行内迁重庆外,还联合“小四行”中其他三行一起发布严正声明。
1943年8月25日起,“小四行”在重庆市《中央日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等报刊连续将其联合公告刊登三天,公告主要内容有三点:宣布各行总行已迁移内地,告诫原有股东应保持立场,声明敌伪假借各总行名义所开办之伪行无效。
风雨通商银行(下):战后恢复,退还官股
战后恢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中国通商银行也随即展开了战后恢复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命令,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小四行”仿照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国家银行的办法,先行派员前往东南沿海一带接收、清理其被日伪劫夺的分支行,同时筹划恢复营业。
为了保证接收、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财政部还特别要求,接收人员不能在原被劫夺的银行中选派,只能在大后方各银行中遴选,而恢复营业的各银行,其经理、副经理、襄理等干部人员也应由后方派往。
为此,中国通商银行于1945年8月29日呈请财政部,该行将前往上海和南京等地办理接收清理工作,届时请京沪财政金融特派员和中央银行予以接济。财政部则训令,前往上海清理资负时,须与伪行绝对划清界限,该行除董事长杜月笙率先前往上海外,派协理骆清华率员前往上海和南京等地办理。
1945年9月,杜月笙先行回到上海,除了积极张罗自己的政治、社团势力外,中国通商银行的接收、清理、恢复工作也是紧锣密鼓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