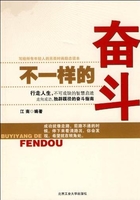然而,正如以上所述,文化的遗传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更易于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促进文化遗传改变的基因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建立起来的。它们产生了具有无限潜力的人类适应机制,后者可以借助人类所具有的生物条件而有效地发展作用。众所周知,有机体在不改变其通常机能运动条件下,针对其外部环境所作出的补偿能力,被称为体内平衡,而人类经由其经验、学习和教育而获得福利的能力,则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自动平衡机制。
白板说的原理对于那些相信凡人皆为平等机会所创造的人来说,或许是有所帮助的。不过,平等是一个伦理学上而不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这是文化进步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平等并非建立于生物同一性基础之上,事实上,除了孪生子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携带完全一样的基因,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由的和不平等的”,人的个性发展显然是因为存在着文化环境上的差异。白板说的追随者们以此作为证据,他们断言,人都是相象的。不过,恰恰是相反的结论才是有根据的。人类发展模式的可塑性是造成人们相互之间差异的原因,它是根据人们生活条件的不同进行适时调整的手段。人是形形色色而又彼此平等。
人精于控制其周围的物理环境,由于技术的进步,如今生活于不同地域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较少的区别,不过,如果整个人类仍然滞留于原始文化状态,这种区别将会大得无法比拟。相反,文明一次次召唤人们作出新的向往,提供了在诸如职业、角色方面日益增长的广大范围。
那么,进化过程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为适应这种本质上无限的功能变化做准备的呢?从生物学上讲,只有两种方式是可能的。首先是遗传特化。这一点可以与狗、马、或其他驯养动物的饲养作一类比而得到说明,人们已经驯化出猎狗、看门狗以及为退休老处女所迷恋的各式各样的狗。第二种方式是体内平衡和发展生物适应性。
人根据其社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涉及到这两种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并非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任意加以选择,相反,它们是互补的。依据经验和训练的修正总是伴随着遗传上的多样化。的确,大体上讲,发展适应性是这两种方式中更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由这种适应性带来的细节上的逐渐改进,曾适应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特征。
社会对于个体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求个体迅速随时代而变化,以便使得遗传本身足以确保种的持久延续性,至少在文明阶段上是如此。不过,遗传多样化倒是促进了人类适应潜能的不断增长。
人种的遗传品质并不能规定所有人本质上的善或无可救药的恶,不能规定人是有德行的还是邪恶的,聪颖的还是呆滞的,愉快的还是乖僻的。宁可说,它们只是提供人们以可能性的范围,但这种潜在可能只有根据环境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完全一样的遗传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对所有“正常”人来说共同的遗传品质。
遗传品质是极其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几乎是与活着的、曾经活着的,乃至将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数量一样多样化地同时并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载体,人类的本性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如同他们的人生观一样。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别就表现在,某些人是较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统一性,想到整体、无限性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们的精神则是具体的,他们往往考虑着健康的疾病、利润和亏损,他们创造了圈套和悲剧,除了那些他们业已具备,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知识之外,几乎从不对别的知识发生兴趣,他们总是试图去劳作、付酬、治愈和教授。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之为梦想家;第二类人通常被认为实际的和有用的。
历史表明,这种实际上的事务人往往缺乏远见卓识,同时也说明“懒惰的”梦想家的正确。不过,历史也表明,梦想家们往往出错。
可惜,我们无法获知,在多大程度上“梦想家”与“实践家”之间的上述区别是由其基因上和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这两者很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过程中。无论如何,一个由梦想家和实践家组成的社会肯定要比一个仅由梦想家或仅由实践家组成的共同体好得多。
人类社会,尤其是文明社会,其繁荣都仰赖于多样性,至于这种多样性究竟是由环境还是由基因引起,都没有两样,这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由许许多多有待运转的不同机构所组成的。的确,人的进化在一方面业已为可教育性和职业上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基因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
在这里,最有趣的谜语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同等权利背后所存在的这一多样性,以便确保人类最大限量的最大幸福。有谁敢斗胆声称,他已经完全解答了这一谜语呢?人为的符号系统是基于分类之上的,这种分类部分是人类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种特定文明历史中发展起来的。
培养完美人类行为的图式
有机体的进步和人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相仿的基础,即还原论假设。这种假设是:生物学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同样,行为科学和社会学亦可以还原为生物学。或者说,一个生命有机体是一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系统,所以人们设想,人的行为是那些低于人类的物种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和行为因素的特别错综复杂的综合产物。
我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明扼要地说,我确信科学领域是由这样三个层次组成的——物质自然、有机体和人的行为即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
让我再澄清一下我所表达的含意。我并不是说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彼此毫无连续性。作为一个对物理学下了很大功夫的生物学家来说,显然,我认为物理学和化学是生物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同样,生物学又是人的行为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我要强调的是,突现观点是基本正确的——每一更高层次上会呈现出较低层次上所不具备的新的特征。
让我们把这个图式运用到人的行为研究当中。人的行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答案简单而明确。人的所有特点是在语言、思维以及其他所有的行为方式中创造了一个符号世界。
人在自然中的独特地位是以其生活中的符号优势为基础的。除了那些生物学需求的即时满足,人主要不是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这里符号取代了物。例如,一个硬币是一种工作量或作用价值的符号;一份文件是某种成就的符号;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是一件事或一种关系的符号。一本书或一种科学理论是积聚起来的符号的奇妙的构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都表明,人的生物学价值和其作为人的价值是不相同的。与那些根据对个体和种类的生存“有用”或“有害”而进行的生物学划分不同,我们所谈的人的价值主要是指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符号世界。你可以发现这个定义涵盖了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如科学、技术、艺术、道德或宗教。当技术使人可以控制自然时,这些符号系统就可能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性和功利性。
这些符号系统可能是中性的,如希腊雕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很难说它们对更好地适应和生存有什么贡献。这些符号系统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个人的小符号世界崩溃了,就会导致战争和大规模的毁灭。
我的观点引出了许多可以思考的问题,这里我只能讨论其中的一部分,即神经学和进化论问题。人取得特殊成就显然源于其大脑的进化。用一种过于简单粗糙的话来说,正是由于神经学家的功劳,才使我们能够区分具有原始功能、本能和冲动的旧脑或原脑与具有人格、意识知觉、情感、意志行为,特别是人的符号功能特征的大脑皮层或新脑。让我们观察一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人的大脑,可以发现它们的特点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即前脑的脑量及其复杂性增加了。
我们所说的人的发展指由于前脑脑量的大量增加所造成的智力方面的发展的结果。由此,人类才得以建立起言语和思维的符号世界,并在5000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当中获利科学和技术的某些发展。
然而,由于对此缺乏解剖学基础的证明,在人的本能方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这里的结论既适用于行为的积极方面,又适用于行为的消极方面。卢梭所塑造的是质朴的完善的自然人,只是被文明所腐蚀了,而弗洛伊德所塑造的是被潜意识压抑力不可靠地束缚着的天生的侵略者、弑父者和通奸者。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浪漫的不现实的人。
尽管这种本能行为可能是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但它并不是人所独有的。几乎在所有动物身上都存在这种父母儿女的特性,其中有些表现得更加充分。我们取得了发展,从原始的神话到量子论用了5000年,从蒸汽机到氢弹用了大约150年。然而,自从老子、释迦牟尼或基督至今的一般道德水准的发展却并不乐观。解剖学的解释非常简单,即人的大脑皮层为智力成就提供了大约100亿个神经细胞,但是并未为情感和本能方面的发展提供基础。
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人为的符号系统是基于分类之上的,这种分类部分是人类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种特定文明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事实可以解释所有高级宗教共同遵循的关于行为的黄金律特征。第二个事实可以解释某些道德规范的特殊性。道德价值确实是有差别的。
这种差异之大,以至在某种文化传统中正常的行为方式会被在其他文化中的人看成是精神分裂症。这完全是由不同文化的符号结构所决定的,甚至是由一种文化中不同的参照系所决定的。在和平生活中将受到惩罚的谋杀行为,在战争的参照系中却被看成是一种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