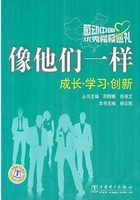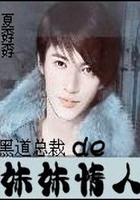企业界也有同样的情形。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或管理者一定也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可是,他应该对未来抱有极强的信心,应该尽量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自行承受所有的恐惧、怀疑或沮丧。在企业里面,在全体员工的面前,避免情感失控。
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我非常喜爱我的学生,和他们非常亲近,也希望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只有在不牵涉成绩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对我永远保持微笑与友谊。我完全有理由爱一位心理学成绩不佳的学生,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也无法接受。当我与学生成了好朋友,如果我给的成绩不好,他们就认为我背叛了他们,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当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认为,心理较健康的人就不会如此想。逐渐地,我放弃了这样的做法,特别是面对学生数目众多的大班级,我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与学生维持一种英国式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只有当我特地为某些学生准备资料,向他们解说,并事先警告他们会有不及格的危险时,这是唯一亲近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表明,老板和领导者必须有开放的态度,但此处的开放是指让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准备接受信息。
关于团体治疗与个别治疗之间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原因之一,两者的目的不同,治疗的对象也不同。因此重点在于,我们必须先弄清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再决定要采取团体治疗还是个别治疗,或是二者兼用。
一种比较大众性的结论就是,这些学习团体可以促进成长,促进人格健康发展,这是一种心理内化的过程(心理治疗是让有心理疾病的人变得正常,心理内化是让正常人变得更好)。这和耕田的道理没什么两样,一个好的农夫把种子播下去,创设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然后就放任这些种子自由成长,只有在它们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才提供协助。他不会常常拔出刚刚发芽的种子,检视它是否正常成长,也不会去扭转它原来的形状,不去推挤它或拔出来后再把它放回土壤里面。他只是把这些种子留在土壤里任其自由成长,只提供最少的帮助,甚至可以说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出手帮助。
毋庸置疑,爱罗湖的团体具备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拥有好的训练员、好的领导者,不会强行训练、塑造学员,只是单纯地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给他们一些成长的有机土壤或激发原来潜藏在内心的“种子”,任其自由地成长,而不给予太多的干扰。事实上,人类生活中也有许多存在性冲突,许多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许多时候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他事物,这就是冲突所在。当我们朝向某一目标前进时,往往必须放弃某件事物,甚至对此感到哀伤,但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正确对待自我实现者的隐私
我差一点忘记另一个问题,恰好现在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个非常私人的问题。这是从我阅读的书籍以及从爱罗湖的训练团体得到的启示,而且至少产生了半打以上的疑问。我发觉这个领域的工作者忽视了隐私的需求。当然,这些训练团体的目的就是要学员守住隐私。他们采取的自发式训练,就是教导学员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我隐瞒或自我揭露。他们所谓的隐私只是一种恐惧、强制、无能和限制等等。
实际上,在针对自我实现的人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当人的心理愈健康,就愈需要非强制性的隐私,他们比较没有神经质的隐私问题,也不会保有不必要的秘密,更不会刻意隐瞒自己的创伤,戴着一副面具生活。
我的这些想法是受到我太太贝塔的刺激,她是一个特别注重隐私的人。如果在20个人的团体面前要她说出自己的隐私,她会感到不寒而栗。这并非是神经质的隐私,她只对自己的知心好友说出心中的想法。许多人需要正常的隐私,他们会自我选择倾吐的对象,因此像爱罗湖的团体就不适合他们,好像对他们而言非常不自然,就算强迫他们参加,也不会有多大用处。在这种集体公开表白的过程中,这些人仍是保持防卫的心态。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区分健康的、有必要的隐私和神经质的、强制的、不可控制的隐私,我们必须努力解除神经质隐私——这些都是无用的顾忌,相当愚蠢、非理性、没必要而且不切实际。健康隐私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我们也很容易忘了个人之间的差异。依据我个人的经验,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从易于自我揭露到需要健康隐私。
为了确立此观点,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达到健康隐私的前提是瓦解神经质隐私,当然还要能够享受隐私,而且保持自己的独立(一些神经质的人,甚至大部分的平凡人就办不到这一点)。神经质隐私的瓦解是迈向健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这里所谓的健康包括对隐私的需求、享受隐私以及保有隐私的能力。
这种情形也诠释了前面所讲的议题,企业领导者在员工面前不暴露自己的一切想法是很必要的。在某些情况下,他最好保有隐私。当将军决定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时,最好不要到处宣扬心中的不确定和怀疑,更不要不停地扭动手指显示他的恐惧,因为这样的行为会瓦解全队的士气。所谓的健康隐私也包括这样的情形,当客观环境需要时就必须保有某些隐私。
这与另一个问题有关系,我曾在某个团体讨论的课程中谈到神经质防卫与健康防卫的必要性。我们必须紧紧记住一点,神经质防卫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是不可控制的、强迫性的、非理性的、愚蠢的、不被接受的。我们有许多控制冲动的力量,其中之一就是防卫,当然,我们现在已意识到,在现今的文化中许多的失序状况是由于缺乏控制所致,但是弗洛伊德当年却未曾意识到这一点。
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某人必须克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玩笑话,而是很有道理的。我认为人们不可以、不应该、也不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表达心中的冲动,我们必须有所节制,不仅是现实环境需要,也是个人发展和价值的需要。
事实上,人类生活中也有许多存在性冲突。许多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许多时候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他事物,这就是冲突所在。当我们朝向某一目标前进时,往往必须放弃某件事物,甚至对此感到哀伤,但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通常一个决定就意味着对一件事物的执着喜爱而对另一件事物的排斥,我们不可能在两件事物间来回做选择。比如说,一夫一妻制就意味着最后的决定以及永远的承诺,因此它就必然涉及必要的、健康的和可欲求的防卫。“防卫”一词已被人们过度滥用。在这里“防卫”一词用“因应机制”又名因应行为,指人在追求目标时,能面对环境限制所表现出的积极性适应行为,因应机制的目的在于减低焦虑、解决困难,而非逃避现实代替。
社会哲学家一再地强调,弗洛伊德所处的1910年与我们非常不同。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承受过多的压抑。部分是因为弗洛伊德使得这些不必要的压抑遭到瓦解。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冲动,甚至控制某些可欲求的压抑。
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曾有一位妇女,当她想到什么时,也不管别人还在说话,就开始说了起来,因此遭受团体学员的猛烈攻击:“请自我控制一下,闭上你的嘴,我们也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再说,别打断他人的话。”这就是必要防卫或因应机制的例证。
以前我常常在想,所谓的学习团体或是其他感受训练、人际关系、领导团体等,都只是假借团体治疗的名义。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不管怎么说,治疗一词已经有点不适用,它代表人在心理上有疾病。但就我研究表明,大部分学员就心理治疗的层面而言不算是病,只是就正常的情况而言有些许的偏差,但他们都是普通而正常的公民。因此他们需要的并非是员工式心理治疗,而是个人发展、自我实现的训练。
此外,我也逐渐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你使用心理治疗这个字眼,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厌恶,即使他们确实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例如,这些假名与同义词对于那些执迷型、倔强型、事物思考型的人以及不信任心理学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虽然我认为有比“训练”更适合的名词,但是我还是保留一些名词(不意味着能够治疗疾病)。
“训练员”这名词也有一点屈就的意味,好像我是一位健康完美的神明,降尊纡贵地帮助你这位不健康、不幸的可怜鬼,类似这样的说法都应该避免。如果我们强调存在型心理治疗师可能会好一点,他们与学员有着同胞之情,身处于同一条船上,相互帮忙,就像哥哥帮助弟弟,一切都源自于爱。所有的团体都应该放弃过时的医疗行为模式——以一种权威的心态,健康的人治疗不健康的人。
“学习信任”是治疗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去除一切的防护和防卫心态,特别是反向攻击和反向敌意,更要放弃以自己为目标的偏执狂心态。这与学习表达和自发是不同的,这也是关于现实主义和客观性的训练,因为它是根植于当今现实,而非儿童时期的现实。对现今而言,儿童现实已经不切实际而且是错误的。这与弗洛伊德强调脱离过去的意义是相同的,因此更好的说法是“学习信任”——当此信任符合现实情况时;或是“学习不信任”——当此信任不符合现实情况时。
另外一个实用的目标是学习隐忍感情。团体的领导者(我拒绝称他作训练员,因为那听起来好像是在训练熊、狗等动物一样的刺耳)必须保持镇定,他必须忍受他人的敌意,即使是碰到深沉的感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都必须无动于衷。学习团体的学员了解到,其他人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容易受到伤害。许多学习团体的报告表明,如果一个人受到客观地批评或是有人在哭,又或是有人激怒了别人,就会有另一个人出来解救他。但是就长期而言,大家必须藉由简单的经验,知道人不会因为受到批评而崩溃,他们所能承受的压力极限要比普通人高出很多,不过,这些批评必须是真的、友善的。
也许另一个目标就是学习辩护个人客观而友善的批评与攻击之间的差异。我在少数的团体训练中,也看到过这样的差别。
我们也应该学习容忍缺乏组织、模棱两可、无计划、没有未来的情况,这些都是重要的心理建设和发展过程,而且非常有成效。对于个人发展而言是必要的,这也是培养创造力的前提条件。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学习团体的选择性,特别是在位于山顶的爱罗湖或是其他孤立的文化领域。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没有真正的恶意,没有真正的毒蛇猛兽,没有真正恶名昭彰的坏人。换句话来说,他们都是高尚的人,或是至少他们都努力成为高尚的人。这是一样的吗?当然,有人会因为这些特定团体的成效,以为在所有的情况下均能实行。其实不然,比较好的说法是,这些位于山顶的学习团体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环境条件的允许。如果现在面对的是独裁性格的人、偏执狂或是不成熟的人,学习团体的成效就会令人质疑,这是很实际的情况,因为这些训练员或领导者都是经过特别筛选的。
我感触颇深的是,团体里的每个人都是高尚的,当然这里的人平均水平也比一般大众要高。这又牵涉到挑选的问题,因为世上没有足够优秀的人,组成上百个或上千个学习团体。这些团队是成长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只能进行有限的实验,因此,它必须小心教条、虔诚和形式等。
当我在山顶上问过一部分学员某些问题时,这种情形显得更加的真实。我问他:“魔鬼在哪里?精神病理学在哪里?现实证明存在的弗洛伊德式消极和悲观在哪里?”我感觉他们太倾向于罗嘉斯式的乐观主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人都是好的,所有好的治疗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但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在良好的环境下,大部分人都能自我成长,但不是全部。我对于领导者也有同样的质疑。就长期而言,我们不能自我选择领导者或治疗师,但是在许多著作中却没提到针对潜在领导者所设计的个人治疗。
我认为接受敏感度训练的人,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讨论心中的敌意——必须更明确、更仔细。例如,在我与他们共处的短短几天里,看到他们不断地练习公开表达自己的敌意。这是我们社会的最大问题,相较于弗洛伊德时代对性欲的压抑,目前心理分析师面对的是对敌意和进取的压抑,压抑的程度不下于当年的性欲压抑。社会越来越害怕冲突、不同意、敌意、反抗和排斥的发生。我们不断强调要与他人和平共处,即使你很不喜欢这个人,也必须这样。
在这些学习团体中,他们不但学习接受他人的敌意,而且还接受成为他人攻击目标的培训,培训人们成为靶子后该如何处理,才会不因此而倒下。我看到某些美国人超越一般礼教的束缚,愿意接受好友负面而善意的批评,也不觉得自己遭受攻击,反而将对方的行为视为情感的表达、协助的意愿。当今社会上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认为批评是对人的全盘攻击。但是在爱罗湖团体里,他们努力教导学员分辨何者是出于关爱、友谊和助人的冲动而提出的批评,何者是出于敌意或攻击的批评。
经过学习、训练后,团队中的学员变得更为坚强,更有适应力,更能承受更多的痛苦。毫无疑问的,这些人比较有勇气向别人说不,敢于批评别人,否定别人的意见,而且会因此产生一种抗拒大变故的能力。
对男人而言,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假如男子气概是我们社会的焦点议题;如果男人不够强硬、不够积极、不够果断的话,那么这些团体的训练对建立男子气概亦有所帮助。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男人喜欢安抚、讨好别人,极力避免任何的冲突、反抗,试着平息争端、手腕灵活、不断妥协、不制造争端、不捣乱,当大多数人反对时就轻易地举手投降,绝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性格的男性被弗洛伊德称为太监——遭阉割的男人,他们像一只宠物狗,努力地摇尾乞怜,讨好主人,在最糟糕的时候也不会做出反击。
为了能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理解,应该仔细研究弗洛伊德关于攻击、毁灭和死之愿望的论述。我并不是说要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主张,而是藉此对人的心灵有更深入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