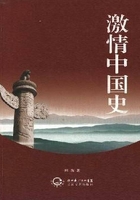跨步,转身,眸子决绝狠戾,袖中利箭快如闪电,横贯暗室,直刺屏风。
一道亮白寒光闪过,映亮屏风内隐约身形,只觉熟悉,她呼吸一滞,惊呼滞在喉间,已然来不及,屏风中人影似也才觉察,猛一闪,却是晚了。
只闻一声闷哼,血漫雪白绡纱。
手上一痛,那人攥住细链,顺势一牵,身子不由自主被拽到近前,下巴被一双冰凉的手扣住,因是受了伤,声音粗哑响在耳畔:“漫儿好手段。”
声音虽已粗哑,气息却还沉稳,想是方才那一闪,躲过了要害,可她那利箭求的便是一个“快”字,讲究狠准,瞬间毙命,他竟能躲闪,已然不俗。
屋内静极,只闻血水从袖沿滴滴跌落,凝到足边,鼻端些微的腥气,夹杂着他身上薄荷香,她既惊且慌,觉他伤得不重,竟觉安心,万种念头涌上心头,却成了反唇相讥:“谬赞,若论手段,临观怎及大人一分。”
他修长的指尚扣在咽喉处,并不觉逼迫,触在肌肤上,却是凉。
赫连瑜低“哼”一声,颈上的手撤离,肩头被轻轻一推,她踉跄几步,蓦然回首,才见箭头深深扎进他左肩,蓝底的常服大半肩头已被染成暗色,只似缭乱锦纹,顺着袖口滴滴答答淌下来。
一时傻了:“你……你受伤了。”
赫连瑜怔了下,迅速掉箭头掷到地上,顿时鲜血喷涌,半身浴血,他抬起眼来竟笑了:“殿下以为这是谁的手笔。”
猛然觉察失态,语气太过慌乱太过呆愣,她面有疑红,别过头去道:“大人私闯闺房,我未将你交与禁军,已是手下留情。”虽是这样说着,终是一句:“我……扶你到床上。”浅色素净的鲛纱帐,枕上满是她淡淡体香,肌肤慰贴十几个年头,只觉颊上烧的厉害,却他从容在床沿坐了,不急不缓抬手扯开领口,露出小片麦色肌肤……她倏地背过身去,背身将白娟伤药放在一旁:“我去收拾一下。”
他戏谑一声轻笑,听得她霞铺满面,忍不住狠狠想,早知就扎深一些。
可他不是鲁莽之人,定不会做这等鲁莽之事,只身到此,莫非是有所图,她心中暗疑,她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他注目的,莫非……陡惊出一身冷汗来,若是那里被他发现,此生她再无后路。
不能让他久留此地。
将那染血的低处拭静销毁,门上打开一条缝隙来,夜色里歪了一人,觉察有人,忙又跪直了,上官漫斜斜倚在旮旯里,随手捡了物件扔在地上,“啪”的一声,立即有人贴在门外问:“殿下有何吩咐?”
她蹙眉,到处都是耳目,将他送出去只怕不易,况已经宫禁,若想出宫,难比登天。曼声道:“没事,不小心打了东西。”那宫女微微迟疑,唯听她呼吸轻微,踌躇许久,才闻渐远脚步声。
顾婕妤刚刚得宠,众多妃嫔虎视眈眈,她不能这种时候冒险,转身进殿。
正撞上他裸着上身独自疗伤,衣裳褪了大半堆砌在腰间,他微微低头,浓密黑发遮住幽蓝眼眸,唯见侧面刀削轮廓,他露齿撕咬臂上缠就的白娟,想是动作极为别扭,身上渗出汗来,汗水顺着精壮劲瘦肌肉蜿蜒流淌迂回腹上,极是野性……曾经的耳鬓厮磨蓦然闯进脑海,她周身发烫,狼狈欲躲,只听他眼也不抬的低声开口:“过来帮忙。”
语气毋庸置疑。
她微微迟疑,暗吐了口气才在床盘杌凳坐了,他一只手极是不便,白娟缠的肥瘦不均,颇是凌乱。她掩住笑意重新给他缠了,边问:“大人打算怎样出宫?”
他低眼瞅着她,离得这样近,深睫浓密,翩翩若蝶,几乎根根看得分明,不禁有些心马意辕:“漫儿倒是盼着我早早离去。”
她用力在伤口上一拍,赫连瑜顿时眉头都拧在了一块,她站起身来用白绢绕过他上臂,广绣层叠拂在他肌肤上,酥酥痒痒,她声音平平:“大人是刑部尚书,请问朝臣与帝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可判个什么罪?”
她指尖柔软,袖中拢香,只觉温香暖甜,他眼中含笑,答得一本正经:“唔,若是已私定终身,罪加一等,朝臣重则丢命,帝姬么,却要听皇后的决断。”
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
上官漫斜斜睨他,重重系上一个死扣:“临观不想被大人连累,还请大人速速离开。”
只要他想,定是有法子的。
赫连瑜淡淡开口:“若是以前,我的人进入姝璃宫并不是难事,如今姝璃宫人多眼杂,宫外的人一接近,随时都会给殿下和充媛招来杀身之祸。”他缓缓抬眸:“殿下若是执意让微臣离开,微臣也只好强行……”
她翻了脸:“不必!”
赫连瑜慵懒弯唇,笑容倾城:“微臣这几日只怕要叨扰殿下了。”
她气结,旋即红了脸:“你我均未婚配,如此同居一室,像什么样子!”
他只挑眉笑望他,眸中意味分明,两人更为亲密的事情都已做过,却还在乎这个么。她读懂他是何意,只恼羞成怒,暗自压了半晌才冷静下来,依现在情形,只能将他藏在这里,殿外不知多少人等着捏姝璃宫的错处,她怎能将这样的纰漏置于人前。
夜色渐深,困意袭来。
转身倒了盏茶过来,置于床榻中间,瞥见他眸中意味深长,只别开眼自己径自和衣朝里睡去,夫妻同床,常是女子在里,夫婿在外,她并未多想,却习性将在外的位置留给了他。
床盘一柄纱罩宫灯,灯光柔和落在他面上,照见眼中溢出的淡略笑意,低头灭灯,拉了纱帐在她身后卧下,床身本就是一人所睡,躺了两人顿觉狭窄,他气息若有若无拂到后颈上,暗夜里枕畔另一人的心跳声。她心烦意乱,僵着身子动也不动,许久却闻身后呼吸渐沉,竟是睡着了。
懒懒翻身,只觉有人呼吸在侧,惺忪睁开眼来,清幽光线透过纱帐柔柔落在榻上,光线晦暗照见另一人侧影,正在疑惑,蓦地对上一双幽蓝眸子,深邃无波,灼亮如宝石,便那样看着她,她惊得身子一颤,这才想起来,昨夜她将他刺伤留宿,两人同塌而眠,想起前因后果,清晨空气清凉,她却莫名热了双颊。
他低低的一声,嗓音尚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唔,醒了?”
她忙转过脸去,只以为有这人在侧,定是一夜无眠,竟想不到睡的极沉。
突想起那碗茶来,转眸去找,四下里锦帐掩映,哪里还有茶水的影子,唯见床畔手边的茶几上空空如也的茶盏,不禁愣了。
赫连瑜的面容在纱帐下俊朗无双:“昨夜渴得很,顺手拈来喝了,该谢谢漫儿的好茶。”
她一口气呛在胸口,咳都咳不出来,冷冷撇脸,却见他斜斜倚在靠枕上,衣摆下修长双腿叠加在一处,并没有起的意思,她倚在床榻内侧,一时进退两难,躺下去不是,坐起来也不是。侧眼去看铜漏,她一向喜欢懒床,殊儿便在巳时唤她用早膳,时辰未到,自然无人前来扰她。
难不成便这样相顾无言,当真是十分难堪的境地。
忽闻殿门外一阵环佩叮当,宫娥内侍多穿软鞋,走路无声,却佩玉环绶压住裙幅,越发显得女子婀娜多姿,皇帝多爱此,宫内一时盛行。
有人轻叩殿门:“殿下。”
因姝璃宫曾是冷宫,无人约束,十几年来,哪些个规矩早已名存实亡,顾婕妤恩宠再现,姝璃宫也褪去冷宫面具,露出华丽面容,却比不得旁日自在了。
她隐约记起来,这个时辰,需去凤栖宫请安的。
宫里规矩,帝姬请安的时辰,使女叩门三声,不起,便可堂皇入室,三声已过,况门外多是皇后的人,只怕下一刻便会破门而入。
她含着怒意瞪向床边好整以暇闭目的那人,他莫不是想让皇后的人捉奸在床么?
却听殊儿声音适时响起:“殿下洗漱由我来伺候,姐姐们先行下去吧。”
回答的宫女语气高傲:“我看你并不懂得伺候主子洗漱的规矩,卯时已过,殿下未起,你倒是怎样伺候的。”立即有人接口轻笑:“姐姐与她计较什么,不过是个执灯宫女,你还指望她懂得大宫女的规矩。”
后面宫女掩口偷笑,声音极小,却是听得一清二楚:“你看她穿的那身衣裳,红衫子配个杏黄裙子,村妇似的。”
殊儿定是急了,一时竟未说话,上官漫听得也奇,殊儿向来穿的素净,今日怎穿着的这样浓重,虽是这样,却也不能让旁人欺负了自家人去。
忽听身畔一声轻笑,赫连瑜缓缓起身下床,让开路来,踱步走至窗下,他一手包了白娟吊在颈上,另一手背在身后,晨曦光线弥漫淡淡青色,只将他背影衬得柔和。
锦褥之上,他睡过的地方微微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