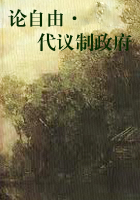第三十四章 露 面 (1)
弗兰士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让阿尔培参观斗兽场,可以不先经过任何一个古代的废墟,这样,游客就不会因对其他废墟心理上已逐渐适应,而对这座伟大建筑物宏伟气概颇有微词。这条路线是顺着西斯蒂尼亚街走,在圣玛丽-马热尔教堂前横切过去,穿过乌尔巴纳街和圣皮得罗街进入凡科利街,然后直达斗兽场街。
此外,这条路线还有一个优点:派里尼老板向弗兰士叙述的故事,居然连他那神秘的基督山东道主也被卷了进去,这在他脑子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象,而这样的走法,就决不会让他分心了。于是他在车厢的一角,双手托住下巴,不断对自己提出来一大堆疑问,然而没有一个问题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况且说,还有一件事也让他想起了他的朋友水手辛巴德,这就是强盗和水手之间的神秘关系。派里尼老板说,在渔民和走私贩子的船上万帕都能找到安身之处,这不禁使弗兰士想到了与那两个科西嘉强盗及小游艇的船员共进晚餐的那件事;仅仅为了把那两个人送走,那艘小游艇还特地绕道开到波托韦基奥港去了一趟。伦敦旅馆的老板也曾提到了基督山的主人自报的那个名字,这就向他说明:他不只在科西嘉、托斯卡纳和西班牙沿海地区,而且在皮翁比诺、奇维塔韦基亚、奥斯蒂亚和加埃特海岸,扮演了同一个友好的角色;在弗兰士的记忆中,他本人也提到过突尼斯和巴勒莫 (意大利城市,西西里岛的首府。),这也证明他的交游非常广泛。
虽说年轻人这会儿是全身心地沉湎在这种种回忆之中,但一当斗兽场废墟那硕大无朋的、黑乎乎的轮廓矗立在他眼前时,这些回忆就随即殆尽了。月亮透过斗兽场上一个个洞口,倾泻下缕缕惨白的光芒,仿佛是从幽灵鬼魂的眼睛里射出来的。马车在Mesa Sudans (意大利文:苏丹台地。)前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马车夫走上去打开车厢门;两个年轻人从马车上跳下来,迎面站着一个导游,仿佛是从地下刚钻出来的。
由于旅馆的导游是跟着他俩一起来的,这下他们就有了两位。
再说,在罗马,同时雇用几个导游的情况已司空见惯:当您踏进旅馆大门时,普通导游就会找上您,一直到您出城的那天为止,除此而外,每一处名胜还有专门导游,我甚至要说在名胜的每个景点上都有。因此读者想想吧,在斗兽场导游还少得了吗,既然这个斗兽场确实不同凡响,连马提雅尔 (马提雅尔(约38/41-约104):罗马著名铭辞作家。)都说过:
“孟斐斯 (孟斐斯是埃及古王国都城,位于尼罗河两岸。孟斐斯墓地有埃及著名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不必再向我们吹嘘它那荒诞的奇迹——金字塔了,人们也不必再歌颂巴比伦的奇观异景了,与恺撒子孙建造的圆形剧场 (指罗马斗兽场。)那叹为观止的工程相比,他们都得让位;用尽一切赞美语言来颂扬这座建筑都不是为奇。”
弗兰士和阿尔培并不想逃避这些导游的盘剥。更何况,只有这些导游才有权擎着火把周游这座名胜,没有他们麻烦将会更大。所以,他们没作任何抵抗,任凭这些带路人随意处置了。
弗兰士已经游览过十次了,他知道怎样去观赏。然而,既然他的伙伴是个新手,又是初次踏进弗拉维?韦斯巴芗 (韦斯巴芗(9-79):罗马皇帝,弗拉维三朝创立者,罗马大斗兽场即为他在位时建造的。)的这座古迹,我得承认是该夸他几句,尽管几个导游在一旁喋喋不休,他仍然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要不是亲临其境,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废墟居然还如此有看头儿;南方的月光仿佛西天落日的余辉,在它的神秘的光芒照耀下,那所有参差不齐的残垣断壁又仿佛放大了一倍。
因此,当耽于沉思的弗兰士在废墟的内廊下走了百来步,他就让阿尔培跟着导游走,自己则登上一个残缺不全的梯级;幸好这些导游是不会放弃那一贯的权利,会指引阿尔培仔仔细细地参观狮子沟、斗士休息室和恺撒家族的看台的。他见他们慢悠悠地一路往前走,就径自走到一根面向缺口的廊柱的阴影下坐下来,这样,蔚为壮观的大理石建筑便一览无余了。
弗兰士在那儿坐了大概一刻钟,他把自己埋进一根廓柱的阴影里,不时地看看阿尔培,后者在两名手拿火把的人指引下,刚从斗兽场另一端的一道门出来,这一行人犹豫紧跟着一簇磷磷鬼火的幽灵似的走下一级级台阶,向童贞女 (指专司家庭生活贞洁的女神维斯太的神庙中的侍女。)专用的休憩处走去。忽然,他仿佛听见从废墟的纵深处有一块石头滚落下来,这块石头是从他选定的台阶对面的那个台阶上滚落下来的,正巧落在他坐的地方。其实,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松动了,一直滚到底并不为怪,可是这一回,他觉得这块石头是某个人用脚踩下来的,尽管踩动石头的那个人尽量放轻脚步,但他似乎仍然感到脚步声移近了。
果然,一会儿工夫,一个人出现了,他延着台阶往上爬,他的身影也就渐渐清晰起来,因为弗兰士对面的上方开口处是被月光照亮着的,所以越往下去,梯级就越深入到暗处了。
此人可能同他一样也是一个游客,他宁愿独自深思也不爱听他的导游那喋喋不休的无聊话,因此,他的出现也没什么可以使他感到惊讶的;可是看他走上最后几级台阶时那瞻前顾后的样子,又看见他走上平台之后停下来,犹如在倾听什么的神态,显然,他来这里有着特殊的动机,他是在等候什么人。
弗兰士不由自主地最大限度缩到廊柱的背后。
离他俩呆着的地面十尺高处,穹顶开裂,有一个圆洞口,大如同一口井,从那儿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或许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洞口始终为月光留下这个通道,在它周围,生长着一簇簇荆棘,在沉沉的深蓝色的苍穹之下,浮现出它那绿色的倩影,而粗壮的青藤和一束束常春藤从这高高的平台上垂落下来,在穹顶下,犹如飘动的缆绳、轻轻摇曳。
神秘人出现引起了弗兰士的注意,此刻他呆在半明半暗处,尽管弗兰士看不清他的脸,但光线还不至于太暗,因此他尚能辨别出来者穿的衣服。此人裹着一件宽大的褐色披风,下摆的一角向上提起搭在他的左肩上,把他的下半张脸遮住了,而他的宽帽边则盖住了他的上半张脸。从洞口射进来的斜斜的月光只能照亮他的下半身衣履,因此还可以看得出他穿的一条黑色的长裤,裤管掖在一双得体的、雪亮的皮靴里。
不用说,这个人就算不是贵族,至少也属于上层社会。
他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开始显现出不耐烦的样子,突然在上面的平台上,响起了轻微的声响。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截断了光线,原来是洞口中间出现了一个人,他以锐利的目光向黑暗处探索,看见了身穿披风的人;他马上抓住了一把垂挂着的常春藤,顺着飘荡的藤滑下去,到了离地面三、四尺时,便敏捷地跳下来。此人穿着罗马台伯河右岸的特朗斯泰凡尔人穿的全套服装。
“对不起,阁下,”他用罗马方言说道,“您久等了。可是,我只迟到了几分钟。圣让?德?拉特朗教堂钟楼刚刚敲过十点。”
“不是您迟到了,是我提前了,”陌生人用纯粹的托斯卡纳方言说道,“所以别客气;况且,您让我等了,我料想您也不是存心的,一定有要事缠身吧。”
“果然如此,您说对了,阁下;我从圣仙堡来,费了好大劲才与贝波谈了一次。”
“贝波是谁?”
“贝波是监狱的一个管理员,我给他一小笔定期年金,他替我打听到教皇陛下堡内的情形。
“哦!哦!我看出您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亲爱的朋友。”
“那能怎么办,阁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我本人有朝一日也会像这个可怜的佩皮诺一样被抓进去;那时我也需要有一只老鼠来把我的牢房上的铁丝网咬断哩。”
“说来说去,您了解到了什么情况?”
“在星期二的两点钟要处死两个人,每逢重大节日开始的时候,罗马总有这套规矩。一个犯人被判锤刑 (原文为意大利文:mazzolato。),他是个坏蛋,抚养他的神甫被他杀死了,根本不值得同情。另一个被处斩刑 (原文为意大利文:decapito。),他就是可怜的佩皮诺。”
“那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您不信使教皇政府居无宁日,而且使邻近的王国人心惶惶,他们正需要杀一儆百哩。”
“可是佩皮诺甚至都没有加入我的队伍哪;他是个不幸的牧羊人,要说有罪,也只是提供了一些粮食给我们罢了。”
“这就完全可以把你们看成同谋了。所以您瞧,他们对他格外优待;假如哪一天他们抓住您,那您也知道,他们是会判您锤刑的,而对他不是这样,只是判他上断头台。再说,这也能使老百姓多看点热闹,欣赏节目的喜好各有不同嘛。”
“还没算上我为他们准备的一个节目,那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特朗斯泰凡尔人紧接着说道。
“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说一句,”穿披风的人又说道,“我觉得您正准备做一件蠢事。”
“为了使那个可怜虫免受死刑,我可以付出一刀,他为了帮我,现在陷于困境。圣母在上,假如我不为这个好心的小伙子尽点力,我就要把自己也看成是一个懦夫了。”
“那么您打算怎么做呢?”
“我将在断头台周围安排二十来个人,他被带上去时,我发出暗号,我们就手握匕首,把他劫走。”
“这个办法,我以为我的计划肯定比您的强。”
“您的计划是什么,阁下?”
“我把一万个皮阿斯特给某个我熟悉的人,希望他同意把佩皮诺的死刑推延到明年执行;而后,在这一年里,我再把一千个皮阿斯特给另一个我熟悉的人,让他帮助佩皮诺越狱。”
“您觉得能成功吗?”
“Pardieu (法文:当然啦。)!”穿披风的人用法语说道。
“您说什么?”特朗斯泰凡尔人问道。
“我说,亲爱的,我只身一个用金钱收买,要比您和您手下的人用刀子、短枪、马枪和火枪有用得多。还是我去做吧。”
这实在太好了!;可要是您失败了,我们还是随时准备干的。”
“假如您愿意,你们就随时作好准备吧,不过请相信,我会拿到他的特赦令的。”
“请您注意,后天就是星期二了。您只有一天时间了。”
“那又怎样!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每小时有六十分钟,每分钟有六十秒,在八万六千四百秒内可以做成许多事哩。”
“假如您成功了,阁下,我们如何能知道呢?”
“这个不难。我租了罗斯波利咖啡馆 (下文又有“罗斯波利宫”之说,其实指的是一个地方。)的最后三个窗口;倘若我得到了特赤令,则拐角处的两个窗户会挂上黄色锦缎,而中间的窗户挂上白色锦缎,上面还有一个红十字。”
“好极了。那么谁递交特赦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