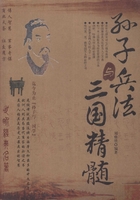第七章 审 讯 (1)
维尔福一走出大厅,就拿出一副手握生杀大权者的庄严气派,他脸部的表情虽极善于变化,——这是代理检察官常常对镜训练出来的,因为一个职业演说家应该善于变化表情,——但现在他却得花一番力量才能皱紧他的眉毛,装出一副庄严沉着的神气。维尔福惟一的遗憾,是他父亲的政治背景,假如他不是自己处理事情极端谨慎,那过去的回忆就可能会影响到他本身的事业。但除此以外,他可说是享尽了人间的幸福了。他已很富有,虽然只有二十七岁,却已有着一个很高的官位,而且快要和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结婚,他爱她,并非出于热情,而是出于理智,他用一个代理检察官所能爱她的态度爱她。她的美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的未婚妻圣?米兰小姐还出身于当时在朝廷里居于最高地位的一个家庭,她的父母别无子女。所以他们的政治权力可以毫无遗漏地由他们的女婿继承。此外,她出嫁时还带来一笔五万艾居的嫁妆,将来有一天大概还可加上一宗五百万的遗产。这一切因素综合起来,使维尔福得到了无限的幸福。所以,当维尔福略一沉思,静心地默察他的内心生活的时候,他就好像望到太阳上的焦点似地目炫神迷起来。
维尔福在门口遇到等侯他的警官,一见这警官,他就从三重天回到现实中来了。于是他的脸部又装出我们先前形容过的神色,说:“那封信我念过了,先生,你办得很对,是应该把这个人逮捕起来。现在快告诉我,你有没有发现他和造反有关的情节。”
“关于造反的情节,先生,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一切找到的文件都已封起来放在您办公桌上,犯人名叫爱德蒙?邓蒂斯,是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的大副,那条船是从亚历山大和士麦那装棉花的,是马赛摩莱尔父子公司的船只。”
“他在从事航海业以前,有没有在海军里服过役?”
“唔,没有,他还年轻得很。”
“多大了?”
“最多不过二十岁。”
这时,维尔福已走到康泽尔街的拐角上。有一个人似乎在那儿等着他。那人走向前来,那人是摩莱尔先生。
“呀,维尔福先生,”他喊道,“我很高兴见到你!您手下的人出于一件令人莫名其妙的原因——方才把我船上的大副爱德蒙?邓蒂斯抓走了。”
“我知道,先生,”维尔斯回答,“我现在就是去审问他。”
“噢,”摩莱尔说,“他是世界最优秀最可爱的青年水手。我敢说,马赛的商船界里,再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海员。维尔福先生,我诚心地向你担保他。”
书中暗表,维尔福是马赛贵族中的人,是一个保王党,而摩莱尔则是犯着拿破仑党的嫌疑。维尔福轻蔑地望了他一眼,冷冷地回答说:
“你明白,阁下,一个人在生活上也许可靠可敬,可以是商船界里最好的海员,可是从政治上讲,却可以是一个大罪人,是不是?”
代理检察官说这些话的语气很重,好像在说船主本人,而他的眼光似乎直穿对方的心,像是说,你为了旁人说情,你应该知道你本人也有问题呢。摩莱尔的脸红了,因为政治方面,他的见解也并不十分明朗,此外,邓蒂斯告诉他拜望大元帅的事和圣上对他所说的那番话也更增加了他的困惑,但他还是用深切关怀的语气回答说:
“维尔福先生,我求您还是像您一向那样公正仁德,早些放了他。”
这“放”在字在代理检察官的耳朵里听来很有些革命的气味。“唔,唔!”他默念道,“难道邓蒂斯是烧炭党的一分子,所以他的保护人要用这种同生共死的态度来求情了吗?我记得,他是在一家酒家被捕的,还有许多少人在一起,”于是他说,“阁下,你可以放心,我必定公平办理,假如他是冤枉的,那你的求情一定不会落空,但假如他的确有罪,那有罪不罚,在当前阶段,这个先例可开得太危险了,我必定要尽我的责任。”
他这时已走到他自家的家门口,他的家就在法庭隔壁,他用冷冰冰的态度向船主行过礼后就进去了,只留下后者像坚石似的呆立在维尔福离开他的那个地方。外客厅里挤满了警察和宪兵司令部派来的人,在他们中间,站着那个犯人,他虽然被严加看管,却仍很镇定,而且还带着微笑。维尔福穿过外客厅,向邓蒂斯瞟了一眼,从一个宪兵手里接过一包东西,一面进去,一面说:“把犯人带进来。”
维尔福的那一瞥虽然很急促,但对那个他就要审问的人却已有了一个看法,他已从那饱满的前额上认出了此人的聪明,从那黑黑的眼睛和弯弯的眉毛上认出勇敢,从那半开着露出一排珍珠似的牙的厚嘴唇上认出了他的坦白,维尔福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但他常常听人警告说,往往被表面所迷惑,他把这句格言都用到印象上去,忘记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所以,他抑制住心头的怜悯感,板起面孔,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过一会儿,邓蒂斯进来了,他很苍白,但却很镇定,还是带着微笑。他从容有礼地向他的法官致了敬,四顾寻找一个座位,好像他是在摩莱尔先生的客厅里一样。他这时才第一次接触到维尔福的眼光——那种法官特有的眼光,似乎要看透嫌疑犯脑袋里罪恶的思想似的。
“介绍一下自己。”维尔福一边问,一面翻阅一堆文件,这里边有关于犯人的情景,就是他进来时一个士兵递给他的。
“我叫爱德蒙?邓蒂斯,”青年回答说,“我是埃及王号的大副,那条船是摩莱尔父子公司的。”
“年龄?”维尔福问。
“十九岁。”邓蒂斯回答。
“你被捕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是在请人吃喜酒,先生。”青年人说,他的声音略微发颤,刚才那个快乐的时刻和现在这个痛苦的仪式对照起来,差别显然太大了。维尔福先生阴沉着的脸色和美茜蒂丝满面红光的面孔对照起来,其间的差别也是太大了。
“你在请人吃喜酒?”代理检察官说,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
“是的,先生,我正要和我爱了三年的漂亮的姑娘结婚。”维尔福虽然仍面不改色,却为这个吃了一惊。邓蒂斯是在他的幸福中被惊扰来的,而他也快要结婚了,他也是在他自己的幸福中被人召来的,但他却破坏了另一个人的幸福。“这种哲学感想在圣?米兰侯爵家里倒是一个极好的谈话资料。”他想,所以当邓蒂斯在等候他往下问的时候,他正在整理思绪。他觉得这是很好的对称话题,而演说家是常常用对称话题来获得雄辩之誉的。当这篇演讲整理好后,维尔福想到它可能发生的效力,不禁微笑了一下,然后转过来面向邓蒂斯。
“往下说,先生。”他说。
“您要我再说些什么?”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
“告诉我您要知道关于哪一方面的事情,我就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只是,”他微笑了一下,又说,“我预先告诉您,我知道得极少。”
“你有没有在逆贼手下服过役?”
“我刚要编入皇家海军的时候,他就倒台了。”
“据人报告说,你的政治见解很极端。”维尔福说,他本来从未听到这一类的事情,但他偏要把这次讯问弄得好像是一场控诉。
“我的政见!我!”邓蒂斯答道,“唉,先生,我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政见,我还不满十九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根本插不进去。假如我得到了我希望的地位,我应该归功于摩莱尔先生。所以,我的全部意见——我不愿说政见,而只是私见——不超过这三个范围:我爱我的父亲,我尊敬摩莱尔先生,我喜欢美茜蒂丝,先生。这就是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了。您看,这都是多么无味的事情。”
邓蒂斯说话时,维尔福凝视着他那伶俐坦白的脸,并想起了丽妮的话,丽妮虽不知道谁是嫌疑犯,却曾代他求过情,请他从宽处理,据代理检察官对于犯罪和犯人的知识来看,这青年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愈来愈使他相信他的无辜。这个孩子,——因为他还不算一个成人,——单纯,自然,有着绝对非人力所可强求的从心底所发出的雄辩。他对每一个人都抱着好感,因为他很幸福,而既使在幸福产生了恶果的时候,他甚至还把他的好感分给他的审判官,虽然维尔福装着一副可畏的目光和严厉的口吻。
“真的!”维尔福心想,“他倒是一个心地高尚的家伙!看来我为何不讨好丽妮,服从她给我的一道命令,我就可以公开吻她的手,还可以私下讨得一个甜蜜的吻。”脑子里充满了这种想法之后,维尔福的脸就变成了如此快乐,所以当他转向邓蒂斯的时候,后者注意到他脸色改变,也微笑起来。
“阁下,”维尔福说,“你知不知道你有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