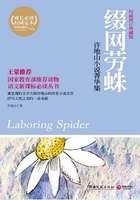第52章续前
莫里斯紧紧捏住须臾不离的长剑剑柄,整个场面对他而言就如一场幻影;他看见眼前一个接一个朋友落进深渊,而且再也回不来了,这个死亡的惨象对他的刺激太大,他扪心自问,为何他作为这些命运不济的伙伴,却能紧靠在深渊边缘而不在冲动之下也随着他们一起坠落呢?
洛兰跨过栏杆,看见迪克斯梅阴沉而嘲讽的神色。
正如我们所说,当他坐在她身边时,热纳维也芙倾身俯向他耳语道:
“啊!我的天主啊!您知道莫里斯也在这儿吗?”
“哪儿?”
“别立即就看;您这一看他就可能完了。”
“放心吧。”
“在我们后面,靠近门口。倘若我们都定了死罪,他有多痛苦啊!”
洛兰带着深深的同情看着少妇。
“我们会被判刑的,”他说道,“我恳求您别再心存侥幸了。倘若您还朦朦胧胧地抱有希望的话,届时会过分失望的。”
“啊!我的天主啊!”热纳维也芙说道,“那么可怜的朋友在世上孤单一人了!”
这时,洛兰才转身朝莫里斯的方向看,而热纳维也芙抗拒不了诱惑,也飞快地向那个年轻人瞟了一眼。莫里斯紧紧地盯着他俩,一只手压在心口。
“有一个法子能把您救出来。”洛兰说道。
“肯定吗?”热纳维也芙问道,眼睛里露出喜悦之光。
“啊,这个法子,我可以保证行得通。”
“倘若您救出我,洛兰,我会怎样为您祝福啊!”
“可是这个法子……”年轻人又嗫嚅道。
热纳维也芙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犹豫不决的神色。
“您也看见他了么?”她问道。
“嗯,我看见他了。您想得救吗?让他坐在这把铁椅上,您就得救了。”
无疑,迪克斯梅从洛兰的眼神中猜出他在说什么,因为他的脸先是白了一阵,转眼又恢复镇定,而露冷酷的微笑。
“不可能,”热纳维也芙笑道,“如果这样,我对他恨不起来了。”
“您想想吧,他了解您的慷慨大度,并且会同您比个高低的。”
“毫无疑问,因为他对自己,对我,对我们大家都了如指掌。”
“热纳维也芙,热纳维也芙,我的品格没您那么完善;由我把他拖下来,让他去死吧。”
“不,洛兰,我求求您了,我与他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死也不能在一起,我觉得,倘若我与迪克斯梅一起死去,我就是对莫里斯不忠了。”
“可您不会死的。”
“倘若他死了,我又如何能活下去?”
“啊!”洛兰说道,“难怪莫里斯爱您哩!您是天使,而天使的祖国已经升天了。可怜可爱的莫里斯啊!”
这当儿,西蒙听不见这两个被告在说些什么,只能用目光死死盯着他俩的脸。
“宪兵公民,”他说道,“请阻止谋反者在革命法庭上继续阴谋反对共和国吧。”
“嘿!”宪兵接着说道,“你很清楚,西蒙公民,他们在这里反不了;即便他们在策划谋反,也长不了。让他们聊天去,既然法律不禁止死囚在囚车上交谈,那又为何要在法庭上禁止呢?”
这个宪兵就是吉尔贝,他在王后的囚室里认识了女犯人,由于他一贯为人正直,不能不对这两人的勇气和忠诚表示同情。
审判长向陪审团征求意见;在富纪埃-坦维尔的提议下,他开始审问了。
“被告洛兰,”他问道,“您与迪克斯梅女公民是什么性质的关系?”
“是什么性质的,审判长公民?”
“是的。”
“最纯洁的友谊把我俩的心连在一起,
她爱我如同姊妹,我爱她如同兄弟。”
富纪埃-坦维尔听见这句辛辣的戏谑话,他那张铁面无情的脸面上微微泛白了。
“迪克斯梅公民是如何看待一个共和党人与他妻子的关系呢?”
“哦,这我可说不出来,我声明从未认识迪克斯梅公民,并且为此而感到庆幸。”
“可是,”富纪埃-坦维尔接着问道,“难道你不想说,你的朋友莫里斯?林代公民是你和女被告之间纯洁无比的友谊纽带吗?”
“倘若我不这样说,”洛兰答道,“那是因为我似乎觉得说出来有所不妥,我甚至觉得您也应该仿效我。”
“陪审员公民们,”富纪埃-坦维尔说道,“请认真分析这两个共和党人与一个女贵族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吧,特别眼下这个女贵族已经承认一桩旨在反对民族的最险恶的阴谋活动。”
“我又如何知道你所说的那桩阴谋呢,公诉人公民?”洛兰问道,他与其说惧怕这个证词的分量,还不如说被他激怒了。
“您认识这个女人,您是她的朋友,她称呼您为兄弟,您称呼她为姊妹,难道您不知她的行动吗?”审判长问道,“要不就如您所说的那样,她是单枪匹马犯下这个罪行的吗?”
“她不是单枪匹马去干的,”洛兰使用审判长所用的词反驳道,“因为我已经对您说了,现向您重复一遍,是她的丈夫迫使她去干的。”
“既然作丈夫的与妻子是一条心,你又怎么会不认识这个丈夫呢?”富纪埃-坦维尔问道。
看来洛兰不得不道出迪克斯梅的首次失踪了;看来洛兰不得不道出热纳维也芙与莫里斯之间的爱情了;最后,洛兰也不得不说出这个丈夫是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劫持了妻子,并且把她藏得严严实实的了;他这样做是为了澄清事实,从而也为自己辩白。
然而,要这样做,就必须揭开他的两个朋友的隐私;要这样做,就会使热纳维也芙当着五百个人的面羞得无地自容;洛兰摇摇头,内心似乎否定了这个设想。
“怎么样,”审判长问道,“您又如何对公诉人公民作答呢?”
“我说,他的逻辑是让人信服的,”洛兰说道,“他让我信服了,甚至使我都不怀疑自己了。”
“什么事?”
“就是我似乎成了前所未有的最险恶的谋反者了。”
洛兰的声明引起哄堂大笑。连陪审员也忍俊不禁:这个年轻人多么油腔滑调啊。
富纪埃感觉到被狠狠地嘲弄了一番。由于他的坚韧不拔的耐性,他终于了解到被告之间的秘密,与被告本人一样清楚,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对洛兰表示出同情与钦佩。
“嗨,洛兰公民,”他说道,“我们在听你说哩。”
洛兰又摇了摇头。
“沉默就是承认了。”审判长接着说道。
“不对,”洛兰说道,“这种沉默的本意就是沉默,就这样。”
“我再说一遍,”富纪埃-坦维尔说道,“你愿意再为自己辩护吗?”
洛兰转向听众,用目光探询莫里斯他该怎么办。
莫里斯没做出任何动作示意洛兰说话,洛兰默不作声了。
这是他给自己判了死刑啊。
接下来便是迅速处决。
富纪埃对他的起诉作了总结性发言;审判长又把讨论概述一下,陪审员去投票表决并且带回了对洛兰和热纳维也芙的判决。
审判长宣布对他俩处以死刑。
法院的大钟楼敲响两点。
审判长把时间算得很准,宣布判决时正巧大钟敲响。
莫里斯静听着这两种声音混和在一起。当宣判声和钟声的双重颤音止息之后,他也气力全无了。
洛兰把胳膊伸给热纳维也芙,宪兵们把他俩带走了。
这两人以不同的方式向莫里斯致意:洛兰微微笑着;热纳维也芙脸色苍白,难以自持,她用沾满泪水的手指,向他送去最后的一吻。
她直到最后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她之所以哭泣不是为了自己的性命,而是即将与她的生命一同消逝的爱情。
莫里斯有点神经错乱了,根本不能应答她的两位朋友的道别;他坐在听众席上时已经瘫软了,起身时脸色更加苍白、神志恍惚。他的朋友都离去了。
他感到还有一件心事放不下来,这就是啮咬着他的深仇大恨。
他向四周扫视了一眼,看见了迪克斯梅,他正与其他听众一齐走出去,并且低着头走过走廊上的那道拱形门。
莫里斯以弹簧弹开的速度,越过一排排坐椅,奔到那道门口。
迪克斯梅已经跨过门槛,走下阶梯,落入走廊的阴影之中。
莫里斯也随后走下台阶。
正当迪克斯梅的脚刚踏上大厅上的地砖时,莫里斯用手按了按迪克斯梅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