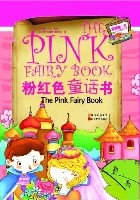第六章 安多纳德 (3)
耶南走到花园里,安多纳德大笑着,耍弄她的弟弟,要他跟她一块儿奔跑,可小奥里维拒绝了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离父亲很近;当安多纳德还纠缠时,他不高兴地推她,她只说些难听的话,见没人搭理,便独自进屋弹琴去了。
外面只剩下父子俩,
“怎么啦?孩子,你怎么不再玩了呢?”父亲柔声问道。
“我累了,爸爸。”
“好吧,陪着我坐一会儿吧!”
他们坐下了,九月的夜色分外清朗,喇叭花的香甜气息和花坛墙脚下泥土味儿混在一起,浅黄色的蛾绕着花飞,对岸的人悠闲的语声隐隐传来,而安多纳德在屋子里的琴声也缥缈地传送过来。耶南握住奥里维的手,抽着烟,孩子只望见黑影逐渐遮住父亲的脸,而他的烟斗里的星星的火光,一明一暗,终于完全熄灭了。此刻两人都不说话,静静享受这寂静幽美的夜。 终于,奥里维问了父亲几颗星的名字,像所有布尔乔亚人一样不懂天文的安东尼,除了几个著名的大星宿外,其他都不认识,但他假装知道,然后把那熟悉的名字一一道出。奥里维也不反驳:他只要听到父亲在讲那神秘的星空,就觉得有乐趣。而且,他也不想知道,只是以此来接近父亲而已。此刻,他们又静默下来。奥里维把头枕在椅子靠背上,张着嘴,仰望天空,父亲的手传来的温暖令他迷迷糊糊。突然,他感到他颤抖起来,奥里维很诧异,便假装轻快地说:“噢,爸爸,你在发抖!”
耶南听见后赶忙把手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奥里维问道:“爸爸,你也累了吗?”
“嗯。”
“别太辛苦了,爸爸。”孩子又亲切地说。
耶南紧紧地抱住奥里维,低声喃喃道:“可怜的孩子!……”
但奥里维又去想别的了。每到星期四,晚饭后他都要看书,那是他最大的乐趣,任何事都不能耽误他。当钟楼的大钟敲响时,小奥里维挣脱了父亲的手:“爸爸,我要看书去了。”
耶南让孩子走了,自己又踱了一会儿步,随后也进去了。
房里,孩子与母亲围坐在灯下,安多纳德往胸襟上缝丝带,嘴里轻轻哼着歌。奥里维听了很烦,拧着眉头,用双手掩着耳朵在看书。耶南太太一边缝补一边和老妈子闲扯——她讲些好玩的故事,语气滑稽,安多纳德还学着玩。耶南注视着他们,但谁也没看他,他迟疑地站了一会儿,又随手翻了翻一本书;他简直没法呆在这儿,便吻了吻孩子们就出去了,他的吻很热烈,有些异常,但两个孩子都没有觉察。他在隔壁的屋子里站着,当老妈子走了,耶南太太拿了条被单轻轻走进来,他迟疑一下,走过去说:
“请你原谅我刚才的粗鲁。”
耶南太太很想对他说:“可怜的人,我没有生气,但你究竟怎么了?干嘛不说出来呢?”
可她复仇的心理却令她说道:“别烦我,你那么凶,我连个佣人都不如!”
于是,她又恶声恶气地开始唠叨他。
耶南苦笑了一下,做了个手势制止了她,走开了。
当晚,谁也没有听到枪声。到第二天事情发觉之后,邻居们才记起半夜有“啪”的一声,好像是在甩鞭子。
过了一两个小时,耶南太太醒来,发现丈夫不见了,惊慌起来,在房间里乱找。当她发现他坐在椅子里,在桌面上趴着,鲜血还在往外一点一点流时,她大叫了一声就失去了知觉。家里的仆人们都惊醒了,把她扶起急救,同时把男主人的尸体放到床上,而孩子们却没有出来,奥里维虽听到外面的嘈杂声很想去看个究竟,但终究怕吵醒姐姐而继续睡过去啦。第二天,虽然孩子们还不知道,可消息已在城里传开,老妈子哭哭啼啼地说出去了。出殡那天早晨,法院就派来办手续的人,而银行家的顾客们拿出一副凶狠的嘴脸来对着那孤儿寡母大骂一通。因此对于两个孩子来说,那天他们恐惧多于难过。在大家的骚乱中,他们连安安静静地哭的权力也没有,安多纳德独自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出于自私的念头,拼命想着她的男朋友——只有这个念头才能帮助她逃避可怕的现实,她认为他会来安慰她,她每个钟点都在家等她男友——可是没人来,连个字条都没有,丝毫同情的表示也没有。
几天内,这个家庭终于完全崩溃了,主人死了,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地位、名誉和朋友——他们生存的基础都不存在了。母子三人都很看重名誉因而感到格外痛苦,其中安多纳德是最痛苦的——因为以前她根本不知痛苦为何物,而耶南太太与奥里维天生就是悲观的,故这个打击他们还能承受。当然这很可悲,但比一个乐观、幸福的人突然之间陷入痛苦,或被逼面对现实感到不平则要好多了。安多纳德突然看见了社会的丑陋,她终于开始面对人生了,她把父亲、母亲和兄弟统统批判了一番,而当母亲和兄弟伤心欲绝时,她却独自品尝痛苦。她在绝望地想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她并不幻想依靠谁,因为她已经看到自己已一无所有了,没了希望和依靠。
葬礼凄凉得很丢人,昔日的亲友无情无义地抛弃了孤儿寡妇。偶尔跑来个人露一下脸,但他们的窘相却令人难堪,那仿佛是对他们的恩赐,脸上又带有难忘的鄙夷同情的意味,而家族所带来的只有恶毒的责骂。在布尔乔亚人眼中,倘若一个人不肯忍辱偷生而宁愿死,他是不可原谅的,那仿佛是在说:“最不幸的是生活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就会以最严厉的法律来对付他,更何况耶南是令他们遭到损失的人,于是他的自杀不但没有得到同情,而且被认为罪无可恕,故教堂是不能接受一个自杀者的遗体的。
反正,耶南的自杀连最懦弱的人也指责他的懦弱——一个人放弃性命,同时又使他们的利益受损,使他们无法报复,他们气愤至极。而耶南经过怎样的痛苦才选择了自杀这条途径,是他们根本不会去想的事,他们要的是他要受到比这重千百倍的痛苦。当然,他既然逃脱了惩罚,为泄心头之恨,他们必须找人来承受——指责他的亲属。虽然,他们心里知道那是不对的,但他们还是必须那样做,才能泄愤。
耶南太太本来除悲痛什么事都干不了的,一听到别人攻击她的丈夫,立刻忘掉悲伤——此刻,她发现她如此深刻地爱着她的丈夫,母子三人一致同意把所有财产拿去还父亲的债务,而一无所有的三人在当地却不能容身,于是决意去巴黎。
动身的情形就像逃亡,在九月里的一个凄凉的黄昏,浓雾笼罩四野,湿透的树丛耸立路旁,而母子三人要去墓地告别。三人跪在新隆起的墓穴四周,悄悄地淌着眼泪:耶南太太在搜索她丈夫最后的言语,奥里维在想着在石凳上与父亲所谈的话,而安多纳德却在想他们的将来:“啊,爸爸,我们的未来多黯淡啊!”但三人对这个断送他们前途的人却没有怨言。雾渐渐散去,潮气浸湿他们全身时,耶南太太依然不忍离去,而安多纳德看见奥里维忍不住打寒噤时,便对母亲说:
“妈,我冷!”
离去前,耶南太太又回过头来,说了声:
“可怜的朋友!”
他们回到了曾给他们带来欢乐与痛苦,与他们自身为一体的老屋,度过他们的最后一夜——那是他们生命里的一部分,死才会使他们分离。
行李早就准备好了,他们准备搭最早的那一班车,趁邻居及街上铺子未开门时动身,不为人注意地离开——他们虽然需要在一起呆着,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间,摸着房里的一切——一动不动的,连衣帽都未脱,只求能与那些心爱的东西多呆一会儿,永远地记住它们。最后,他们尽力遗忘痛苦,聚在母亲的屋内——那是全家团聚的房间:当没外人光顾时,他们一家人尽量呆在这里,可他们发现以前的日子已经远去了——他们围坐在壁炉旁,一言不发,最后做了晚祷,便早早睡去,以便第二天起身。可是,每个人都不能入睡。
清早四点,耶南太太便起来了,安多纳德也起来了,只有奥里维依旧在熟睡。耶南太太望着那熟睡的孩子,不忍心叫醒他,她轻轻地走开,对安多纳德说:“轻点儿,让可怜的孩子再睡一会儿吧!”
她们收拾停当。外面依旧是静悄悄的——在秋凉的夜里,人们都留恋温暖的床不愿起来。那刻,安多纳德牙齿却在连连打颤,她感觉到身心冰凉!
当最后一次侍候主人的老女仆打开大门时,一阵寒气马上冲了进来,她是个又矮又胖、身子硬朗的老女人,脸上围了块布,鼻子通红通红的。当她发现夫人早已起床了,且把炉子也生好了时,不由得不安起来——当那老妇人泪眼汪汪地一进门,奥里维就醒了,而他一转身,闭上眼又睡过去了。
天色快亮时,安多纳德走近奥里维:“小乖乖,时间到了!”奥里维睁开眼睛,正看到姐姐对他凄凉地笑着,嘴里说道:“起来罢。”
他们悄悄地走到外面,晨风凛冽,街上空荡荡的,老妈子推着辆装载衣箱的车,而母子三人则手拿着包袱——他们几乎没带走什么,惟一有的则是几箱书、几幅画,还有摆动着的古式钟座,但那也是交给慢车运。所以,除身上的衣物外,可怜的一家可谓是一无所有了。耶南太太静静地想着她最后一次所见到的场景,想把过去的生活全部留在记忆里。
到了车站,因为不愿在几个熟人面前露出窘相,本来想买三等票的耶南太太买了二等票,随后又携带孩子们扑入空车厢,深恐再遇上熟人。然而一个熟人也没有:他们动身时,城里的人还未醒,车厢里只有几个乡下人和几头不断悲鸣的牛。当火车缓缓而动时,三个流浪者把脸贴在窗户上,对小城瞧了最后一眼。当火车拐了个弯,所有小城的风景都远去时,耶南太太忍不住哭起来,小奥里维哭倒在妈妈怀里,而安多纳德则躲在一旁悄悄地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耶南太太和奥里维想的是过去的生活,但安多纳德却是理智地想到以后的事情,她才不会像母亲那样把希望寄托在有钱的姊姊身上,而且还相信以他俩所受的教育和天分,找份好工作是件容易事。相反她对巴黎不存任何幻想,她埋怨的是自己不该情不自禁地浸入往事的回忆里。
一到巴黎,巴黎的拥挤和车水马龙便令他们疲惫不堪!天下着小雨,路上到处是飞溅的污泥,这三个被包裹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可怜人处处被人敲竹杠:雇了辆肮脏不堪的破车,结果是一卷被褥掉在泥浆里,价钱却是双倍的;住了一间又坏又贵的房子,被人挤在一个小房间,却算了三个房间的钱;后又为省钱不到饭堂吃饭,只叫了一些简单的菜,结果价钱却和饭堂的价钱一样,还没有吃饱;而旅馆里的脚步声、关门声、电铃声总是让他们心惊肉跳,车马和运货的响声亦令他们头昏脑涨,而沉闷的空气则使他们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在这可怕的城里,他们不知所措,被吓坏了。
第二天,耶南太太便携带两人去拜访她的姊姊——她姊姊住在沃斯门大街上的豪华公寓里——这是她摆脱困难的依靠,可第一次拜访便令人尴尬。因为她姐全家对这次破产十分不满,惟恐自身受到牵连,故对这破落户找上门来拖累自己表示愤怒。所以,他们只是用冷冰冰的态度来招待妹妹,而耶南太太说的处境和遭遇,他们只装没听见,也不留他们吃晚饭,只是在口头客套说请他们周末去吃饭——当然,态度也不诚恳——耶南太太回到旅馆,三人对这次初访都不敢说什么。
以后的几天,他们为租一间公寓爬着一层层累死人的楼,而对住惯大房子的耶南太太来说,住那军营式的屋子,走污垢的楼梯和阴暗的房间太难受了。而且,他们实在太笨,不能自卫,每一样东西买到他们手上都特贵——走在街上、进铺子、上饭馆,他们老是很慌乱,被人欺骗。
耶南太太尽管对其姊一家已经失望,但对那未吃的一顿饭还心存幻想,所以他们一边打扮一边心惊肉跳地想着他们被当成不受欢迎的人。而在饭桌上,其姊姊僵直地坐着,摆出一副教训人的神气,而耶南太太鼓足勇气想说出自己的要求时,亦被她生硬地打断。而孩子们的表兄表弟也拿出一副傲慢而无礼的态度,跟他们乱扯一通,令孩子们相当尴尬、狼狈。
饭后,耶南太太又教女儿弹了一会儿琴,以显显他们优良的教育。而小姑娘十分窘,她完全被弄糊涂了,因而弹得一团糟,而她的姊姊们厌烦得要命,只盼她弹完,亦和耶南太太胡扯。当她弹完时波依埃先生喊了声:“好极了,把咖啡端过来吧。”
波依埃太太说她女儿的老师是比诺,而那位小姑娘则傲慢地说:“你弹得不赖,小可怜……”然后问安多纳德是谁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