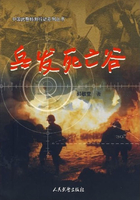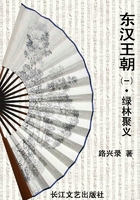这件祸事开场时,谁都当是喜事。胭脂化开来,于唇间印下一抹艳色,君家二姑娘披上大红的裙帔,就要出嫁。
“小姐,你还是要嫁他。”身后有人道。
二姑娘听这喑哑声音,除了阿小再没别个,气呼呼转头时,猛见她坑坑洼洼的黄脸皮,纵然是看常了的,也有些心悸,便错开目光道:“今日是我的大日子,你不必说了。”话是淡的,并不曾当真责骂。但比平时已重了许多。
阿小听在耳里,笑笑,上来接了丫头手里的玳瑁八宝梳篦为她梳头,口中道:“纤云死了。”却是好生轻闲一句。
二姑娘双肩一抖,觉得背脊骨寒浸浸的发毛,张大眼睛问:“什么?”
“跌到水里淹死了。也有说她是自己投水死的,老爷捆了几个小厮叫大少爷问着。”阿小说得还是闲随,“不过小姐不用担心,我已问准老爷,替了她的缺儿便了。”
“你——”二姑娘下力气把头一仰,牵动了头发,“嗳哟”叫出声来。阿小双手不停,口中道:“小姐别急,别乱动,这当儿就好了,且插个簪子……瞧,这不是好了?”前后菱花对住,合祥髻果然已梳完,点翠凤簪衬着鬓边的金珠宝石掠子,甚是端丽。二姑娘点点头,提起裙子往外走。阿小在后头叫:“小姐!花儿还没戴上呢!”她哪儿理会,一径寻母亲去,还没寻着,乳娘早抱住了叫道:“快上轿了还跑哪儿去哎!看把头发毛了。”
二姑娘心头躁急,问:“我娘呢?”乳娘笑道:“我的小姐!你出阁的箱箱笼笼、桩桩件件,不都得夫人看顾?这会子正凿二门外那干小鬼的头皮,你倒找她呢!”说着,觑了二姑娘的神色,心里敞亮,悄问道,“为那丫头的事?”说着努努嘴皮子。
二姑娘跺足:“可不是?不知爹怎么会……”说到一半便顿住。阿小虽然没有认祖归宗,说到底是君家老爷跟外头女人生的孩子,老爷难免照顾她些儿,阖府都清楚,二姑娘是大家闺秀,自然不好抱怨得,只是想想阿小那个丑样子,竟跟她嫁到夫家去,成何体统,眼圈儿还是急红了,“我找娘去!”
乳娘一把拉她到旁边,附耳道:“那时候,夫人在跟前呢!也是许了的,没得空过来,知道小姐要烦恼,特别叫老奴来告诉小姐一声。纤云那丫头太不规矩,出事儿是迟早的。小姐慈善,要带她过门,她没这个福分,早走了倒好,总比到那边再闹出来强,是不?再说阿小,一听说出了这事,就到老爷面前主动请着去服侍小姐,也算有心,不枉小姐一向来待她的仁厚。她心思虽深一点,过去就跟小姐是一条船上的人啦,那张脸皮争不得宠,闹不出夺主子地位的事,总得尽心尽力帮衬小姐,这不是小姐因祸得福的好事儿?”
二姑娘依然嘟着嘴闹别扭,感怀着纹月,还很掉了几滴眼泪,及至君老爷觉得过意不去、给她多加了两大箱子嫁妆,她才拭了眼睛回去梳妆,披上大红盖头、上了大红喜轿,一路吹吹打打、风风光光嫁进了肖府。话说肖府世代书香,肖少更是举城闻名的佳公子;而君家经商,富甲一方。这两家联姻,看出了多少人肚里的妒虫。总说是泼天的喜事,谁猜到呢?十七个月后,新房便张起素帷,白烛替了红烛,君氏新娘子成为一具冰冷的尸。
二姑娘死的时候,肖少正在他新娶的小妾房里。家人奔过去喊他,阿小独个儿守在死人的床前,看那张容颜,早是病得瘦损了,如今失尽生气,倒显宁静。西风萧索,吹起一点儿杏仁香。阿小慢慢想:谁都猜不到吧?这么快就有今天。当年,何尝不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只当能胜却人间无数。
那时节,天气刚有点儿交暑气,君家园子里小台子上早用水泼得透凉了,重金购些奇石修竹点上,做出极雅致样子,君家大少爷带了个客人回来,于台上饮酒消暑不足,又道是府里一个丫头种了盆好芍药,便叫捧来看。
种花的就是阿小。照理说即使妾生的女孩,也是君家的血脉,人前人后照样得被尊一声小姐。但阿三的母亲连妾都不是,无非一个打零工的下女,日常交往都有些不清不楚的,生阿三时,早离开君家到外头谋生活去了。后来君老爷把阿三领回家来,到底没给她正名分,一来是轻贱,二来也难免存着疑心,含糊着在君家作个丫头,给呼来喝去的,已习常了。大少爷要她捧花去赏,她也就依命过去。
这盆芍药长得好,叶浓花茂,在小车儿上推过去,枝叶遮了她的脸,单露出一双眼睛来,倒是秋水一翦。客人看得不觉有些儿凝神。谁知走到近前,是那么张面皮,不由“啊哟”骇了一声。大少爷捧腹而笑。
阿小听到声音才抬头,看了看这个锦衣玉带的贵客、又看了看幸灾乐祸的君大少爷,木然片刻,唇角倒勾起来,手一甩,生生把那盆花在地上摔了个稀烂,手指着大少爷便道:“你莫作鬼,叫我来见客呢?我是不惯逗趣的,撑不得少爷你的场面,少爷要寻乐子,找别人卖笑去。这里我不配差使,少爷找老爷撵我出去,大家落个清净!”
两位少爷不由愣住。二姑娘正好经过院墙外头,听见声响,知道自己亲生哥哥惯常行事是有些不妥当的,怕当真闹成大事,急着要来劝解,待转过树脚,方见有客,避也避不回了,索性大方见礼,肖少忙回一礼,彼此觑着:一个是玉容绮貌,一个是俊采温柔;一个是闺阁里惯养幽致,一个是文墨中久识风流。两下对了面,哎呀,春风怎的一个交错,眉睫间遍地韶华。阿小在旁边看得清楚,当时就觉得不祥。
二姑娘是没听她的话。不然,何至于真把性命虚掷在这人身上。阿小淡漠的想。她人丑,谁都不愿多看一眼。这层淡漠就没引起什么注意。肖少赶到时,跟阿小招呼了一声,也没认真看她,只是立在二姑娘尸体前,开始发呆。直到阿小忍不住了,开口问:“姑爷,这怎么办好?”1他才茫然抬头:“什么怎么办?——哦,这、这事……”忽然间怪俊气的眉毛都垮了下来,捂着脸呜咽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的?”
他问别人,别人还要问他呢!肖家老爷一把捽了他去:“这是怎么回事?”肖少红着眼圈:“我也不知道啊。”肖家老爷捞起一把扇子劈头盖脑就打下去:“你不知道!叫你冶游,叫你纳妾,叫你不三不四不上进,叫你不知道!”
那扇子结实,是二十骨的紫檀木泥金扇,合起来,跟一根短棍也不差什么,“呼”一抽一道血痕子。肖夫人在旁边看得肉痛,扑上来护住儿子:“说就好了,打什么!儿子自有些淘气处,也不过出去游玩,打小儿有的,什么大事。她一个商贾女儿,要不乐意,别嫁过来我们家呀!我早说别结这头亲,她家一盆火的送进来,如今自病死了,又关儿子什么事?”
肖老爷攥着扇子喘粗气。君家是商贾门户,“士农工商”里垫底的人家,他本来就有些看不上,只是忽闻说媳妇恹恹病死了,那做家长的总要有个姿态,何况老话“棒头出孝子”,儿子本来有机会就该多打两下的,见得是个家教。如今他打得累了,觉得已经教训得差不多,不再认真追究,虚踹一脚,叫肖少进祠堂思过去。
二姑娘的灵堂已经设起来,齐整归齐整,就有点冷清样子。她自嫁过来,没得过公婆什么好脸色,此刻死了,更没人把她当回事,不过香烛上供足礼数,再拨两个丫头守着,也就是了。
这种苦差使,阿小是逃不了的,在灵前老老实实跪了。另一个小丫头是灶房里拨过来的,老揉眼睛打呵欠,顺口问阿小:“哎,听说你在那边本来不是跟你家小姐房里的,感情好,才带过来?”
阿小点头。她被君老爷带进府后,不曾认真分进哪个房里,日常就应应散工。各房却正因为知道她的出身,格外有机会要多踩她几脚,聊为解闷消闲。多亏二姑娘时时照拂她一二,日子久了,难免积下些感情。“我们家小姐是个仁厚人。”她说。
“跟我们家少爷早就认识了?听说还有点儿……事情?你们小姐是不是挺那个啥……有故事的啊?”灶房丫头兴致勃勃贴过来问,两只眼睛贼亮。
阿小默然。二姑娘有什么故事?顶顶端庄不过的人,有事,只闷在心里。肖少当年那样子讨好她,她心里欢喜,回了房也不过脸埋在枕头里头笑;及至过了门,吃了苦楚,苦也只往肚子里头咽。如今死了,人家还当她是自荐的莺莺、夜奔的文君呢!死了也是白死。阿小当初劝什么来着?不听的。端庄人就有这么股子牛脾气,埋头走她的路,乱棍都打不回头,到死方休。
外头脚响,有人进来,灶房丫头忙行礼:“少爷!”阿小抬头看时,可不是肖少?祠堂罚的时辰满了,此刻着身齐衰之服2,头发拿银环在顶上一总束起,衬那个眉眼,穿孝都穿得格外风流俊俏,来到堂前,不忙举哀,先向灶房丫头点点头,又向阿小欠欠身,非常客气。
他总是客气的。阿小想。温文尔雅,缱绻温柔,没的像股子春风,不怪傻女子们飞蛾扑火的赶着他呢!销魂销魂,争晓得断了魂?
这么想的时候,她唇边浮出点子冷笑来。依然没人注意。肖少已走至灵牌前。原先随众人一起尽哀礼的时候,他有点木讷讷样子,拘束着,脸上未敢现什么表情,如今单独立住了,看着灵牌,眼圈倒一点点红起来,叫声爱妻,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好一会儿方收住了,坐片刻,烧了几把纸元宝,才起身离去。灶房丫头感动道:“少爷真是多情人儿!”阿小不语,蹩至窗前,看肖少的身影往他新娶小妾那边去,唇边又浮出一丝冷笑。
也就这样子了。什么多情?什么结发?明明负了这么多,世人还要夸他。要说公平,天下是没什么公平的。二姑娘怎么就傻得嫁过来?那时候大少爷贼忒忒跟她咬耳朵:“肖公子家世很好啊!我们家的生意都要靠他照顾。妹子你要是能嫁给他,以后都不用愁了。”二姑娘不过啐一口。可后来肖少悄悄传进来一个香囊,里面塞个纸条,不是诗、不是词,单只没头没脑一句:“你有没有觉得,世上的花都开了?”二姑娘颊边忽而就飞透了红霞。阿小她看得是清楚的,当时就苦劝:“这种瞎说白话的人,顶顶不好信,小姐你莫发昏。”二姑娘不听啊!唉,那一刻的动心,刹那里繁花开遍,哪里还听人劝谏?只管往斜路上去,到底遭了报,而这个让人吃苦送命的凶手……也该有报应吧?
夜幕沉沉,灶房丫头熬不住夜,早埋头睡去,迷迷糊糊觉得有冷风拂面,心下一激灵,想睁眼,眼皮却像粘住了似的,勉强只睁开一丝来,见条影子飘出门去。她闪念过:“别是有鬼咧。”随即又陷入睡梦中。
西院厢房里,甜纱斗帐覆了香衾,交颈鸳鸯正在缠绵。月色惨白,窗口传来一声幽幽叹息。肖少的动作猛然僵住了,神情比死还难看。那新娶的小妾唤作明月,倒是机敏大胆,忙转头看,只见个雪青斗篷的人影一闪而没。肖少的身子筛糠般抖起来。明月抱住他,问了又问。他嘴里只迸出一个字:“鬼……鬼!”
肖府彻底乱了套。肖少那夜见鬼,虽然死都不肯说鬼是怎生模样,但里里外外都传说:恐怕是少奶奶的魂儿回来讨说法了。不然,何以不找别人,单到他前面叹口气?
这个推论非常之有理。肖老爷虽然念叨着:“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寂寞了两日的肖少奶奶灵堂前,忽而就做起了热热闹闹的法事来,明里是超度亡灵,实在却为祛邪消灾。阿小再见到肖少,他的神气比先前已经不一样,没那么顾盼自如了,惶惑着双眼、肩背都有些缩起来,像只受了惊的老鼠。阿小看得又是解气、又是可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今日,见着人家回来找他就害怕;可是当初,分明是他求着人家的呀!
那个孟兰节,二姑娘去佛寺上香,一路山景清美,她在个悬崖边停了会儿,笑笑,片刻方入寺去。阿小独在门口采买香花烛纸,肖少过来就作个肥揖:“姐姐!你们家小姐适才站了住一会,是在看什么?”
阿小吓一跳,兜头啐道:“你这人怎么跟个鬼似的,从哪里钻出来!”肖少也不恼,软言软语,塞她一枝包金簪,苦求帮衬。阿小软了口气道:“她说悬崖中那簇花生得好看呢。你知道了,又待做什么?”肖少点点头,笑嘻嘻不言语,只是千恩万谢而去。
结果,二姑娘一行再出寺时,平白吓一跳:悬崖边观者如堵。一个锦衣公子,身上系了几根结实绳子,着三个壮汉慢慢往悬崖下放,接近半中腰那簇桃红山花时,伸手去采。山风吹来,他身子晃了两晃,二姑娘倒吸一口冷气,面色忽红忽白。纤云悄声道:“小姐,那不是肖公子?”阿小急促道:“小姐,我们快走!”二姑娘死挪不开步子,眼神盯着那人,泪水涌出来,只管在眼圈里打转,不知是感动的还是吓的。直到肖少擎着一枝上好山花,平安回到山道,二姑娘才松口气,再转念一想,只怕他当众将花赠给她,那惹起闲话须不好看,忙催促阿小和纤云搀她离开。谁知肖少只向这边望了望,并没过来,顾自走了。
围观人议论纷纷,不知肖家公子发的是哪门神经。二姑娘一分放心、十二分失落,坐到轿中不言语,生着闷气。行到处僻静地方,却忽听后头蹄音踏踏,青玉鞍的骏马、玄缎披风的肖少,那么泼风样的赶来,赶到了,也不做什么别的,只从披风下取出那枝山花,插在她轿子的窗前,隔着帘子看她一眼,唇角温柔的弯起来,一笑,拍马离开。二姑娘唇角不觉也泛起个笑意,掀帘子将那花取在手中,见上头还缚着块丝巾,打开来,几个字道:“昨夕凭尽栏干,今日酬卿一笑。”二姑娘耳畔酡红、双眸滟滟流光,默然扬起纨扇遮住脸,而嫣红唇边的那抹笑,再没褪下过。
那时候,连阿小都不得不承认,她真美。可是谁能猜到?美丽的姑娘和吓人的鬼魂,只需隔过两度春秋。
水陆道场那边,还在摇铃打锣的喧嚷。阿小因为守夜累了,告假退回自己房间。窗外风色融和,隔了半个院子,道场的香烟依然袅袅传过来。阿小手放在抽屉柄上,想取什么东西,忽身后帘子一动,有谁出现在门口?唬得她从凳子上跳起来,回头:“谁?!”旋即行礼道:“姨奶奶。”
来的正是明月。一般穿了孝服,头上略插几件银器,淡扫了双眉,口脂红得似有若无,格外清婉。她本是勾栏里出身,果然懂得打扮,又且有风韵,怪不得肖少爱呢。
阿小神色有点僵:“姨奶奶玉趾亲临,未知有什么事?”明月还是立在门口,自举手擎着帘子,影子长长拖到阿小脚边来,凝了一凝,“噗哧”笑道:“你要我站着说么?”阿小只得让座,打开箱子取出体己花茶,好好的给泡了一壶,复问她来此何事。
明月端了茶盏,也不喝,笑咪咪看了看阿小,道:“姐姐是女诸葛。先少奶奶门里门外的,都是姐姐一力照应。姐姐有什么不知道的?”
她是客气,赶着阿小叫姐姐。阿小听着就觉得有点发毛。二姑娘身边,确实是阿小出力良多,但明月提这个是什么意思?
想当初,肖少跟娶二姑娘赌咒发誓说“非卿不娶”,他父母却嫌弃君家是商人、不愿答应,二姑娘只管垂泪,是阿小轻闲一声:“非卿不娶?那既然娶不了,怎的还活着?”激得肖少卧床绝食,硬逼家里点了头。二姑娘进门后,公婆冷待,是阿小教她拿金银细软先买通几个得脸的丫头婆子,日子过得容易点。再后来肖少说要纳明月进门,二姑娘闻说这是他做了多年的青楼姑娘,气得卧床,肖老爷召丫头来问道:“少爷少奶奶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当?”更是阿小挺身道:“很妥当。”肖老爷怔一怔:“怎么说?”阿小回道:“婢子随小姐过来,不曾听见小姐说姑爷一句不是,所以知道他很妥当。”肖老爷默然,回头悄跟肖夫人说:“想不到君家主婢倒很有点妇德。我们书香传家,也不能太肆意了,惹人笑话。媳妇虽然到现在没有子息,他房里纳的人,你还是帮帮眼好,别叫他浪着把什么都找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