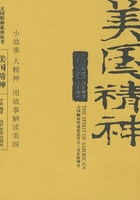——概念与语词
在著名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里,巴尔尼巴比的学者们认为,说出一个词来多多少少会侵蚀肺部,因而提倡废除语词。他们出门随身携带各种实物,见面时各自打开包袱,指点实物进行交际。指点完毕,各自收拾包袱,相互帮助背上,挥手告别。
小说毕竟是小说,如果把它搬到实际生活中来,那有多荒唐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完全取代语词的交际作用。交流思想离不开概念,所谓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是思维的细胞,要靠语词来表达。
概念无臭无味,无轻无重,我们可以理解它,描述它,却无法感知它。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或摸到概念。要把头脑中的概念传达给别人,必须借助于有声的或有形的语词。
语词是表示事物的声音或笔画,这些声音和笔画之所以能表示事物,就是由于人们头脑中有相应的概念。概念与语词相互依存。
有人不理解,说交通警用红绿灯来指挥交通,海上船只用旗语来联络,人们在交际时,点头表示赞成,摇头表示反对,这不说明概念也可以感知吗?
其实,红绿灯、旗语以及点头、摇头所表达的意义还是要通过语词来解释,人们才能够理解。
美国人在公共场合演讲,举起双手与头并排,掌心向着听众,成投降式,是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但是在希腊,这是最侮辱人的手势。印度人的习惯,点头是反对,摇头是赞成。可见,用手势表达思想还得用语词来解释。
鼓掌、吹口哨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可有时候会带来误会。20世纪50年代初,京剧大师程砚秋到抚顺、鞍山演出。在第一场演出当中,台下掌声不断。戏演完后,虽然谢幕10多次,观众仍连连鼓掌,不肯退场。剧场经理赶到后台,对程砚秋说:“事先忘了跟您说了,我们东北时兴便装谢幕。您卸装,换便装吧!”
这位京剧大师没有思想准备,一再说:“我卸装慢,您跟观众解释一下吧!”剧场经理转达后,无奈观众不接受,仍然鼓掌,有人甚至吹起了口哨。
程砚秋误认为让他便装上台,是拿他寻开心,便匆匆卸装,从后台悄然离去。热心的观众认为程砚秋看不起他们,第二天观众骤减,有人买了票也没来。第三天人更少。本来要演10场,却只演了3场,京剧大师郁郁不乐地离去。
美国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到一个小镇演讲,附近许多农民慕名而来。会场里挤满了听众,但马克·吐温发现听众的反应远不如他想象中那般热烈,于是提前结束演讲,从后台快步绕到会场大门外,了解气氛不热烈的原因。
出乎意外,他发现人们在模仿他的话,笑着,议论着。一对远道而来的老夫妇在登上马车启程时,丈夫对妻子说:“他讲得真好笑,我费尽力气,才忍住没笑出声来。”妻子说:“要是忍不住,可就失礼了,人家可是个名人呢!”
大作家长舒一口气,以后他每每谈及此事,总是悔不当初,对不起那些远道而来的乡间听众。
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而语词是概念的表达方式,但它们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古时候,不同的人家贴不同的春联,似有不成文之规矩。人们从门联就大致可猜出户主的身份。“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一定是书香门第;“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门一倒歪之乎”,猜酒家不会错。
有一家的门联很奇特,左右两联都是七个“长”字。过路人围着看热闹,猜不出其中奥妙。这时有个乡下人进城,边看边念,说这一家是卖豆芽的。一问,果然不错。
“长”字,既可读作“生长”的“长”,又可读作“长短”的“长”。“长”还与“常”谐音。这样,上联是“常长,常长,常常长”,下联是“长(zhǎng)得长(cháng)点,长(zhǎng)得长(cháng)点,再长(zhǎng)得长(cháng)点”。这不是发豆芽的又会是什么人家呢?
这副对联的构思利用了一词多义的情况,即同一个语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外交用语”是个多义词。它可以指称外交家们在交谈或行文时实际使用的某种民族语言;也可以用来指称外交界常用的词汇、专门的术语;还有第三种也是最普通的意义,是指被用来表示那种经过谨慎考虑的措辞,这种措辞委婉曲折,对方领会,第三者也懂得,使外交家们能互相谈论尖锐的问题而又不致激怒对方或失礼。
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由于不了解某个语词的多义性而发生误解的情形常有发生。《尹文子》记载,古时郑国人把未经雕琢的玉石称为“璞”,周人把未腌制的鼠肉称为“璞”。由于同名异实,在一次买卖中闹了笑话。周人怀里揣着璞问郑国的商人:“要买璞吗?”郑国的商人说:“要呀!”当周人拿出璞来,郑人一看竟是鼠肉,“因谢不取”,颇有风度地拒绝了对方。
鲁迅先生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曾这样写道:
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人,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予大众语有什么益处呢?
鲁迅先生在这里提到的一词多义的情况,是文化落后的一种表现。我们从中也可悟出一个道理:不同的概念究竟是用同一个语词来表达好呢,还是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好呢?这是没有一定之规的,要看具体的语言环境来决定。
一个多义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它的语义又是确定的,表达确定的概念。
在清朝时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时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都要填相貌册,以防止冒名顶替。有位考官对每位考生都要亲自过过目。有些考生在相貌册上填“微须”,意思是有少量胡须。哪里知道,考官大人把“微”当作“无”解,许多考生因此倒了霉,被当作冒名顶替者被撵出了考场。
有个常熟考生填了“微须”后感到事情很不妙,急忙找文书修改,偏又找不着,到了半夜,只好到剃头铺把胡子刮光。天一亮赶到考场听点。谁知那考官一拍惊堂木:“又来了一个顶替者,册上填明有须,而你却是无须的!”原来他的老相识考场文书已代他将“微须”改作了“有须”。多年苦读,毁于一旦。
另有一位微须的考生不服,与考官争了起来。考官训斥他:“读书人怎么连朱老夫子(朱熹)以‘微’训‘无’都不知道呢?”在明朝,应试者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不可,清袭明规,朱注《四书》成为考试制度中评判高下、决定取舍的标准本。哪想到考生笑着回答:“照你这么说,那么孔子微服而过宋,就是脱得赤膊精光了?”
这一驳,直驳得考官哑口无言。“孔子微服而过宋”,是孟子书上的话。这里的“微”是微贱的意思。“微服”指便服或平民服。古时皇帝微服私访,就是穿了老百姓的衣服暗中访察。由于孟子比朱子更有权威,考官只好吃瘪。
“微”是个多义词,一共有13种用法。词义不同,表达的概念便不同。
概念与语词并非完全一一对应还有第二种情况:不同的语词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
同义词中的等义词,由于其意义完全相同,就是说,其含义与适用对象都完全相同,因而表达同一个概念。等义词往往是借用外语词和方言词的结果。
“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耽误了很多青少年,有人问:“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两位先生是何许人?”其实,“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两个词分别是“科学”与“民主”的代名词。“科学”与“民主”是外来词,根据英语音译过来是“赛因斯”与“德谟克拉西”。“五四”运动前,经梁启超一趣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就风行全国了。
我们现在叫惯了的“青霉素”,这种在抗日战争时期闻名一时的新药叫做“盘尼西林”或“配尼西林”(英语音译)。鲁迅早期杂文里提到过的“虎力拉”,即是现在大家熟知的“霍乱”。“维他命”在当代汉语里早已改为“维生素”。维生素保留了原来音译借词中的第一个汉字“维”,而创造了音义相关的“维生”加上表意的“素”,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意译和音译结合的新词。
在方言中,以不同的方言词表达同一个概念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向日葵”这个概念的方言词就很多。河北唐山叫“口头转”,承德叫“朝阳转”,任丘叫“望天葵”,山东济南叫“朝阳花”,昌乐叫“向阳花”,莒县叫“转日葵”,栖霞叫“转日莲”,湖南邵阳叫“盘头瓜子”,等等。
在同义词中,有一部分具有不同的形象色彩、风格色彩或感情色彩。“母亲”、“妈妈”、“娘”,这三个词的含义及适用对象都完全相同,但是在风格色彩和感情色彩上是有不同的。“母亲”很庄重,多用于书面语。“妈妈”很亲切,是口头语。“娘”则富于地方色彩,也很亲切,常用于口头称呼。这三个词所反映的客观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只在主观运用上有所区别,因此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如果能选用不同的语词去表达同一个概念,那么说话或行文就会更加生动贴切。
在文学语言中,有不少看起来是相反的语词,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概念。例如,“好神气”与“好不神气”;“好快活”与“好不快活”;“好伤心”与“好不伤心”,等等。每一组都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每一组中的后一语词中都有“不”,按本义是表达否定的意思,但是“不”在这里却失去了它的本义,而起到强调语气的作用,“好不神气”就是“好神气”。
大家知道,“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是一种奇谈怪论。照这种逻辑,工人偷产品不算偷,售货员偷商品也不算偷。可有人不这么看,鲁迅小说中一位穷困潦倒的书生孔乙己就说,“窃书”不能算“偷”。他自以为用一个书面语“窃”就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真是可悲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