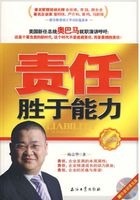话未说完,已被水溶冷笑着打断:“‘什么大不了之事?’,太子难道不知道,名誉对于一个姑娘家来说,到究有多重要?况且除过此法儿,我们就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法子了?非也,只不过是这个法子比较轻松,比较能最快的达到咱们的目的罢了!远的不说,太子若真想离间大皇兄与贾府,何不直接娶个贾府的姑娘回来作侧室?横竖对贾府那样儿人家来说,别说是女儿能高攀上当今太子爷儿作侧室,便是只能做个没有名分的通房,只怕亦是愿意的!”
“你当我没有想过此法儿的?”闻言太子不由激动的反驳道,“问题是将来咱们果真成了事儿,宁荣二府头一个便不能留,到时又该怎么安置明面儿上来说,已成了我太子府之人的贾家姑娘去?而林姑娘就不一样儿,她原非贾家之人,又是六弟你未过门的妻子,将来亦不会有什么麻烦可言,何乐而不为呢?”
又语重心长的道,“我知道六弟你看重林姑娘,林姑娘亦是个举世无双的,可是,咱们毕竟是要作大事之人,作大事者,又岂是能这般拘泥于小节的?只此番原是二哥对林姑娘不住,对你不住,二哥在此,与你诚心诚意的赔个不是了!”说完便深深的鞠下了躬去。
水溶听说,明白太子这一番话儿于理上来说,确是无懈可击,然要于情上来讲,他却是无论如何亦接受不了,因忍不住低吼道:“可是无论怎样,你们都不能这般逼迫伤害玉儿,还意图一直欺瞒着我才是!”
太子亦忍不住低吼道:“难道六弟你忘记小时候咱们过的什么日子了?还是六弟你想重蹈以前的覆辙?可是你就没有想过,倘此番咱们败了,别说咱们的身家性命保不住,便是林姑娘,亦极有可能会因此受到牵连?难道你就不想保护她吗?惟今之计,咱们除了主动出击,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子吗?”
伴随着太子的话音落下,水溶的眼前攸地浮现过当年幼小的自己是如何孤寂的留在自己已故母妃的宫殿里忍饥挨饿;如何的被其余有母妃的皇子帝姬们恣意嘲笑谩骂,甚至欺凌毒打;又是如何的骂自己及之后同样儿亦没了娘的太子‘没娘的孩子’;及至到他二人有了足够的能力和权势将他们一一踩倒在地后,他们又是如何转化了嘴脸,立时来巴结于他们……等等诸多情景,旋即他的心便止不住狠狠的抽痛起来,“成者为王败为寇”这句话儿,他还体会得不够多吗?!将来若是事成了倒还罢,一旦失败,难道真要让黛玉将来亦跟着成为了“寇”的自己,一块儿吃苦甚至赔上性命去?倒不如趁早儿抽身儿离去罢!
又思及自己沉浮尔虞我诈的朝堂斗争这么几年,亦非没作过那伤天害理之事,此番若不是攸关黛玉攸关自己,只怕他早已比太子还要做得过分了,又还有什么脸面指责太子去呢?
只是,终究还是不能原谅太子利用了黛玉,利用了他对他的信任,因惨然一笑,道:“事已至此,说再多指责太子的话儿,亦没有办法挽回了,臣也不想再白费口舌,只请太子此番不要再遣人寻玉儿去,并想法子让贾府的人亦不寻玉儿去,更不要寻我去,留给咱们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空间罢。若是太子能做到,臣必定感激一辈子!”
一席话儿说得太子面色惨白,摇摇欲坠,半日方颤抖着声音道:“六弟这么说,是打算不要我这个二哥,是打算只丢下我一个人,在这个尔虞我诈、吃人不吐骨头的朝堂宫廷中,孤军奋战了吗?”太子是见识过自己这个弟弟无情起来时是有多无情的,然同时亦知道,他这般无情之人,又恰是那最重情之人,一旦对谁动了情,便是一生一世、那人是好是坏都极难再改变的,如今既见他这般决绝,遂打起二人同舟共济十几载的兄弟情这张牌来。
果见水溶迟疑了片刻,却仍是既不点头,亦不摇头,只是狠下心肠闭上眼睛颤声儿道:“如今事情已算是成功了一多半儿,只要太子爷继续按计划行事,当可以万无一失,有没有臣在,又有何干系?太子爷就高抬贵手,放水溶这一码罢。”说完睁开眼睛,甩开袖子大步便往外走去。他怕自己再多停留片刻,又会止不住心软了。至于他要求太子不要再去寻他与黛玉之事,以他对太子的了解,在他将话儿说到这般决绝以后,太子当是不会再为难他们的了!
不想还未行至门边儿,就听得太子在后面儿略带着哭腔又急又快的道:“六弟竟忘记母后薨逝前,曾再四叮嘱过的要咱们兄弟二人‘相亲相爱、不离不弃一辈子’的吗?果真此番咱们兄弟就此分开,母后在天上瞧见了,不定伤心成什么样儿,你就当真那么忍心吗?!”
听得太子提及已故的皇后,那个曾给了他无限温暖,无限关爱,甚至可以算得上给了他二次生命的人,水溶心里攸地大恸,腿也跟着再迈不动,身后的人是皇后惟一的儿子,是打小儿待他恩重如山的二哥啊,他真要这般决绝的弃他而去吗?可是若不解决好这些尘世俗事,他又该以何颜面,再去打动黛玉呢?
又听太子在后面凄声儿道:“六弟你便是不看咱们兄弟同舟共济这十几年以来的感情,也请你瞧在天上母后的份儿上,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啊!”说完几步小跑至水溶跟前儿,缓缓向他张开了双臂。
此情此境,让水溶攸地忆起在皇后薨逝后的头两年间,每每兄弟二人在外面儿受了谁的欺凌,或是其中一个惹了另一个不高兴后,都会在事后向彼此张开双臂,然后紧紧拥抱在一起,彼此鼓励打气或是求得彼此谅解,随后再更坚强更勇敢的去面对下一次的欺凌!
随着兄弟二人的渐渐长大以及越变越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个动作,甚至久到水溶都要忘记他们约定的这个动作背后的含义了,如今既见太子忽然这般做,他心底最深处那根儿弦,终于被触动,忍不住亦缓缓抬起手,向着太子作了那个拥抱的举动。
太子见状,大喜过望,大跨一步,便要拥住水溶,却见水溶在自己即将拥过他的那一刹那,攸地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同时后退了一大步!他不由怔住了,似是不敢相信都到这一步了,水溶仍是拒绝自己一般。
正发怔之际,却听水溶饱含痛苦的声音道:“二哥,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这般轻易的便原谅你,原谅你枉顾我们兄弟十几年的感情,利用玉儿,欺骗与我!你理解那种‘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的感觉吗?”
说完不顾太子同样儿满脸的痛苦扭曲神色,他径自大踏步出去了,临到门口,又快速扔下一句:“待我考虑清楚,自会回来给二哥一个说法儿的!”便凌空跃去,眨眼消失在了浓浓的夜色中。
余下太子一人,直直盯着外面儿看了半日,心里到底不若方才那般没有底儿了,至少水溶又唤他“二哥”,而非“太子”了,那就说明,他潜意识里已经原谅了他,只是心里终究还接受不了顾了他这个‘此’,便不好去面对黛玉那个‘彼’罢了!没关系,这点子时间,他还等得起……
水溶回至林家的院子,已是半夜时分。白日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儿,让他只觉身体和心灵都说不出的疲惫,然脑子里却又是说不出的清醒,以致他躺到床上辗转反侧大半晌,竟是不能入睡。烦闷急躁之下,他索性不再强迫自己入睡,而是命人拿了一坛酒来,便跃至房顶,平躺其上,一面望着漆黑浩瀚的夜空,一面大口大口的灌起酒来,以期能让自己暂时的忘记痛苦。
然他原就内力深厚,一坛酒喝光,除却眼前不时浮现过黛玉的一颦一笑,竟是越发的清醒了。他不由扯唇苦笑了一下儿,想要暂时忘记痛苦,果真的就这般难?看来他喝的还远远不够多,至少需得再喝上三二坛才行。
翻身猛地坐起,又猛地站起身来,方才还一片清明的脑子,被一阵自下而上猛地窜起的酒意一袭,竟觉着昏昏沉沉起来,连带眼前的景物亦有些儿个模糊不清了。水溶心知自己已有了三五分醉意,禁不住自嘲一笑,看来想醉一场,亦算不上多难嘛,顶多再喝上一坛酒,也就罢了。遂抬起脚,欲行至屋檐前,以便跃进院子里再拿酒去。
适逢一阵凉风吹过,水溶冷不丁儿打了一股寒战,酒意亦越发沉了几分,竟致一脚踩空,摔倒在了屋顶上,身不由己的便往下急速滚去。练武人的本能,让他在摔倒的那一瞬,便反应了过来,立时欲反手重拍房顶以借力,然下一瞬,想着或许这一摔能将自己摔得人事不省,暂时忘记一切烦恼,他又自动放弃了,旋即还闭上眼睛,期待起落地那一瞬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