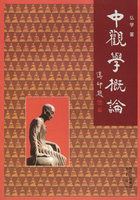一、世界及我为常耶?二、世界及我为无常耶?三、世界及我为亦有常亦无常耶?四、世界及我为非有常非无常耶?五、世界及我为有边耶?六、世界及我为无边耶?七、世界及我为亦有边亦无边耶?八、世界及我为非有边非无边耶?九、死后有神去耶?十、死后无神去耶?十一、死后亦有神去亦非无神去耶?十二、死后亦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耶?十三、后世是身是神耶?十四、身异神异耶?
释迦答:“无此事实,故不答。诸法有常无此理,诸法断亦无此理……譬如人问?牛角得几汁之乳,是为非问,不可答也。”
孔子则回答得更干脆:“不知生焉知死。”
“东方文化”堵死了一切玄学之门,也堵死了一切宗教神秘之门,也否定了超自然的造物主。
我们十分欣赏南老在《金刚经说什么?》一书中对宗教神秘主义的否定。
翻开一部《楞严经》,七次征心,八还辨见,实是把一个“知”字说透了。 西方古典文论绝无此精美的篇章。
孔子的表达简短得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是知,承认“不知”,也是一种“知”。任何“知”不仅以“不知”为前提,而且其中都包含无量的“不知”。任何“不知”,首先是由于有“知”, 绝然无知,不可说“知”,也无法说“不知”。“知”与“不知”高度统一的“知”,才是真知。
大德至善的“宇宙—生命”系统,时而涟漪荡荡,时而浪花四起。这里浊浪排空,那里莺歌燕舞,美、丑、善、恶、真、假、祸、福……到底是什么?左浪推右浪,前浪阻后浪,从来都是一个连一个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结构,一个组合接一个组合。
佛家将他称之为“帝网珠”。运动着、变化着、普遍联系的“帝网珠”。
在这样的文化中,想为宗教神秘主义找到一个立脚之地,实在太难了。
《道德经》几乎是竭尽全力描写这个“帝网珠”活剧的千姿百态。有人说《道德经》是一部兵书,未必没有道理,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力与力交接的永不停息的活剧。
这便是东方文化的大思维。
这个大思维永不拒绝一切现代,因为现代是你拒绝不了的。
这个大思维,永不迷恋一切过去,因为过去你也迷恋不了。
这个大思维,永远乐观瞻视未来,因为“宇宙—生命”系统失不去什么。
这个大思维,不给造物主以地位。
这个大思维,不给垄断者以地位。
这个大思维只崇拜“宇宙—生命”系统本体自身的“本愿”。“本愿”也无愿,只是历史的“矢星”。
我真不相信,这样的大思维与什么文化有抵触,容纳不了什么。
东方文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自己走入了“误区”?
我也奉劝一切唯物主义者,东方文化不是你的异类,可能比你更彻底。
东方文化永远给“不知”留有地位。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并非是相信鬼神的实有性,而是给“不知”留了一个地位,对于“不知”冠一个“鬼神”的名字,有何不可?“子不语怪力乱神”也说明了孔子忠于自己的学说。“怪力乱神”这些词既然传之甚远,不必贸然否定,但他是“未知”,更不可肯定,暂且存疑也没有什么坏处。
如果多读几遍《道德经》、《庄子》,你会发现“鬼”“神”之类的概念的人间意义。
佛学就复杂得多了。
早在佛学产生之前,中国文化已经从原始神秘的巫术宗教文化中走了出来。中国人用“仁”、“义”、“礼”这些人间概念来论天说地,就是一个明证。孔子的“仁”作为一个范畴,是直指“宇宙—生命”大系统本体的,当然也包含人本身的道德。在孔子那里,“宇宙—生命”系统与个体人的生命活动是不可分的,不过是在表述时有时偏于本体,有时偏于个体。读《论语》等作品时,要细细辨认。朱熹把二者绝对同一,把“仁”“义”之类作为人必须遵循的道德,是孔子学说的庸俗化。若人真有什么需要永恒遵守的东西,天就不是“仁”,而是“不仁”了。 孔子绝不犯这种诬天的错误。
释迦诞生的时代,印度婆罗门教达到了鼎盛期,当时的印度没有其他文化,也没有其他文化符号。释迦牟尼不能不完全利用当时现行的文化符号,包括表述方法。今人读佛经,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是会出现误会的。
也和孔子一样,释迦也给“不知”留下了更广阔的地位。
在释迦那里,生命的存在形式太宽泛了,根本不单指人、动植物、鬼、神、佛、菩萨……可以说一切存在方式,在释迦牟尼那里都是生命存在方式。 《金刚经》中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实是包括了一切宇宙的存在方式,这一切方式是宇宙的存在方式也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孔子、老子大致一样, “宇宙”、“生命”这两个概念在东方文化中是不能分家的,说宇宙时,便是在说生命;说生命时就是在说宇宙。南老在解释这一段文字时,把小乘佛教练功夫的“四禅八定”引进去了,在南老的眼中,释迦这段文字,无处不是指的“功夫”境界而言,这便差之千里了。
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非人也非神,准确地说只是体之用。佛经中的大量佛、菩萨、天人……大半是“体”之用。如果是中国古人写佛经,用当时中国文化的概念,当是“仁”、“义”、“礼”、“智”、“信”之类。在佛经中,说是某某来会,有的说的是真人,有的则是用名号提示该经内涵外延的意义的。
举一个较易说明的例子,佛教有“七古佛”之说,丁福保指责禅宗的七古佛名号、偈语是伪造的,他也列了七位古佛,似乎他列的是实有之佛。其实,禅宗的发挥是正确的。七古佛的名号及偈语实指的是在释迦成就之前,即建立佛学前,“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必有七步发展过程,不然“宇宙—生命”系统不会发展到产生释迦这样的人物。至于七位古佛是文明的进步层次,还是实有其人修炼成了佛?这在佛学中没有重要差别。
也许是由于古典作家给“不知”留下了地位,后世的儒、道、释三家一直没有能彻底与宗教神秘主义一刀两断,有的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道家与道教的区别是人所共知的。禅宗中许多大佬一直企图令佛教从神秘主义中走出来,但从今天的情况看,效果并不明显。奇怪的是儒家,晚期也出现了“儒教”的提法,这怕是大儒们太羡慕和尚道士在民间的地位了。民国以来,“儒教”的呼声日高,怕是想以孔子为旗帜组成一个政治派别吧!
目前,儒、道、释三家的现实状态,不是笔者议论的重点,但凡是一个明眼人是会作出清楚的判断的。
如果想概括一下,我以为可利用“三神化”这个概念,说明“东方文化”的现状。
一曰:宗教神学化。这在儒家的早期,董仲舒是个典型,他把孔子的“天命说”完全神化了。正如上文所说,孔子为了给“不知”以地位,对鬼神存疑,而董仲舒又借天人感应说,把神鬼偷运进儒家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
“天人感应”说如果是从“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的因缘运动入手,说明人心对本体的感应作用,正好破除神秘主义,对于刚从原始宗教神秘中走出来的人类,应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董仲舒把“天”说成了完全决定的东西,人莫过是刍狗,这就大谬不然了。“天人感应说”实在是割裂了天人一体关系的神学目的论。
类似这样的,将“东方文化”神学化的东西还很多,利用《易》作文章的最多。宋儒的世界模式图,也迹近神学目的论。
在佛教中这个问题便更严重了。
“净土”学说是佛学区别于儒、道的重要学说,也可以说是佛学中最深刻的东西,可到近现代又成了什么呢?
当代一些人解《佛说阿弥陀经》中“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一句,是这么说的:“过十万亿佛土”即“飞过十万亿个银河系,那里有一个世界( 星球或其他的什么)叫西方极乐世界。那里有一个佛,叫‘阿弥陀’,现正在说法。 "只要人们每日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临终之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就会把他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
这与基督教的“天堂”说何异?多的只是借用“银河系”这样的现代科学名词装潢了一下门面。
南老当然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老人家对所谓“持名念佛”有新解,说是要引入“止住”概念,从而使念佛进入“定境”。南老是大家,修行上有成就,我辈不敢妄加议论。但用“止住”,念到“一心不乱”,忘了自己、忘了身体、忘了一切境况……与佛学的“净土”学说真是相应吗?不管如何说,南老的说法比上述我们引的一些大法师的观点是要强得多,起码南老不太同意把阿弥陀佛理解为彼岸之佛,这对破除神秘主义是有好处的。南老大半是想把净土说引出神学化的迷宫。
“过十万亿佛土”的本解应是“超越无量众生心”,佛土者,众生心也。“十万亿”表无量。“过”者,“超越”。即是说在一切众生思虑不到的“地方”,有一个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事实上是“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未来发展的理想境界。“西方”者终极之义也,并非真是说地球以西。早在唐代,慧能大师就破过这个疑。“净土说”还是佛学的“就地还家”说,还是从属于佛家的“缘起性空”的根本理论的。如果真如那些大师们解释的“净土观”,那我们上边提到的释迦本人确立的“十四不正问”原则就不对了。人死后,肉体留在了地球,那是什么东西到了西方?是灵魂吗?佛家断然否定灵魂说,释迦拒绝回答死后为何的问题。既然不承认灵魂实有,那阿弥陀佛接走了我们什么?这个东西的重量、质量如何?阿弥陀佛怎样飞越十万亿银河系?
佛学的正确观念在这里成了神话了。
本文不可能详解“净土说”,但佛学不会编造如此神话。东方文化与神秘主义无缘。
二曰:神圣道德化。最典型的是朱熹的“理学”。
这个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孔子学说的庸俗化。正如前文所说,孔子的主要出发点是“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即孔子所说的“天”的本性是“仁”是至德。至德之用,则为“义”、“智”、“礼”。后人多加了一个“信”。上天的“仁”中包含了“义、智、礼”诸用,对于受益者来说,应该尽可能接近这种“天德”,但不可能完全达到,也不用强制达到。因为“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社会生活中是求“和”不是求“同”。“礼”在形而上层次上说就是和谐、合和、中庸。
“克己复礼为仁”。
“克”的本义包含朱熹所说的“克制”义,但主要不是“克制”,而是“完成”、“完善”义。“复礼”者,即与社会归复于“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充分完成自我,又与社会保持和谐。在实现自我的基础上也承认别人实现自我的权利,这一切对于“天”来说,就是“天”的至德——“仁”。天的“仁”,正是承认一切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但不是消极的,“君子”——明了道的人,知天命的人,要积极向天之至德靠拢。我们以为这应是孔子的本意。这个本意与“道”、“佛”两家是基本相通的,构成东方文化的根本骨架。我们称东方文化为大思维,就在于东方文化三家的基本学说,都是从“天”、“道”、“佛”的法身本体来说话的。
后人不明白这一点,希望把本属于法身本体即“宇宙—生命”系统整体的德行强加给个体生命的人,这样就把一切都颠倒了。理学的根本失误就在这里。“宇宙—生命”本有的至德, 都被朱熹们曲解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律令。 这才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荒唐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