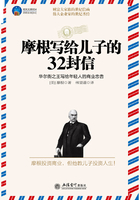此时他已达到了毕生的夙愿。他抓住了欢乐。但是,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有时还是会徘徊于往昔的伤痛的暗夜,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亦充满着诡异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1824年9月17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贝多芬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意死亡将我带走,因为我还欠他很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须让精灵启示着我而要我完成我的艺术东西以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见贝多芬书信集第22页。《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诗人原作讲述一个骑士恋上一个女神而被她囚禁,他思恋家乡与自由,这首诗和瓦格纳的名剧《汤豪舍》颇为相似,贝多芬在1823至1826年间从事此工作。、为克尔纳的《奥德赛》所作的曲子、根据歌德的《浮士德》谱的曲子贝多芬从1808年起就想为《浮士德》谱写曲子,这是他人生最重视的规划之一。以及清唱剧《大卫与扫罗》,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向往着德国古典大师的恬美境地,如巴赫与亨德尔,并且,他尤其倾向于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或者他魂牵梦萦的意大利贝多芬在日记中写道:“法国南部!是啊!是啊!”“离开这里,只要你能做成这一件事,你便能重登艺术的高峰。……写一部交响曲,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天,为了旅费而工作,然后周游意大利,西西里,和别的艺术家一起……”。1826年,施密特医生见过他,说他气色红润并且朝气勃发。同年,当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他时,贝多芬反而还鼓励这位颓废的诗人说:“啊,要是我能有你千分之一体力和魄力,那该有多好啊!”时事艰难,专制反动的政权横行,思想界也被狠狠地钳制压迫着。格里尔巴泽哀叹道:“言论审查制度将我戕害了。倘若一个人想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前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可以被禁锢的,但幸运的是,自由之声还没有熄灭。”贝多芬正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他是德国思想界硕果仅存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那就是把他的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赐予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怯懦。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强壮的心灵鞭策着这些可怜的人们。”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可以发表自由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肆无忌惮。警察当局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将他的批评和责难看成无害的痴言梦语,因此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可以平安无事。”1819年他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公开宣称:“归根结蒂,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犹太人。”那时他正写着《D调弥撒曲》。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宗教观念极其自由的人。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的毫无顾忌,可以很大胆地抨击他的政府腐败。他特别指责这样几件事情:法院趋炎附势且独断专行,程序繁琐,妨碍司法公正;经常滥用职权;官僚腐化而又无能;颓靡的贵族享有特权,霸占着国家最高的职位。从1815年开始,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国的。据辛德勒说,他非常热烈地读着英国国会的记录。1817年英国的乐队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到达维也纳,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的字眼痛骂奥国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他说英国人的脑袋的确还长在肩膀上。”(1814年拿破仑失败,列强举行维也纳会议,重新瓜分了欧洲。奥国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颇有只手遮天之势。对内奉行压迫之政策,毫无言论自由。当时欧洲各国皆趋于反动统治,虐害共和党人。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弥漫全欧,蠢蠢欲动。从1820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接踵而至,随后1830年法国又有七月革命,1848年又有二月革命……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1814到1830年之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读者读到此地,必须参考当时国际形势,才能对贝多芬本人的思想有比较准确的认识。)
所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卑躬屈膝。这个时期,他似乎开始玩弄痛苦了。在他晚年,虽然环境依然恶劣(比如侄子的自杀事件),但此段时期所创作的音乐,却呈现一幅崭新的面貌,它嘲弄着一切,睥睨着一切,鄙视和不屑着一切,同时,他也是欢乐的。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即他逝世的前四个月,他完成了第一百三十号作品,即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曲。那是非常轻松欢快的,但这种快乐并不是一般人常有的那种快乐,它时而是莫舍雷斯所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疼痛之后的拈花一笑。不管怎么样,他是胜利者。他不相信死亡。
然而死神还是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底,他患了感冒,随之病情加剧转为了胸膜炎。此时是隆冬时节,他在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归来,病倒在了维也纳。朋友们远在天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但是据说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竟然忘记了这个重要的使命,两天之后才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了,况且治疗的又不细致。他钢铁般的运动员似的体魄同病魔抗争了三个月。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心爱的侄儿立为了正式的继承人。他思念莱茵河畔的挚爱友人,他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说说话儿啊!但我身体太虚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申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洛申即为韦格勒夫人——这是对埃莱奥诺雷的亲密称呼)如果不是几个仗义的英国朋友,贫苦的阴影几乎要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有耐心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说他看见最后一次病中的贝多芬,觉得他心境宁静,慈祥豁达至极。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的弥留之际,在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贝多芬躺在床上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着大概一切事情都是善恶相伴吧,也许厄运也伴着善意据格哈得·冯·布罗伊宁的信,说他临死时还受着臭虫的骚扰。他的四次手术时间分别是1826年12月20日,1827年1月8日、2月2日和2月27日。”
这个善意,便是解脱,正如像他临终时所说的:“是喜剧的终章。”而我们却说这是他一生悲剧的剧终。
在大风雨中,在一场疾风骤雨的高潮中,在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中,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这个陌生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尔姆·西顿布伦纳。布罗伊宁写道:“感谢上帝!感谢他结束了这长久悲惨的苦难。”贝多芬的手稿、书籍、家具,全部拍卖掉,代价不过175弗洛令。拍卖目录上登记着252件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共售982弗洛令。而谈话手册只售1弗洛令零20。时间是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贝多芬!有多少人赞颂歌唱过他在艺术上的伟大!但他绝非仅仅只是音乐家中的领军人物,而是近代艺术史上最坚实勇敢的力量。对于那些受着苦难受着挫折的人来说,他是最伟大最亲密的朋友。当我们对这世界的苦难感到疼痛和忧伤时,他会来到我们身边,犹如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身边,深深缄默着,在用他的钢琴唱着他隐忍的哀歌,安慰那些哭泣的人。当我们因为和庸俗无知、道德缺失等丑恶现象斗争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就可以到他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就可以收获到无穷尽的能量。他馈赠给我们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欢乐他在致“不朽的爱人”信中写道:“当我有困难可以对抗时,我总是快乐的。”而在1801年11月16日写给韦格勒信中又称:“我愿活上千百次……我注定不能过恬静的日子。”、一种与上帝同在的迷醉之意。似乎在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感应中辛德勒曾经说道:“贝多芬教给我大自然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给我的指导和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区别。使他陶醉的自然的规律,是自然的基本威力。”,他竟获得了大自然深邃而又无穷的力量。格里尔巴泽对贝多芬是又害怕又钦佩,他在提及贝多芬时说:“他所到达的境界层次,是艺术居然和诡异、野性融合为一。”舒曼评价他的《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但它对你的影响始终如影随形,犹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但总是让人充满恐惧与惊奇。”他的挚友辛德勒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灵魂。”的确,贝多芬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他这种原始的力量在和大自然其他部分碰撞之后,便迸发了荷马史诗般的精彩火花。
他的人生宛如一个雷雨天。最初是一个平静如水的早晨,吹过几丝懒洋洋的风。但在这静止的空气中,早就有一股隐隐的威胁和沉闷的气息。然后,突然而至的阴霾涌过,电闪雷鸣,这是充满着吼声的恐怖沉默,一阵又一阵的狂风呼啸,这就是《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尽管如此,白日的清灵之气没有被污染。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中永存着一缕希望。但是,一八一〇年后,心灵的天平歪斜了。光线变样了。明镜台般的心灵仿佛也惹上了尘埃,这尘埃飘忽而起,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们像又诡异又变幻的骚动,将心灵笼罩。音乐的灵感在这层薄烟之中沉浮,这样一两次后,又完全消失了,湮灭了,直到曲终才会狂飙突进般地出现。甚至快乐本身也被蒙上苦涩与狂野的烟尘。所有的情绪都蕴含着一种悲苦,一种狂热,一种毒素贝多芬在1810年5月2日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噢,人生多美,但我的却永远受着毒害……”。夜幕降临了,雷雨开始酝酿。随后是蓄涵着雷电的厚重的乌云,将夜染成了墨汁般的成色,暴风雨即将呼啸而来,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在这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被撕裂了,暗夜被坚强的意志给赶走了,还给天地之间一片太平。
这是多么华丽的征服啊!还有什么胜利能够和之比拟呢?拿破仑哪一场战争可以与之作比?奥斯特利茨哪天的阳光能有这种无上的光芒耀眼吗?谁在心灵上获得过这样的凯旋?一个承受苦难的不幸者,他贫穷、残废而又孤独,他被痛苦铸就,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凝成欢乐,可以用他自己的豪言壮语概括他的一生,这句话也是一切拥有力量的勇士的箴言:
“用痛苦来兑换欢乐。”——一八一五年十月十日贝多芬写给埃尔德迪伯爵夫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