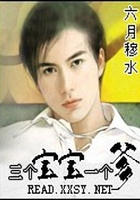对面的冰男人寒眸聚拢,从牙缝中挤出,“仇烈!”
仇烈?仇字还不够,还跟了个烈,烈火汹?,怨气冲天?雪枫心里嘀咕着,冰坨子苦大出身的样子简直像是在怨恨缸里泡过,皮肉,骨头,就连血液都是冷的,那份怨恨连同霸势从骨子里悄无声息的渗出。
门外的躁动扰了雪枫兴质,侧过身寻声看去。
“我的爷,您前天不是查过了吗,怎么又……”
“兔崽子,你以为爷整天吃饱了没事干啊,光查有个屁用,一天查不到人,谁都别想安生,大人说了,别说是舅爷的店,就算是他亲爹开的铺子也得查清楚,别到时候让那些人搜出来,都得他娘的玩蛋。”
“真这么吓人?”
“兔崽子,哪天爷带你进大牢里溜一圈,保准吓死你,那些人,个老子的,真他娘的心狠手毒的,凡是能活着出来的跟扒了皮似的,剩下的那些倒霉蛋都……咔嚓,赶紧赶紧,把簿子拿来,老子一一对人。”
被衙头这么一吓唬,机灵的伙计哪难怠慢,大掌柜已将簿子双手奉了上来,东家不在,他们还是随了衙头的心思好。
一队人上了二楼,一队人去了后院,余下对厅里用餐的逐个验查。
真他娘的邪门,衙役门二话不说直接将人拖起来,验腿。
验够了腿,再量身段,知道的是衙役在搜什么人,不知的还以为富足的郡阳好客,要给客人量身制衣呢。
“凡是罗圈腿、矮个子的,全给爷带回去,胆敢拒捕,爷手里大刀可不是吃素的。”衙头嚷嚷着,也没闲着,带人朝楼梯左侧的那张红木桌奔去。
袁山朝袁木使了个眼色,未等衙头靠近,袁木主动迎了上去,满脸恭敬的朝衙头抱拳施礼。衙头何许人啊,那可是郡首身边见过大世面的红人,就凭衙头的眼力,他们这桌人就跟各位爷要搜的人不沾边。
衙头扒开袁木,指着个头娇小的雪枫,哼笑道,“那可不好说,你们几天是不沾边,这小子到像的很。”
“嘿嘿……”嘿笑间,袁木自袖袋中掏出一包硬硬的东西,塞进了衙头怀里,“爷,您见过细皮嫩肉的偷儿吗,那小公子年级尚浅,手不能拿,肩不能挑的,也是不沾边,您说呢?”
衙头咂吧咂嘴,抻着脖子把雪枫看了再看,“到也是,还是个孩子吗,替爷盯着点儿,遇到罗圈腿赶紧禀报爷,郡首大人重赏。”
“是是,爷放心。爷,小的斗胆问一句,昨晚那些凶神恶刹黑衣人,哪有爷面善啊!”袁木突生怯意的问道。
衙头似被踩到痛脚般,瞪着大眼警告袁木,晚上没事少出门,落那些人手里,没个活。
“爷,他们到底什么人啊,想咱郡阳城在郡首大人的英明下,那真是过着神仙般的好日啊,怎么那些人一来,死气就来了……”
“娘的,活腻了。”
“是是,小的一时替爷您气怒,那些人骂骂咧咧的,太不把爷您放眼里了。”袁木奉承着,惹得衙头恶狠狠的重哼。
“个老子的,一群狗日的王八蛋,仗着势大简直把郡首府当成上将府的后菜园子了,想踩哪儿就踩哪儿,想骂谁就骂谁……”
上将军府?将军重任意在守疆卫土,那个皇亲国戚的手是不是伸的太长了,南郡有郡首,有守疆大将军,几时轮得到他一个京官如此操心费力,仅为了一偷儿?这件事镇南将军楚魁雄一定知道细枝末节。
雪枫拎起吃食袋子,“师兄!”天易微点头,两人近乎同时起身。
“站住!”
冰冷的声音绊住了雪枫,转身朝仇烈挤眉弄眼道,“想讹钱不成?”
“讹钱?”仇烈声音低沉的重复着,待再次举目看来,骨子里渗出来的冷收敛几分,“你可是从福源……”
“个老子的,抓红眼了,要的是罗圈腿,你给老子弄个瘸子做甚?”衙头大骂着,因为衙役从后院绑了个一走一瘸的汉子出来。
“枫儿!”天易叫道。
“来了,姓仇的,咱们后会有期啊!”
俊影不见,曾坐过的位置残留淡淡山草香,枫?还是峰?此枫儿会是当初讹他的那个混人儿吗?怎会这般凑巧,此人额头亦有颗圆润红痣,却已认不出今日仇烈,就是当初那个上邪烈。十年,圣山一别,整整十年啊,十年光阴竟会如此折磨人心,变的何止相貌,心已死,有何必让他记得呢。
“酒!”清冷的声音沉沉的说道。
袁木刚要劝解,却被袁山扯住,摇头暗示,主子心思别人不懂,他们怎能不懂,那俊美的红痣少年,定是让主子忆起当年。十年间,他们主仆三人已非往夕,有的只是天差地别。
飘香的米酒灌入腹肠,一碗接着一碗,心不醉,人无言。
天易驾车朝着记忆中的北街前行,雪枫亦然倚着车门懒散的坐着。
“师兄可觉得那三个人面善?”雪枫随意的问着。
雪枫不问,天易永远不会将外人放在心上,即便那两个侍卫模样的人确是面熟的很。
“哈哈……”雪枫莫明其妙的笑了起来。
“笑什么?”天易问道。
“笑那个仇烈啊,头一次有人不看我的脸,专盯着我额头红痣看。若不是看那两个侍卫脸熟,打死我都不会跟他扯连上,十年而已,竟然将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师兄,郡阳还真是热闹啊。”
“枫儿为何不问问他是不是被你讹过的小皇子?”
“嘿嘿,师傅可说了,出门在外凡事不能冒尖,箭射领头鸟。被讹的都不招惹我,我何必上赶子套近乎,哼,他爹还欠着我呢。”
千叶雪枫打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吃亏,更不受世间那些个道德理的束缚,不单单因为师傅疼他宠他,实乃他家师傅的看世之道,怪不得百多岁的人了,还没彻底修成仙身,就是让教徒无方给耽误了。有仇不报,那是无能之辈。
“我总觉得那个仇烈跟我会扯连不清?”雪枫自言自语道。
“为何如此说?”
“不知道,只是感觉,编个什么姓不好,偏用仇。师兄,你觉得仇烈眼里有什么?”
天易想都未想,直截了当回道,“仇!恨!整个人好似在寒潭中泡过一般。”
雪枫微点头,不知他跟哪个有仇?又能跟哪个又恨?
“主子,别喝了,奴才追去问……”
“问什么?问问他是不是福源镇的雪枫,是不是圣山中救我们性命的雪枫?哈,如果是呢,我该如何跟其说天论地,如果那幅伶牙俐齿问我境况,问起……问起他的姨姨,我又该如何做答?不认也罢,世上路人如此多,不在乎多他一人。”话落,杯起,清凉的米酒被仰首灌入腹中,待上邪烈再次睁开眼,丝丝混钝荡然无存,“此事绝不能再拖,今晚我要夜探郡首府,如其大海捞针,不如坐享其成……”
黑夜降临,“仙客来”临街的天字一号房中漆黑一片,窗敞开着,皎月银光映出窗前高大身影。
天黑了,鸟儿会回归山林,远处民宅灯光隐耀,上邪烈想像着里面融融暖意,而他这里不但清冷孤寂,又该归于何方?家,随着疼爱他的那个人逝去而逝去,他灵魂深处的伤,只有在黑夜降临时独自舔食。
遥望黑夜的远方,嘴角露出浅浅的笑,能望透冷月,却望不透自己的心,多久不曾有过的黯然神伤,却在今夜涌动而出,他竟然后悔未与雪枫相认,他是路过?还是到此投亲?深遂黑眸望的更远,试图寻找、猜测此时此刻那人会身在何处。就算认不出他,也认不出袁山袁木吗?或许,雪枫与他所想不尽相同,擦肩而过的路人何止几千几万,他们,不过沧海一粟。
房门被轻敲三下,吱嚓声中,袁山袁木走了进来。
“主子,时辰到了!”袁山恭敬的提醒着。
月光镀照下,上邪烈如斧凿刀刻般棱角分明的脸尤显冰冷毅然,没有回应,举步离开窗前。
“主子,如果东西到手了,咱们要回京面圣禀明一切?”袁木小声问道。
上邪烈冷笑道,“我们可是违抗圣意,私逃皇陵之人,京里那人金口一开,我们便是大逆之罪,再加上陷害皇亲,造谣生事,有人会给我们机会禀明一切吗?如此回京,就算不死,已无翻身之力。东西,我一定要弄到手,皇城?总有一天我要回去,那里的血,还没洗刷干净呢。”
话落,高大的身影走出漆黑的房,袁山袁木追随。
云纱笼月,望月之人何止上邪烈。
楚将军府华灯耀动,处处扬逸着喜悦,慈母盼儿十余载,今日终见爱子,那双擒着泪花的眼深深触动了雪枫心弦。如果,只是如果,师兄换成他,师兄的娘亲换成他千叶雪枫的娘亲,他一定会扑进娘亲怀中,紧紧抱着娘亲,告诉她,她的枫儿回来了,他的枫儿长大了。他定要好好看看娘亲,好好抱抱娘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