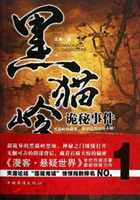阿希礼信步从斯佳丽和查尔斯坐着的地方走过,脸上露出若有所思、暗自高兴的笑容。
“真是太狂妄了,不是吗?”他目送着巴特勒说,“他看上去就像手腕毒辣的政治家鲍奇亚家族的人。”
斯佳丽赶忙想了一下,可想不起县里、亚特兰大或萨凡纳有姓鲍奇亚的人家。
“我倒没听说过这家人家。他跟他们是亲戚吗?他们是什么人?”
查尔斯露出一副怪相,心里有一种既奇怪又羞愧的感觉正在跟爱情搏斗呢。结果还是爱情胜利了,因为他认识到女孩子只要温柔、可爱、漂亮就够了,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无妨,于是他赶紧回答:“鲍奇亚家是意大利人。”
“哦,”斯佳丽听他这么一说兴趣顿减,“原来是外国人啊。”
她对阿希礼甜甜一笑,但不知怎的他的目光没朝着她。他正望着查尔斯,露出既理解又怜悯的神情。
斯佳丽站在楼梯口,小心地从栏杆上朝下面的过道张望。过道里空空荡荡。从楼上的卧室里传来嗡嗡不绝的低语声,时起时伏,还夹杂着叽叽喳喳的笑声。听见有人说,“得,你这话当真!”又有人说,“后来他怎么说来着?”六大间卧室的床和长沙发上躺满了姑娘,大家脱了衣服,解开胸衣,披散开头发,正在休息。乡下本来就有睡午觉的习惯,要参加全天的宴会,从大清早开始,到舞会时才进人高潮,这样一来,午睡更是必不可少的。那些姑娘先花上半个小时说说笑笑,随后仆人就来拉上百叶窗,在温暖朦肽的环境中,说话声就渐渐变成耳语,终于消失在一片寂静中,接着便是柔和而有规律的呼吸声起伏其间。
斯佳丽先证实玫兰妮、哈妮和赫蒂都在床上躺下了,这才溜进过道,走下楼梯。她从楼梯口的窗户可以看见成群的男人坐在凉亭里,正用高脚杯喝酒,她知道他们要一直在那儿待到黄昏。她眼睛在人群中寻找着,但阿希礼不在其中。于是她仔细听着,居然听到了他的声音。果然不出所料,他仍在前面车道上,跟那些先走的太太孩子们告别。
她提心吊胆地一阵风似的跑下楼梯。要是遇见韦尔克斯先生怎么办?其他的姑娘都在睡午觉,而她则偷偷地在屋里跑来跑去,为此她能找什么借口呢?行了,非得冒下险不可了。
当她走到最下面一级楼梯时,听见仆人在管家的命令下正在饭厅里忙活,将桌椅搬开,准备舞会。走过宽敞的过道就是藏书室大开着的门,她毫无声息地溜了进去。她可以在那儿等着,等到阿希礼送完客回来就叫住他。
藏书室里光线暗淡,因为怕太阳照射,百叶窗都拉上了。昏暗的房间里,四壁高高的全堆着黑鸦鸦的书,真使她丧气。她才不会把这里选做她希望跟他约会的地方呢。见了一大堆书总是让她感到没情绪,见了喜欢读一大堆书的人也一样。只有阿希礼除外。半明半暗中那些笨重的家具在她眼前耸立着,那些高靠背、阔扶手、深座位的椅子是给韦尔克斯家高个儿男人特制的,丝绒面的矮座软椅,配着丝绒面的膝垫,是给姑娘们坐的。在这间长方形房间的顶头,壁炉前有一只七英尺长的沙发,那是阿希礼最喜欢的专座,沙发靠背高高耸起,就像头熟睡的巨兽。
她把门掩上,只留下一条缝,尽力平静了一下心跳。她拼命回想着昨晚打算跟阿希礼说的话,但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是她想出了什么话又忘记了呢一还是她只打算让阿希礼对她说点什么?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不由得让她猛吃一惊。她又一想只要心别在耳边咚咚跳个不停,也许还想得出说点什么。不料听见他送别最后一批客人,走进前面过道时,她的心反而跳得更厉害了。
她只记得一点,就是她爱他一上至他昂然抬起的金发脑袋,下至他那瘦长的黑靴子,从头到脚都是爱,另外她还爱他的笑声,尽管这笑声有时使她莫名其妙,还爱他那让人困惑不安的沉默。哦,只要他现在走进来,一把搂住她,那她就什么也不用说了。他肯定是爱她的一“也许我祷告一下的话一”她双眼紧闭,急急忙忙暗自念叨起来院“仁慈的玛丽亚一”
“咦,斯佳丽!”阿希礼的声音打断了她喃喃的祷告声,她一下子变得慌乱不堪。他站在过道里从门缝里向她张望,脸上带着疑惑的微笑。
“你在躲谁一查尔斯还是塔尔顿兄弟?”
她喘不过气来了。原来男人怎么围着她转他注意到了!他站在那儿,眼睛亮晶晶的,一点也没发觉她的激动,真是说不出的可爱。她说不出话来,只是伸出一只手把他拉进屋。他进来了,虽然糊里糊涂,但也感到有趣。她一副紧张样儿,眼睛瞪得发亮,这是他从没见过的,而且虽然光线暗淡,他也看得出她脸蛋绯红。他不自觉地关上了门,拉起她的手。
“怎么了?”他说,声音轻得像说悄悄话。
他的手一碰到她,她就颤抖起来。现在,事情果然和她梦中完全一样了。她脑子里一下子闪过千百种不连贯的想法,但她一个也抓不住,想不出一句话。她只会哆嗉,抬头仔细地打量他的脸。他干吗不说话呀?
“怎么了?”他重复了一遍,“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吗?”
她突然能说话了,母亲多年来的教导突然统统都被丢在了脑后,父亲那副直截了当的爱尔兰脾气突然从她嘴里显露出来。
“是的一一个秘密。我爱你。”
刹那间,四下一片沉寂,凝重得他们俩都喘不过气来。一阵幸福和自豪一下子涌上心头,她也不再颤抖了。她为什么不早这么做呢?这样岂不比平日所学的那套闺秀手段简单得多?接着她用眼睛探索着他的眼睛。
他眼睛里是惊恐,是怀疑,还不止一是什么呢?对了,有一天父亲心爱的猎马摔断了腿,他只好把马打死,当时他的眼里也是这种神情。为什么她这会儿会想起这件事?多么傻的念头啊。阿希礼怎么看上去那么古怪,一言不发呢?随后他脸上像戴上了一副老练的面具似的,潇洒地笑了。
“今天这儿所有男人的心都被你收服了,还嫌不够吗?”他又用起那种半开玩笑、半奉承的老口吻了,“你是要大获全胜吧?那好啊,你知道你一向深得我心,从小就深得我心的。”
事情不对一全错了!她的计划中可没这个情况。她脑子里一时有很多念头在拼命打转,有一个念头已开始形成了。不知怎的一总有什么道理吧一阿希礼这模样是装出来的,他以为她只是在跟他调情。可他心里并不是那么想的。她知道不是的。
“阿希礼一阿希礼一告诉我一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哦,别再逗我了!你的心给我了吗?哦,我亲爱的,我爱一”
他赶紧用手捂住她的嘴。露出了真面目。
“千万不能说这种话,斯佳丽!可千万不能说。你是说着玩儿的。将来你就会恨自己说了这些话,也会恨我听了这些话的。”
她扭过头。浑身顿时涌过一股热流。
“我决不会恨你的。我告诉你我爱你,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也喜欢我,因为一”她住口了。她从没见过这么痛苦的脸色。“阿希礼,你喜欢的一不是吗?”
“是啊,”他木然地说,“我喜欢的。”
即使他说讨厌她,她也不会这么惊慌。她拉住他的袖子,一时无言以对。
“斯佳丽,”他说,“我们还是走吧,忘掉刚才说的这些话好吗?”
“不好,”她悄声说,“我做不到。你是什么意思?你不想一娶我吗?”
他回答说,“我就要与玫兰妮结婚了。”
不知怎么,她发觉自己已坐在一只丝绒面的矮椅子上,阿希礼就坐在她脚边的膝垫子上,紧紧握着她的双手。他不停地说着一说些她没法理解的事。她脑子里完全一片空白,刚才满脑子的想法统统都没了,他的话如雨点打在玻璃上,一点也没在她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那些话说得很快,充满温柔与同情,就像是父亲在对伤心的孩子说话,只是她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当他提到玫兰妮这个名字时她才清醒起来,她仔细打量着他那双清澈的灰眼睛。看见眼神里有至今仍令她困惑的那种冷漠一还有自怨自艾。
“父亲今晚就要宣布我们订婚的消息了。不久我们就要结婚。我本该早告诉你的,但我以为你知道。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一都知道好几年了。我根本没想到你会一你有那么多男朋友。我还以为斯图特一”
她感到自己又有了生命、感情和理解力。
“可你刚才还说喜欢我的。”
他那双温暖的手都把她捏痛了。
“亲爱的,你一定要让我说些让你伤心的话吗?”
她一言不发,逼得他只有说下去。
“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这些事呢,亲爱的?你那么年轻,遇事又不假思索,你都不明白结婚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我爱你。”
“像我们俩这样缺乏共同志趣的人,光有爱情,就是结了婚也不会美满。斯佳丽,你要求得到的是整个人,包括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和他的思想。要是得不到,你会痛苦的。可我不能把自己整个人都给你。我也不能把自己整个人给任何人。我也不会要你的整个头脑和心灵。那样一来你就会伤心的,于是你就会恨我一恨得多么厉害!你就会恨我读的书,恨我爱的音乐,因为这些东西把我从你身边抢走,哪怕只是抢走一会儿。而我一也许我一”
“你爱她吗?”
“她像我,我们有部分血统相同,我们彼此了解。斯佳丽!斯佳丽!我说的话还不明白吗?除非两个人志趣相投,否则他们的婚姻怎么也不会和美的。”
有人曾说过院“必须和志趣相投的人结婚,否则就不会幸福。”这是谁说的?这句话她似乎已听说过一百万年了,但还是没法理解。
“但你说过你喜欢我的。”
“我本来不应该说这话。”
她脑子里渐渐冒出一股怒火,狂怒之下一切都顾不得了。
“得了,说这话够混蛋的一”
他脸变白了。
“我说这话是混蛋,因为我就要跟玫兰妮结婚了。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玫兰妮。我本来就不该说,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理解的。你对生活充满热情,这正是我缺乏的,叫我怎么能不喜欢你呢?你能大胆地爱,强烈地恨,而我却办不到。为什么你像火、像风、像野生物一样纯真,而我一”她想起玫兰妮,仿佛猛然间看见她那对娴静的棕色眼睛,那副恍恍惚惚的眼神,那双戴着黑花边长手套的文静的小手,看见她那种脉脉温情。于是她又突然来了无名之火,当初她父亲也是无名之火突起才杀了人,另外一些爱尔兰祖辈同样也是由于无名之火起,干了不法勾当,送了性命。她母亲家世代都有教养,天大的事都能默默忍受,而眼下这种美德在她身上丝毫都没了。
“你干吗不说出来,你这个懦夫!你是怕跟我结婚!你宁可和那个傻丫头一起过日子,除了唯唯诺诺,她别的什么都不会说,将来还要生一窝小仔,都和她一样说话拐弯抹角!为什么一”
“你不该这样说玫兰妮!”
“你混账,我怎么不该说!你算老几,敢来教训我该不该?你这个懦夫,你这个混蛋,你一你让我以为你要娶我一”
“说话要公平,”他央求道,“我何时一”
尽管明白他说的是真的,她也不愿讲什么公平。他与她从来没有越过友谊的界线,她一想到这一点,心头就又升起一股怒火,这是自尊心和女性虚荣心受到伤害后的愤怒。她追求他,可他一点也不稀罕她,宁可要玫兰妮这样脸色苍白的小傻丫头。唉,她后悔没听从母亲和黑妈妈的教诲,千万,千万别流露出她对他的喜欢一那就不会落得自取其辱了!
她一骨碌站起身来,双手紧握拳头。耸立在她面前的他脸上充满了沉默的痛苦,一个人被迫面对苦恼的现实时就是这副模样。
“我到死都恨你,你这混蛋一你这下流一下流一”她该骂什么词儿?她想不出更恶毒的词儿了。
“斯佳丽——我求求你——”
他向她伸过手去,恰在此时,她使足了劲儿打了他一个耳光。啪的一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就像抽了一下鞭子似的,她的怒气突然消了,心里只感到一阵凄凉。
他白皙疲倦的脸上清清楚楚留下了几道红印。他一言不发,只是捧着她那只软弱无力的手到唇边吻了一下。接着没等她说话,就走掉了,还轻轻带上了门。
她非常突然地又坐下了。愤怒之下,她竟感到双膝发软。他走了,他那张挨了一巴掌的脸她到死也忘不了。
她听见他轻柔、低沉的脚步声在长长的过道里消失,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她永远失去他了。今后他会讨厌她,他一见到她就会想起她是怎么百般向他献媚的,可他对她根本就没半点意思。
“我跟哈妮·韦尔克斯是一路货了。”她突然想了起来,还想起以前大家怎么轻蔑地取笑哈妮行为放荡,她笑得尤其起劲。她仿佛看见哈妮扭捏做态,挎着小伙子胳臂嗤嗤痴笑的样子,想到这里,不禁又勃然大怒,生自己的气,生阿希礼的气,生大家的气。她对大家的痛恨来自于她对自己的恨,因为这份花季少女的痴情受了挫折,丢尽了脸面,因此恼羞成怒。她这份痴情只有一小部分是真诚的柔情,大部分则是虚荣心和自恃天生魅力的得意劲。现在她失败了,可心里的恐惧比失败的感觉更大,她害怕的是自己当众出了丑。她有没有哈妮那样露骨?大家都在笑话她了吧?想到这一点她不禁不寒而栗。
她的手落在桌边一张小桌子上,摸到一只小玫瑰瓷钵,钵上两个小天使塑像在对着她傻笑。房间里如此安静,她几乎憋不住要尖叫来打破这片寂静。她一定得做点什么,不然就要发疯了。她一把抓起瓷钵拼命朝屋子那头的壁炉扔去。瓷钵刚好擦过沙发高高的靠背,啪的一声,砸在大理石壁炉架上,成了碎片。
沙发深处传来一个声音,“真是太不像话了。”
她从来没这么惊慌害怕过,她口干舌燥说不出话来。她抓住椅背,腿直发软,只见瑞特·巴特勒从他躺着的沙发上站起身来,彬彬有礼且有些夸张地向她鞠了个躬。
“刚才一番争吵硬灌进我耳朵里,一场午觉就此给搅了,这已经够呛了,你干吗还要害我的命呢?”
他是真人。不是鬼。可是,上帝呀,什么话都让他听去了!她打起精神,摆出一副架势。
“先生,你在这儿也应该让别人知道啊。”
“是吗?”他一口白牙闪闪发光,那双大胆的黑眼睛正嘲笑她,“但闯进来的是你呀。我是在等候肯尼迪先生一起离开,又感到我在后院也许不受欢迎,所以就知趣地把这讨人嫌的身子挪到这儿来避避,以为在这儿总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了。谁知,哎呀!”他耸耸肩,低声笑了。
一想到这个粗鲁无礼的家伙听见了一切一听见了她在此时此刻宁死也不愿再提的事,不禁又气上心头。
“你这躲着偷听的一”她怒气冲天地说。
“躲着偷听的往往能听到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事。”他咧开嘴笑着说,“根据长期偷听的经验,我一”
“先生,”她说,“你不是绅士!”
“好眼力,”他轻佻地答道。“你呢,小姐,也不是淑女。”他似乎觉得她挺逗的,因为他又低声笑了,“一个说了和做了我刚才无意中听到的事的人,还算得上什么淑女?不过话又说回来,淑女对我不大有魅力。我知道她们想什么,可她们缺乏勇气,也没有教养,不敢把心里想的说出来。而且,总有一天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家伙。可是你呢,亲爱的奥哈拉小姐,精神倒是难能可贵;这种精神真令人钦佩,我向你脱帽致意了。我真不明白,这位斯文的韦尔克斯先生有什么吸引人的魅力能把像你这样性子暴烈的姑娘给迷住。他能有你这样一个一他是怎么说来着?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姑娘,真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才是,可谁知道他竟是个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一”
“你还不配给他擦靴子呢!”她狂怒地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