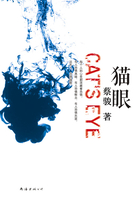那模样看上去真是吓人,现在提起来也还是叫人毛骨悚然。双眼成了两个窟窿,嘴唇烂掉了,一排白牙紧紧地并在一起。暗黑、干枯了的长发贴在太阳穴上,把塌陷下去的青灰色面颊盖住了一点儿,但是,在这张脸上我尚认得出以前经常看到的那张白里透红的欢乐的脸孔。
阿芒无法把目光从这张脸上挪开,他把手帕塞在嘴里咬着。
至于说到我,仿佛有一个铁环紧紧箍在我的头上,眼前一片模糊,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打开碰巧带在身边的一只嗅盐瓶,拼命地嗅着。
我在这种头晕目眩之中,听到警长对杜瓦说:“你认出来了吗?”
“认出来了。”年轻人用颓丧的声音说。
掘墓人把裹尸布又重盖在死者的脸上,再盖上棺材盖,一人抬一头向指定的地点抬去。
阿芒一动也不动,眼睛死死地盯住这个空荡荡的墓穴。他的脸色像我们刚刚见到的死尸一样苍白,俨然成了一个石头人了。
我知道一旦那个场面引起的痛苦缓和下来,不能再支配他时,将会出现什么事情。我走到警长跟前,指着阿芒问他:“这位先生还有没有必要在场?”
“不必了,”他对我说,“我甚至要建议你把他送走,因为他像是病了。”
“走吧。”我挽起阿芒的胳膊,对他说。
“你说什么?”他望着我说,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事情办完了,”我又补充道,“你应该走了,我的朋友,你脸发白,身子发冷,你这样激动会把身体弄垮的。”
“你说得对,我们走吧。”他无意识地回答说,可是一步也没有挪动。
我只好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着走。他像一个小孩一样任人领着,只是有时喃喃地问道;“你看到那双眼睛了吗?”说着,他掉过头去,好像那幻觉已唤起了他对她的回忆。
尽管如此,他还是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动着。他的牙齿格格地作响,双手冰凉,浑身都在剧烈地颤抖。我对他说话,他也不回答。他所能做的,便是让人领着走。我们在门口找到了一辆马车,这真是太凑巧了。他一坐上,就颤抖得更厉害,神经受到了真正的打击。他担心我会受到惊吓,就紧握我的手,低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哭罢了。”
他直喘粗气,眼睛充血,却没有眼泪。我让他嗅我用过的嗅盐瓶。当我们回到他家的时候,他还在颤抖。
在仆人的帮助下,我扶他躺到床上。我把他房里的火炉生得旺旺的。我又连忙跑去找我的医生,把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跟着我赶来了。
阿芒满脸通红,神志昏迷,语无伦次,只听得见他在呼唤玛格丽特的名字。
“怎么样?”待医生检查了病人以后,我才问道。
“还好,算他万幸,他害的是脑膜炎,而不是别的病。因为,天主饶恕我,我本以为他疯了呢。幸好他肉体上的病将会消除精神上的病,过上个把月,也许这两种病都会痊愈。”
阿芒害的那种病,有它爽快、侥幸之处,它要么一下子叫人送命,要么很快地让人治好。
在发生上述的那些事情以后两个星期,阿芒便完全恢复了健康。此时我们也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卧床患病期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一步。
春天,百花盛开,树木葱茏,鸟儿起舞,处处荡漾着它们婉转的歌声。我朋友房间的窗子正面对他的花园,迎来了一片欢乐,迎来了花园里一阵阵有益于身心的清新气息。医生已经同意他起床,从中午到下午两点,正是太阳最暖和的时候,我们经常坐在打开的窗子前促膝谈心。我小心翼翼地避免扯到玛格丽特,生怕这个名字会勾起那掩饰在病人平静外表下的悲伤回忆。可是阿芒正好相反,仿佛偏偏乐意谈到她,而且不像以前那样两眼泪汪汪的,却是带着甜蜜的微笑,这才让我对他目前的精神状态稍释心怀。
我注意到,自从他上一次去过墓地以后,自从那个场面给他带来了这种险些送命的病以后,精神上的痛苦似乎已经让疾病给压住了,玛格丽特的去世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他悲痛欲绝了。确信逝者已矣,这倒使他感到释然。为了驱除经常在他面前显现的悲伤景象,他就一味只追忆跟玛格丽特交往的幸福时刻,好像下了决心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去想了。
热病的摧残,甚至热病的医治过程,都使阿芒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因而精神上再也经不起强烈的感情激动。同时,四周的一片春意盎然也使他的思想本能地追忆一些欢乐的情景。他老是固执地不把他病危的情况告诉家里人,所以在他脱离危险以后,他父亲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天傍晚,我们在窗前坐得比往常稍晚一点。天气好极了。太阳在闪耀着天蓝色和金黄色的暮霭里沉沉入睡。虽说我们身在巴黎,但四周一片翠绿,仿佛让人感到远离了尘世,只有偶尔驰过的马车的辚辚声干扰我们的谈话。
“正好差不多就在这样的季节,在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我才头一次真正认识了玛格丽特。”阿芒对我说,他好像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而不想听我说什么,所以我也就没有出声。然后他向我转过身来,又说下去:
“我必须把这个故事一股脑儿都讲给你听,你可以用来写成一部书,未必有人相信它,但是写这样一部书也许是件有趣的事。”
“你过些时候再讲吧,朋友。”我对他说,“你恢复得不是很好。”
“今晚很暖和,我刚吃过我的一份炒鸡子,”他微笑着对我说,“我已经退烧了,我们又没有什么事要做,我现在就把所有的事情统统告诉你吧。”
“既然你一定要讲,那我就听着。”
以下便是他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动人,我几乎没有改动一个字。
是呀,(阿芒又接着说,把头靠在椅背上)是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加斯东在乡下玩了一天,傍晚我们才回到巴黎,由于无所事事,就去瓦丽爱丹歌剧院看戏。休息的时候我们走了出来,在走廊里看到一个细高个儿的女人走过去,我的朋友向她施了礼。
“你向她施礼的是谁呀?”我问他。
“玛格丽特·戈蒂耶。”他对我说。
“她的模样好像变多了,因为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激动地说,这种激动你等一下就会明白了。
“她生病了,可怜的姑娘活不长了。”
这两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就好像昨天才听到的一样。
朋友,我必须告诉你,两年来每当我遇到这个姑娘的时候,她都会令我产生一种奇特的印象。
我也弄不清楚是何缘故,我的脸色会变得刷白,我的心会“怦怦”地直跳。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秘术的,他说我感受到的是“流体的亲力”,我呢,只知道我注定要爱上玛格丽特了,我预感到了这一点。
她总是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的好些朋友目睹过这种情形。当他们了解到留给我印象的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时,就总是不停地哈哈大笑,这倒是确凿的事实。
我头一次见到她,那是在交易所广场苏斯商店门口。一辆敞篷的四轮马车停在那里,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从车上走下来。她走进商店,跟着就引起一阵切切的赞叹之声。至于我呢,从她进去到出来,就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一动也未动。我透过橱窗玻璃,看着她在商店里挑选想买的东西。我本来也可以进去的,可就是不敢。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但我还是怕她猜到我走进商店去的用意,怕她会受到冒犯而生气。不过,那个时候我倒也没有料到以后还会见到她。
她的穿戴很雅致:穿着一条镶满花边的细纱长裙,披一块四角绣上金线和绸花的印度披肩,戴一顶草帽,手上只带一只手镯,胸口还系着一条正时兴的粗金项链。
她又重新坐上马车,走了。商店里的一个小伙计站在门口,目送着那个漂亮的女顾客的马车离去。我走到他跟前,向他探听这个女人的名字。
“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他回答说。我不敢打听她的住址,于是就走开了。
我以前有过很多崇拜的偶像,过后便忘得一干二净。但这一个偶像富于真实感,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从此我便四处寻找这个美丽非凡的白衣女子。
几天以后,喜剧歌剧院有一场盛大的演出,我去看了。我在包厢里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玛格丽特·戈蒂耶。
和我同去的一个年轻人也一下就认出她来,因为他对我讲着她的名字,说道:“瞧那个漂亮的姑娘。”
就在这时候,玛格丽特用望远镜朝我们这边观望,看到了我的朋友,就对他微笑,做手势叫他去见她。
“我去向她问一声好,”他对我说,“我不消一会儿就回来。”
我情不自禁地说道:“多走运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能去见这位女人。”
“你是不是爱上她了?”
“没有的事,”我说道,脸一下红了起来,因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过我很想认识她。”
“你跟我来,我替你介绍。”
“你先去征得她的同意。”
“啊!老天爷,跟她有什么好拘谨的,来吧。”
他这话叫我心里难受。我生怕玛格丽特真的配不上我对她的感情。
在阿尔封斯·卡尔一本叫《烟雾》的小说里,写一个男人一天晚上紧跟在一个漂亮女人后面,因为她太美了,那男人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为了吻一吻这个女人的手,他感到自己有一股什么都能做的力量,有什么都能征服的意志,有什么都办得到的勇气。这个女人怕裙子碰到泥泞的地面而把它撩起了一下,露出了迷人的小腿,他却几乎不敢正眼看一看。正当他幻想着一定要设法占有这个女人的时候,她在街角站住了,问他愿不愿意上她家去。他掉转头就走,穿过街道,懊丧地回到自己家里。
我想到了这篇作品,我本来渴望为这个女人受苦,我害怕她太快地接受我,太快地把爱情给了我,而我却宁愿用长时间的等待或巨大的牺牲来换取她的爱情。
我们这些男人都是这种脾气,能这样地让感情带上想像的诗意,能让心灵的梦想超过肉欲。也是非常值得庆幸之事。如果有人对我说:“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得到这个女人,而你明天将被处死。”那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人对我说:“你付十个英镑即可成为她的情人。”那我就会拒绝,而且会像一觉醒来看到梦里的城堡已消失的孩子一样哭个不停。
不管怎样,我都很想认识她。这是弄清她是怎样一个人的惟一办法。于是我对我的朋友说,我坚持一定要征得她的同意后才把我带到她跟前去。我的朋友走后,我便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心想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而我尚不知道采取什么态度为好呢。我竭尽全力把该说的话串好(爱情令人变得多幼稚可笑啊)。
一会儿以后,我的朋友回来了,他对我说:“她在等我们。”
“只有她一个人吗?”我问。
“还有一个女人。”
“没有男人吗?”
“没有。”
“那我们去吧。”
我的朋友向剧院门口走去。
“喂,不是从那儿走的。”我对他说。
“我们去买点糖果。她要我买的。”
我们走进歌剧院过道当中的一家糖果店。我真想把整个糖果店都买下来。我正在想看买什么好,这时候我的朋友要买一磅糖渍葡萄。
“你知道她喜欢吃这种东西吗?”
“大家都知道,她从来不吃别的糖果。”
“啊!”离开糖果店之后,他继续说下去,“你知道我要给你介绍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吗?你不要把她想像成一位公爵夫人,她不过是一个妓女,货真价实的妓女罢了。我亲爱的朋友,你别扭扭捏捏的,你想到哪就说到哪好啦。”
“好,好。”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跟在他后面,心想我就要医好自己的多情了。
当我走进包厢的时候,玛格丽特正在大笑不止。我倒宁可看到她是个愁眉不展的样子。我的朋友替我作介绍,玛格丽特对我略微点了点头,说道:“我的糖果呢?”
“在这儿。”
她拿糖果时望了我一眼,我垂下了眼帘,脸红了起来。
她对她身边的那个女人侧过身去,耳语了几句,接着两个人都哄然大笑。很显然,我是引起她们哄笑的原因,这一下我更加尴尬不堪。那时候,我有一个情妇,她是个温柔多情但胸襟狭小的女人,她的自作多情和伤感的书信每每引我发笑。由于我此时此刻的感受,我总算懂得了我给过她的难堪,因而有五分钟样子我爱她胜过一切女人。
玛格丽特吃着她的糖渍葡萄,一点也不再留意我。我的介绍人在旁感到过意不去,想让我尽快摆脱这种可笑的窘境。
“玛格丽特,”他说,“如果杜瓦先生没有跟你说话,你不必为此而大惊小怪,你弄得他这样心慌意乱,他自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倒认为你一个人独自上这儿来会感到无聊,所以才要这位先生作陪的。”
“果真如此的话,”我也开口,“我就不会事先有劳艾尔奈斯特来求得你的同意,然后再作介绍了。”
“这也不过是为了拖延这个逃脱不掉的时刻罢了。”
只要跟玛格丽特这类女人稍有过一点交往,就都知道她们喜欢故意卖弄聪明和捉弄她们第一次见到的人。这无疑是她们对每天从同他们厮混的人那里受到的侮辱的一种报复。
为了很好地对付她,要有她们那种乖巧的本领。但我却没有获得那种本领的机会,而且我对玛格丽特原先的想法更使我觉得她的这个玩笑太过分了。可是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又让我不能无动于衷。因之我霍然站了起来,用一种无法掩饰,气得走了样的声调对她说:
“如果你认为我是这样一种人的话,小姐,那我只好请你原谅我的鲁莽,我不得不向你告辞,并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了。”
说完我行了个礼,便走了出来。我刚关上门,就又听到第三次哄堂大笑。这时候要是有什么人撞我一下,那可不是好玩的。
我回到了我的座位上。这时候准备开幕的信号灯亮了。艾尔奈斯特也回到了我的身旁。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他一面坐下一面对我说,“她们都以为你发疯啦。”
“我离开以后。玛格丽特说了些什么?”
“她又笑话你,说她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好玩的人。但是你可不要认为事情是无可挽回的了。只是你对这些姑娘犯不着做出必恭必敬的样子。她们不知道什么是客气和礼貌。就像往狗身上洒香水,它们倒觉得气味难闻,跑到沟里去打滚、洗掉。”
“这到底跟我有何相干?”我竭力装出冷淡的模样说道,“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个女人了。如果说在我没有认识她以前,她令我有所好感的话,现在我认识了她,那就完全感觉不同啦。”
“算了吧!我相信有朝一日还会看到你坐在她的包厢里面。还会听说你在为她而倾家荡产呢。不过,你说她缺少教养。这也有道理,但这确是一个值得弄到手的迷人的情妇哪!”
幸好幕拉起来了,我的朋友不再出声。我不可能告诉你演的是什么戏。我现在能记起来的,便是我不时抬起眼睛向那个我刚才突然离开的包厢望去,见到的是一些接二连三出现的来访者。
要我不去想玛格丽特,谈何容易。另一种感情又控制了我。我觉得必须把她对我的侮辱和我自己的可笑样子全都置之脑后。我心想,只要我肯把我所有的钱财都花在这上面,就能把这个女人弄到手,堂堂正正地占据我放弃得那样快的位置。
戏还没有演完,玛格丽特和她的朋友就离开了包厢。我也站了起来。
“你要走?”艾尔奈斯特问我。
“是。”
“为什么?”
这时他才看到那个包厢已经空了。
“去吧,去吧。”他说,“去碰碰运气,或者说去碰碰好运气。”
我走了出去。
我听到在楼梯上有长袍的声。我闪过一旁,不让别人看到,而我倒可看到那两个女人从身旁走过去,由两个年轻人陪着,在剧院的入口处,一个小厮迎了上来。
“叫马夫在英吉利咖啡馆门口等候,”玛格丽特说,“我们步行上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