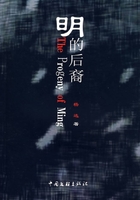每一个黎明都是一份令人愉快的邀请,使我的生活跟大自然一样简朴,也可以说纯真。我跟希腊人一样,真诚地崇拜着黎明女神奥罗拉。我早早起床,沐浴在小湖之中;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活动,是我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据说在成汤王的浴盆上铭刻着这样的文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懂得这个道理。黎明带回了英雄时代。一大早,我敞开门窗坐着,一只蚊子穿越我的房间,开始了一次看不见、也想不到的旅行,它那微弱的嗡嗡声使我大受感染,就像我听到了吹捧英雄美名的号角一样。这是荷马的安魂曲,其本身就是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吟唱着自己的愤怒和漂泊。此中颇有些宇宙之念。只要容许它存在,它就会不停地宣扬世界的无穷活力和生生不息。清晨是一天之中最难忘的时节,也是觉醒的时辰。那时候,我们一点也不瞌睡,至少有这么一个时辰,我们身体中日夜昏睡的一部分开始苏醒。如果唤醒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守护神,而是用肘机械地轻推我们的某个仆人;不是我们的新生力量和内心抱负,伴随着天上的美妙音乐和袭人的馨香,而是工厂的铃声;如果我们醒来时,生活的境界并没有比睡前高多少,那么这种白天,如果也可以称作白天的话,也没有多少可期待的;反过来说,黑暗也可以结果子,从而证明自己是好样的,不比白天差。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每天都有一个比没有遭到他亵渎的更早更神圣的黎明,那他一定是对生活产生了绝望,从而步人了一条走向黑暗的道路。感官生活部分歇息之后,人的灵魂,或者不妨说人的感官,每天都在散发新的活力,他的守护神又在试他,看看他能创造何等高贵的生活。可以说,一切值得记忆的事情都在黎明时的气氛中发生。《吠陀经》说:“一切智慧都于黎明中醒来。”诗歌和艺术,还有最美丽最值得纪念的人类行为,都源于此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都跟曼侬一样,是曙光女神奥罗拉之子,在日出时分弹奏出美妙的音乐。对于思想活跃,富有活力,和太阳同步的人来说,白天是一个永恒的黎明。闹钟如何报时,人们是何态度,从事什么劳动,这些都与他无关。清晨就是我醒来时,心中有一个黎明的感觉。道德改革就是要抛弃睡眠。如果人们不是成天睡觉,那么他们为什么把白天说得这么差?他们的计算本领并不差嘛。如果他们不是昏昏欲睡,他们本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有几百万人清醒得可以做体力劳动,但是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清醒得可以做有效的智力劳动,而一亿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过得富有诗意而神圣。清醒就是生活。我还从未碰见过一个异常清醒的人。我怎样去面对他呢?
我们必须学会再苏醒,学会使自己保持清醒,这不是通过什么机械的帮助,而是通过对黎明的无限期待,就是我们睡得再熟,黎明也不会把我们抛弃。我知道,令人振奋的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提高。能够画一幅特别的画,或雕刻出一尊塑像,或美化几个物体,这确实了不起,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塑造出,或者画出那股气氛,那种媒介,这样,我们就能从中有所发现,在道义上有所作为。要能影响时代的特征,这才是最高的艺术。每一个人都应使自己的生活经得起崇高和关键时刻的考验,哪怕是微小的细节。如果我们拒绝,或耗尽了我们业巳取得的这点微不足道的信息,那么神谕就会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一切。
我到森林中去住,是因为我希望生活过得谨慎一点,只面对基本的生活事实,看看我是否能学会生活教我的一切,免得临死之前发现自己没活过。我并不想过不是生活的生活,要知生活这么可爱,我也不想与世隔绝,除非有此必要。我要深人地生活,吸出生活的全部精髓,要坚强地生活,像斯巴达人一样,扫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将其夷为平地,然后再小心地加以修理,将生活逼到每一个角落,将它的条件压到最低限度,如果证明生活是卑微的,那么就要将生活中的一切卑微之处弄清楚,然后公之于众;如果生活是高尚的,那么就要通过体验去了解它,好在下次郊游时将它真实地记载下来。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对生活都捉摸不透,不知道它是属于魔鬼呢,还是属于上帝,因而多少有点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颂扬上帝,永远享受他带来的喜悦”。
然而我们依然生活得很卑微,像蚂蚁似的;虽然神话告诉我们,我们早就变成了人,但是我们仍像侏儒一样,在跟仙鹤作战;这真是错上加错,脏上加脏,我们最好的美德此时成了多余而可避开的倒霉鬼。我们的生活就这样消耗在琐碎之中。一个老实人只要数他的十个手指就够了,极端情况下,还可以再加上他的十个脚趾,余下的不妨以此类推。简单,简单,再简单!我说,你的事情只要两三件就够了,而不要上百件或上千件;数个半打就够了,何必要数一百万呢,记账用你的大拇指就够了。在这种波浪滔滔的文明生活海洋中,一个人要想生存,就得顶住风云暴雨,层层流沙,还有一千零一件事件,除非他想让船沉没,自己跃身海底,不作航位推算,不到目的港,那些成功的人必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计算家。简化,再简化。一天不必三顿饭,如果必要,一顿就够了;菜不必一百道,五道就行了,其他事情也按比例递减。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德意志联邦,全是由一些小邦组成的,边界不断在变,就是德国人也无法随时说出他的边界在哪儿。顺便说一下,国家内政的所谓改善,全是些外表而肤浅的东西,国家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畸形发展、难以驾驭的机构,由于缺乏计算,没有崇高的目标,机构里塞满了家具,从而掉进自己设计的陷阱里,给奢侈和挥霍毁掉了,就像陆地上的上百万户居民;对国家和居民而言,惟一的对策就是实施一种严格的经济政策,过一种比斯巴达人还要简单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标。现在的生活太放荡了。人们认为国家应该有商业,出口冰块,通过电报交谈,一个小时跑30英里,也不怀疑他们是否做得到。至于我们的生活过得应该是像狒狒,还是像人,则心中无数。如果我们不是铺设枕木,锻造钢轨,日日夜夜地忙于工作,而是马马虎虎地过日子,以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谁去造铁路呢?如果铁路没有造好,我们又如何能及时到达天堂呢?但是如果我呆在家里,照料自己的事情,那么又有谁需要铁路呢?不是我们乘火车,而是火车乘我们。你们是否想过,那铺在铁路下面的枕木是什么?每一根枕木都是一个人,一个爱尔兰人,或一个北方佬。铁路就铺在他们身上,他们满身沙土覆盖,火车稳稳当当地从他们身上驶过。我敢保证,他们就是熟睡的枕木。每隔几年,一批新的枕木就会铺在钢轨下面,因此,如果有人有幸乘火车,就必然会有人不幸地遭火车碾轧。如果他们压上了一个梦游者,一根出了轨的枕木,将他唤醒,他们就会紧急刹车,然后大嚷大叫,好像这是一个例外。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每隔5英里就需要一帮人,负责让枕木长卧地上,和路基一样平,这表明,有时候,枕木是会重新站起来的。
我们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匆忙,浪费生活?我们下定了决心,没饥之前,就先挨饿。有人说,即时缝一针,可以省九针,因此,他们今天缝了一千针,省掉了明天的九千针。至于工作,我们还没有什么结果呢。我们患上了圣维特斯舞蹈病,无法使自己的头静下来。我只要在教区拉几下钟绳,就像报火警一样,也就是说,钟声还没响彻起来,我敢说康科德郊外农场上的任何一个人-尽管今天早上还屡屡借口说忙得要死,任何一个孩子,还有任何一个妇女,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活计,循着钟声跑来;说实话,他们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从火中拯救财产,而是观看火势,因为火巳烧着;要知道,火并不是我们放的,我们也不是来看火是如何被扑灭的,而是想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也帮忙救救火;是的,哪怕烧的是教堂。一个人吃完饭,难得睡上半个小时的午觉,醒来后抬头就问道:“有什么新闻没有?”好像别人都在给他站岗。有人吩咐,每隔半个小时就把他叫醒,显然并没有什么目的;然后,作为报答,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梦。一夜醒来,新闻跟早餐一样必不可少。“请告诉我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任何人所碰到的任何新事”,-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看报读新闻,什么一个人今早在瓦奇托河上被人抠去了眼珠啦,他也不想想,此时此刻,他就生活在世界这个深不可测的大黑洞中,只剩一点眼睛的痕迹。
对我来说,没有邮局,我也能凑合着过。我觉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通过邮局来交流。说得准确一点,我一生中只收到过一两封值得邮资的信一这话还是我多年前说的。所谓便士邮政制,就是你正儿八经地为一个人付一便士的钱,希望能得到他的思想,结果呢,得到的都是笑话。我敢肯定,我从没在报纸上读到任何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一个人遭劫,被谋杀,出车祸,或一座房子被烧,一艘船沉没,或一艘汽船爆炸,或一只奶牛在西部铁路上给碾死了,或一条疯狗给杀掉了,或冬天出现了一群蝗虫,一我们根本就不必再看下去了,一条也就够了。如果你巳熟悉了原则,何必又要去管这么多的实例和应用呢?对哲学家而言,一切所谓的新闻都是流言蜚语,只有上了岁数的妇人才会一边喝茶,一边编辑阅读这些。然而却有不少人在贪婪地追求这些闲言碎语。我听说前几天,有许多人蜂拥到一家报馆,想了解最新的外国新闻,以至于把报馆的几块方玻璃都挤破了,一而我却正儿八经地认为,这种新闻,聪明的人12个月或12年前就巳丝毫不差地报道过。比如说西班牙,如果你知道如何将唐·卡洛斯和公主,唐·彼得罗,塞维涅和格拉纳拉时时放在合适的报道位置就行了,一自从我读报以来,他们的名字可能变了些一,如果没有其他趣事可以报道,你可以报道一场斗牛,这场报道一定真实,它将西班牙的准确现状和衰败现象统统告诉了我们,就像报纸同一标题下所作的简洁明了的报道一样;至于英国,来自那个地方的最新新闻差不多还是关于1649年的革命,如果你知道英国历年谷物的平均产量,你就再也不会去留心这类事情了,除非你的投机只是为了钱;如果让一个人下判断,看谁很少看报,他会说,国外没什么新事发生嘛,就是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什么新闻!要知道永不衰老的事情,那才是最最重要的新闻啊!“蘧伯玉(卫大夫)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一周工作下来,农夫们昏昏欲睡,一星期天正好是一周辛苦工作的总结,不是新的一周的新鲜美好的开始。而传道士们偏偏不是在他们的耳边进行冗长乏味的布道,而是冲着他们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停,停下!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快,而实际上却慢得要死?”
虚伪和谬见被推崇为最健全的真理,而现实则成了虚构。如果我们安安稳稳,只观察现实,不让自己受骗,那么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相比,生活就成了一篇童话和《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如果我们只尊重不可避免的事和有权利生存的事,那么诗歌和音乐就会在街头回荡。如果我们生活悠闲,办事聪明,我们就会看出,只有伟大和优秀的事物才能永久而绝对地存在,一而小小的恐惧和小小的乐趣只不过是现实的影子。现实永远使人振奋,令人崇敬。人们闭目养神,任凭各种假相的欺骗,就这样,他们养成了日常生活习惯,并且到处加以巩固;而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纯粹的幻想基础上的。嬉戏生活的儿童,反而比成人更加清晰地看出了生活的真正规律和关系;而成人却生活得没有价值,可是他们却还以为他们更聪明呢,因为他们积累了经验,而实际上,他们积累的是失败。我在一本印度的书中读到:“有一位王子,从小被逐出本土,后被一位樵夫收养,长大成人,他一直以为自己就是贱民中的一员。他父亲手下一位大臣发现了他,向他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对他身份的误解得以消除,他知道自己是一位王子。所以,”这位哲学家接着说道,“由于灵魂所处的环境,因而误解了自己的身份,直到某位神圣的老师向他指明真相,这时他知道自己就是梵。”我看到,我们新英格兰人之所以活得如此卑贱,就是因为我们的视力没有穿透事物的表面。我们把似乎是看成了事实。如果一个人走过这个小镇,看到的只是现实,那么你想“密尔德姆街”会通向哪里?如果他给我们描述他在那儿看到的现实,那么他描述的地方我们就会认不出。瞧一瞧礼拜堂,或县府大楼,或监狱,或商店,或住宅,说一说你真正看到的是什么,在你的描述里,它们都成了碎片。人们推崇的是遥远的真理,远在系统之外,就在最远的一颗星星之后,在亚当之前,人类灭绝之后。永恒之中确实存在着真理和崇高。但是所有这些时间,地点和理由都在此时此刻啊。上帝本身的荣耀就体现在现在,绝不会随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更加神圣。我们只有永远地融人周围的现实,和现实打成一片,才能理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崇高。宇宙温顺而不停地回应着我们的想法;无论我们跑得快还是跑得慢,路轨总是给我们铺好。让我们毕生作此构想吧。诗人和艺术家从未有过这么美好而高贵的设计,但是他的子孙后代至少可以完成它。
让我们像自然一样从容地过上一天,不要因掉在路轨上的坚果外壳或蚊子的翅膀而出轨。让我们黎明即起,轻手轻脚,泰然自若,用或不用早餐;让人来人往,让钟声响起,小孩啼哭,一我们下定了决心,好好过上一天。我们为什么要举手认输,随波逐流呢?让我们不要跌人到子午线浅滩处人称“美餐”的可怕急流与漩涡之中。一旦渡过这一险关,你就平安无事了,剩下的就是下坡路了。神经不要松弛,利用早上的活力,像尤利西斯一样,将自己拴在桅杆上,向另一个方向航行。如果汽笛鸣叫,让它叫好了,叫疼了,嗓子也就哑了。如果钟鸣,我们为什么要跑?我们还要考虑考虑,看看它们像什么音乐。让我们安心工作,涉足于污泥浊水般的观点、偏见、传统、欺骗和幻象之中,这覆盖了全球的淤土,让我们穿越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康科德、教堂和国家,穿越诗歌、哲学和宗教,直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坚硬的底层和牢固的磐石,我们将此称之为现实,并说,瞧,就是这儿,没错;一旦有了这个pointd"appui,你就可以在山洪、冰霜和火焰之下,开辟一个地方,建造一堵墙,或建立一个国家,竖一根灯柱,或测量仪不过不是尼罗河水位测量仪,而是现实测量仪,如此一来,后代子孙就可以知道,山洪般的欺骗和幻象日积月累有多深。如果你笔直而立,面对现实,你就会看到太阳照耀着事实的两面,好像这是一把东方弯刀,你会感到它甜美的刀锋正在分割着你的心和骨髓,这样你就会愉快地结束你的凡人生涯。生也好,死也好,我们追求的只是现实。如果我们真的要死了,让我们听到自己的喉咙里发出的格格声,感觉到四肢的寒冷情况曰如果我们活着,那么就让我们忙自己的去吧。
时间只是我垂钓的小溪。我喝的是小溪的水;但是我喝水的时候,清晰地看到了河底的沙子,从而感到小溪是多么的浅啊。河水潺潺逝去,永恒却保持不变。我愿饮得更深,或到天上去垂钓。天底布满了星星,像鹅卵石一样。我连一个都数不出。我认不出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我一直感到懊悔,觉得自己没有生来时那么聪明。智力是一把刀子,一旦看准,它就会一路割下去,切开万事万物的奥秘。我的双手再也不想去忙多余的事情了。我的头脑就是手和脚。我感到我的一切最佳本领全都集中于此。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头脑是一个奥秘挖掘器官,就像有些动物用嘴,有些动物用前爪一样,我要用自己的头脑,一路挖掘,在这些山上开出我的路来。我想最富有的矿脉就在附近,因此,运用手中的占卜杖顺着腾起的薄雾,我就此作出判断,我要从此开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