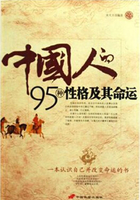人生到了某种境界,便不免认为处处皆可安家落户。因此,我在住所周围,方圆12英里之内,将每一个农庄都考查了一番。在我的想象中,我把所有的农庄接二连三地都买下了,因为所有的农庄都得买下,我知道他们的价格。每个农民的田地我都转悠了一遍,品尝了他的野苹果,和他谈谈耕作,按他开的价,买下他的农场,然后再盘算着用什么价格,将农场抵押给他,价格甚至不妨开得高一点,一什么都买下了,就是没有立下契据一就把他的话当契据,因为我很爱谈话。我耕耘了这片土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想也耕耘了他这个人,就这样,我尝够了耕种的乐趣之后,便扬长而去,由他接着耕下去。由于这番经历,朋友们都把我当成了房地产经纪人,无论坐在哪儿,我都可以生活,并给四周的风景发去相应的光芒。何谓家宅,一张座位而已。如果这个座位设在乡下,那是再好不过了。我发现了许多造房地点,地价似乎不会因为造房而马上得到提高,有人或许会说,这离村子太远,但我却认为,是村子离他太远。我说,好吧,我可以在那儿住,瞧,我真的在那儿过了一个小时的冬夏生活,体验了一下岁月是如何流逝;熬过了冬天,便看到了新春降临。这个地区的未来居民,无论房子造在何处,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他们之前,有人就已在此住过了。只要一个下午,就可以将这块地辟为果园、林地和牧场,决定好哪些优良的橡树或松树应该留在门前,并将每一棵枯树派上最佳用场;然后我就撒手不管了,或者说让它休耕,一个人拿得起,放得下,自然也就富有。我的想象纵横驰骋,我甚至得到了几个农场的优先购买权,一而这正是我所期盼的一不过实际拥有财产也从未使我吃过苦头。购买霍乐威尔农场那一次,我就差点实际拥有了这座房产,当时,我已选好了种子,找好了做手推车的木料,准备将此事继续下去,但是,还没等主人将房契给我,他的妻子一每个男人都有这样一位妻子一却变了卦,说她想保留这座房产,于是,他提出赔我10美元,解除约定。说真的,此时此刻,我在这个世上只有10美分,如果我是那个拥有这10美分的人,或者是拥有一个农场,或10美元,或所有这一切的人,那么我就算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了。然而,我没收下这10美元,也没有占有这片农场,因为我做得已经过火了;或者不妨说我慷慨大方,按买进的原价,将农场又卖给了他,由于他并不富有,我将这件10美元的礼物送给了他,手上还留着我的10美分和种子,还有准备作手推车用的材料。由此我发现,自己一直是一名贫不失志的富翁。但是我保留了那儿的风景,自此以后,我年年将风景所产生的果实带走,用不着手推车。至于风景,一是眺望一切美景的君王,我的权力不容争辩。我经常看到一个诗人,在欣赏了农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后,扬长而去,而执拗的农夫却还以为他拿去的只是几只野苹果。唉,诗人已将他的农场写进了诗,而农夫多少年来却还一直不知道,这道备受人们赞美、肉眼又看不到的栅栏,已经将它拦了起来,挤出它的牛奶,脱去牛奶里的奶油,然后再将乳脂全部拿走,留给农夫的只是脱了脂的牛奶。
在我看来,霍乐威尔农场的真正魅力在于:农场离群索居,村子离它有两英里之远;就是最近的邻居,离它也有半英里,况且还有一大片农田将它与公路隔开;农场傍靠河流,据主人说,春天,河上下雾,霜冻也就没有了,对此我倒无所谓;农舍和牲口棚看上去阴沉昏暗,圮废失修,就是篱笆也是支离破碎,好像我和前一个居民之间,彼此相隔了不少岁月;给兔子咬过了的苹果树树身空洞,苔藓密布,表明我会有些什么样的邻居;但最主要的还是那段回忆,早年,我曾溯河而上,当时,红枫簇簇,房子掩映其中,红枫深处,犬声不断。我急于将它买下,也不管业主是否已将那些石块搬走,或砍掉那些空洞的苹果树,或铲掉牧场上拔地而起的那些小白桦树了,总之,我再也等不及进一步收拾了。为了享受这些好处,我已准备将它继续下去,像阿特拉斯一样,将世界扛到我的肩上一我从未听说他为此得到过什么好处一万事一身担,我这样做只是想付清账款,平平安安地拥有这座农场,并没有什么别的动机或借口,因为我一直感到,如果我能放手经营,农场就一定会像我希望的那样,五谷丰登,但是结果呢,前文已交代过了。
关于大规模的耕作(我一直耕耘着一个园林),我惟一能说的就是我的种子已经准备好了。许多人认为,随着年代的前进,种子会变得更好。时间分得出好坏,对此我并不怀疑;等到最终真的能播种了,我不会感到大失所望的。但是我要最后一次对伙伴们说:你们要自由自在地生活,无拘无束地生活,能多久,就多久,热衷于农场与关在县府大牢,二者没有多大区别。
老加图的《农书》成了我的“栽培者”,他说,一可惜我见到的那个惟一译本将这段话译得一团糟,一“当你要买农场时,你要多动脑筋,不要贪婪地就将它买下,也不要怕吃苦,不去看它,不要以为去转悠一次就够了。如果农场好,那么你去看的次数越多,你就会越喜欢它。”我想我不会贪得无厌地去买,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经常会去转转,就是死了,也要先葬在那儿,这样,就会使我最终获得更大的乐趣。
眼下要说的是我这种试验中的第二个,至于更加详细的细节,容我慢慢道来;为了方便起见,我把两年的经验合二为一。正如我一开始所说,我无意写一首沮丧之歌,只是希望像一只报晓的雄鸡,栖息在窝棚上,引吭高歌,哪怕唤醒我的邻居。
我住进森林的第一天(也就是说我昼夜住在那儿),碰巧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即1845年7月4日,当时我房子还没完工,抵挡不了冬寒,只能勉强挡挡风雨,房屋没有粉刷,烟囱也没砌好,墙壁用的是风雨侵蚀、斑驳变色的旧木板,缝隙很大,一到夜晚,屋子里就冷飕飕的。砍削好的立柱白白直直的,门框和窗框也是刚刚刨平,整个房子给人一种清洁通风的景象,尤其是在早上,木头浸着露水,这时我总爱幻想:到了中午,一些甜甜的树胶就会从中渗出来。在我的想象中,这种黎明般的情调一整天都留在屋子里。我不禁想起上一年我游览过的那个山上小屋,这个小屋通风良好,又没涂灰泥,正好适合四处游玩的神仙逗留,女神也可在此拖曳长裙。吹过我屋脊的风,恰似那吹过山脊的风,风吹过处,断断续续地传来美妙的旋律,这只是人间音乐的天上片断。晨风永远在吹,创世纪的诗篇连续不断,可惜听者杳然。奥林匹斯山就在大地的外表,随处可见。
除了一只小船,我曾拥有的惟一房产就是一顶帐篷,夏天出游时,我偶尔用用它,这顶帐篷至今还卷着,放在我的阁楼里,但是那条船,几经转手,已经随着那时间的长河,飘逝而去了。有了这座实实在在的安身立命之处,我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渐渐地安顿了下来。虽说屋架有点单薄,但它到底给我筑就了一道水晶似的保护层,并在造房者身上产生了作用。它使人多少想起一幅素描的轮廓。我不必坐到室外去呼吸空气,因为室内的空气同样新鲜,坐在门后与坐在门里也没多大差别,即使是在滂沱的雨天也是如此。《哈利梵萨》里说过:“巢之无鸟犹如肉之无味。”我的住所并非如此,不知不觉之中,我发现自己突然与鸟儿成了邻居。我并不是捉一只鸟,然后把它放在笼子里,而是在它们边上,将自己囚在笼子里。我不仅离经常光顾园林和果园的鸟儿更近了,而且离森林中的鸣禽也更近了,这些鸣禽——鸫科鸣鸟,威尔逊鸫,猩红比蓝雀,野麻雀,三声夜鹰,还有其他一从来没有向村民吟唱小夜曲,就是有也很稀少,但它们更有野性,也更令人激动。
我住在一个小湖滨,往北一英里半是康科德村,我这儿比康科德村更高一些,小镇与林肯乡之间,森林茂密,我就身居其中,再往北约两英里是惟一的胜地康科德战场;不过我的位置在森林中很低,和别处一样,小湖的对岸也为森林覆盖,因此只有半英里之遥的湖对岸,却成了我最遥远的地平线。第一个星期,无论我何时凝视这小湖,我都感到这是一个山中之湖,湖底远远高出别的湖面,日出时分,我看到小湖脱掉了夜幕般的雾衣,渐渐地,小湖四处,微波粼粼,湖面如镜,而雾则像幽灵,不知不觉地向四处撤退,隐到森林之中,就像夜间的某个秘密宗教集会,悄然隐散。露水则悬挂在树梢上,悬挂在山的两侧,到了晚上还不消失。
8月里,在和风细雨的间隙,小湖成了我最可贵的邻居,那时,风平浪静,但是空中却是乌云密布,虽说下午已过去了一半,却跟晚上一样安静,鸫科鸣鸟到处歌唱,隔岸相闻,这时没有比这样的小湖更安静的了;由于乌云的推进,湖面上的那部分清新空气变得稀薄而暗淡,而波光粼粼,倒影重叠的水面,其本身就是一个下界天国,自然弥足珍贵。附近的山顶上,树木刚被砍去,站在小山顶,放眼向湖的南岸看去,湖光山色,甚是宜人,山与山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凹口,正好形成湖滨,两座小山坡相互倾斜,使人感到有一条溪涧从森林覆盖的山谷中倾泻而下,而实际上并没有溪涧。就这样,我看到了临近的青山,越过青山,我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些更高更远的山脉,层峦尽染天蓝色。说真的,踮起脚尖,我能看到西北角上的一些小山峰,更蓝,也更遥远,就好像是上天筑就的一块块货真价实的蓝色硬币,我还看到了乡村的一隅。但是换个方向,即使还在这个视角上,我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森林覆盖,挡住了我的视线。附近有些水真好,水给大地以浮力,让它漂浮起来。即使是最小的井也有价值,其中之一就是当你向井中观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地球并不是绵绵相连的,而是一个孤岛。这一发现很重要,就像井可以冷却黄油一样。站在这个小山巅,我将目光越过这个小湖,伸向了萨德伯里草原,发大水的时候,我感到草原在上升,或许这是山谷中热气腾腾的海市蜃楼作用的结果吧,就像盆底的一枚硬币一样。小湖之外,所有的大地看上去都好像是一层薄薄的外壳,就这么小小的一层水流就使它成了孤岛,在水面上漂浮,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住的这块地方不过是块干燥的土地。
虽然从我的门向外看去,视野有所限制,但是我一点也不感到拥挤,也不感到狭窄。因为这5世纪印度经典,记载了毗瑟拿(Vishnu)的化身克利须那(Krishna)的事迹和教义。
儿有片辽阔的牧场,足够我的想象驰骋。小湖对岸,长满了矮橡树的高原突兀,一直向西部的大草原和鞑靼式的干草原延伸,给所有的浪游家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当达摩达拉的牛羊需要更大的新草原时,达摩达拉说道:“只有自由自在地享受广袤的地平线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地点和时间都在变,我住的地方离宇宙的这些区域,离我为之神往的那些历史时代越来越近了。我住的地方跟天文学家每夜观察的天体一样遥远。我们常常幻想,在天体的某个更加神圣的角落,有一些稀罕而且格外宜人的地方,就在仙后座五亮星的后面,远离尘嚣。我发现我的房屋位置就坐落在宇宙中这个离群索居之处,亘古常新,纯洁清静。如果说住在这些地方,靠近昴星团,或毕星团,金牛星或牵牛星座是值得的话,那么我住的恰好就是这种地方,跟这些星座一样,将人世远远抛在后面,就像一束微光,一闪一烁,照耀着我最近的邻居,而只有在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才会看到我,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天地万物中的这一部分:
从前住着个牧羊人,他的思想高过了山,山上有他的一群羊,时时将他来喂养。
如果他的羊群总是跑到比他的思想还要高的牧场上,那么牧羊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