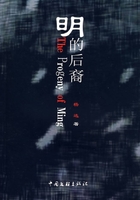1942年,我认识了贝塔,当时他20岁,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小伙儿,有一双智慧的黑眼睛。他双手容易出汗,举止中能看出他有些过分腼腆,腼腆之中隐藏着他的雄心壮志。他的言谈举止中既有高傲又有谦卑,内心则充满了自信,深信自己高于那些谈话对手。他在突然抨击他们之后,又会立即羞怯地退缩回去,并且把自己的利爪隐藏起来;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充满了隐忍的嘲讽。也许当贝塔跟我或者跟别的比他年长的作家谈话时,他的这个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诗人,他觉得应该尊敬长者,但与此同时,贝塔认为他们也没什么可让他尊敬的地方,他更知道,在自己身上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杰出作家的天赋。
那是在1942年的华沙,我们生活在绝望之中,但仍抱着某种希望,尽管我们知道,这仅仅是幻想。我们这个被占领的国家,曾是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看到这个帝国的实力是如此强大,只有最盲目乐观的人方能相信德国有一天可能被完全击败。对我们国家的人来说,**党**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DeutscheArbeiterPartei,简称NSDAP),即德意志******工人党。的计划一目了然:消灭知识阶层,实行殖民化,并将部分居民强制迁徙至更远的东方。贝塔属于在“二战”时期开始用奴隶的语言写作的青年人之一。他以打各种零工维持生计——很难确切地解释,那时在一个完全没有法治的城市里,人们如何找到谋生的途径。大家通常是在工厂或机关办公室拿到一张假的就业证明,有了就业卡后,就在黑市找机会做点买卖或者靠扒窃为生,这种行为并不会被认为不道德,因为这样做是为了对抗德国当局。那时,贝塔还是地下大学的学生,跟参与反抗运动的年轻人一起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在年轻人的秘密集会上,他们喝烈性酒,情绪激昂地争论文学和政治问题,还阅读许多违禁杂志。
贝塔曾经以轻蔑嘲笑的态度观察自己的同学,他知道的事情比同学们多,也更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贝塔认为,他们抵抗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对他来说,纯粹是非理性的冲动。斗争——是的,可是以什么名义?没有一个年轻人相信民主。战前,东欧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半独裁的统治之下,议会制度似乎属于遥远的过去。获得政权的手段毋须经过讨论,那些想执掌政权的人必须制造“运动”,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获得共同执政,或者武装夺取政权。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兴盛的时代,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为此立下了榜样。参加华沙抵抗运动的年轻人深受这种不久前还非常普遍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均没有任何好感。他们并没有很明确的纲领,波兰民族遭受德意志民族的蹂躏,因此就应奋起反抗德国。当贝塔提出自己的论点,认为这仅仅是波兰的民族主义反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时,他的同学们都攘臂相争反对他的说法。贝塔试图把他们逼到墙角并质问他们:“你们想扞卫的是怎样的价值?未来的欧洲将建立在何种原则之上?”但他也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这里是黑暗的核心:不仅没有任何解放的希望,也看不到任何明天的景象。大家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即便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许能盼到英、美胜利的那一天,作为对他们的奖励——也只不过是看到自己的祖国重新回到战前状态;其实,战前的情况也并不令人满意。这种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的局面,使贝塔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之外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堕落世界。当老一代的自由派人士仍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要尊重人的老调时,其周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遭受屠戮,这些自由派人士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他们早已落伍到可悲的老古董行列了。
贝塔没有任何信仰——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别的信仰,而且他够胆在其诗歌中承认这一点。他费了很大的劲,用非常原始的凸版印刷和非常差的颜料(因为难以弄到好颜料)做了种种努力,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当我拿到这本诗集并费力地翻开黏糊糊的油印封面朝里看时,我立即意识到是在与一个真正的诗人打交道。但是,阅读他的六步韵诗并不令人感到愉快。沦陷中的华沙街道充满了阴郁,抵抗运动的各种会议在弥漫着烟雾和因没有暖气而冻得人发抖的寒室里举行,与会者在谛听楼梯上是否响起盖世太保的脚步声时,都会觉得毛发悚立,犹如当年基督徒在古罗马阴森森的地下墓室里偷做礼拜那样,人人感到不寒而栗。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处在帝国的底部,就像是处在巨大的弹坑底部,头顶上的天空是我们与地球上其他人共同分享的唯一财富。这一切都存在于贝塔的诗中:晦暗、迷蒙、阴郁和死亡。但他的诗不是那种控诉的诗歌,而是属于斯多葛主义斯多葛主义,亦称斯多葛哲学学派(或称斯多亚学派),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英文stoics,来自希腊文stoa,原指门廊,后专指斯多葛学派)聚众讲学而得名。他的诗中所描写的同龄人也都没有任何信仰,他们最基本的动机就是号召大家去战斗,然后英勇牺牲。死亡在不同时代的许多年轻诗人的作品中常常作为浪漫的道具,这里描写的死亡与之相反,恰是过于现实:华沙所有最年轻的诗人都死于战争结束之前,或者死在盖世太保手下,或者死于战场。然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像贝塔那样怀疑牺牲的意义。“我们身后只留下一堆堆废铁——和世世代代沉闷的、嘲弄的笑声。”贝塔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
在贝塔的诗中,没有包含对世界的任何肯定,这种肯定在艺术中通常是以好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艺术家带着好感展示一只苹果或是一棵树木。他的诗表露的是一种深深的失衡情绪。从艺术中能领略出很多东西:巴赫的世界或者彼得·布鲁盖尔彼得·布鲁盖尔(PieterBruegel,1525-1569),16世纪荷兰尼德兰地区的伟大画家,自扬·凡·艾克(JanvanEyck,1385-1441)始的早期荷兰画派的最后一位巨匠。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被称为“农民的布鲁盖尔”。他善于思想,天生幽默,喜爱夸张的艺术造型,因此人们又赠给他一个外号“滑稽的布鲁盖尔”。他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农民画家”。的世界,都是非常有序的世界,当然也是等级森严的世界。现代艺术包含很多盲目激情的例子,从来也不满足于对形态、色彩和声音的描写。只有当艺术家感受到爱世间一切萦绕在他身边的事物时,对感性美的内省才有可能。艺术家一旦对一切事物都兴味索然,他甚至无力在某处驻足和观察这些事物。他甚至会为那种爱的冲动感到羞惭。他会认为不停的运动是天意使然,他会不由自主地动着,一刻也不能静止。他会断断续续地写出他对世界零碎、片段的观察。就像一个梦游者,只要还在行走,他就能保持平衡。贝塔诗中的画面,宛如不停旋转的雾,只有靠他的六步诗韵干巴巴的严谨节奏才能挽救那些画面,使之不致完全混乱。造成贝塔诗歌这个特点的,部分是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不走运的民族,属于不幸的一代。但与此同时他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拥有数千个兄弟:他们也都是满腔热情却失望沮丧的人。
贝塔与他的同学们恰好相反,他们因为忠于自己的祖国,一直参与各种行动,并试图在基督教或含糊不清的形上学领域中寻找根据,而贝塔却需要为自己的行动寻觅合理的基础。1943年,当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时候,城里曾传言他是因某个左翼团体的暴露而被捕。如果说在华沙的生活是天堂,那现在的贝塔就陷入了地狱的最底层,因为他被关在“集中营环境”的大门之内。那时,根据正常的顺序,他先在监狱度过了几个星期,接着他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能从这个集中营活着出来的机会非常渺茫。我们认为,贝塔像其他被运送到集中营的人一样生还无望,但在苦熬过了两年时光后,在苏联红军逼近奥斯维辛时,贝塔和其他囚犯被运到了德国城市达豪(Dachau),他在那里被美国人解救出来。关于这一切,我们都是在战后才得知的。后来他写了一部短篇小说,详尽地描述了他在“集中营环境”里所经历的一切和那里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书中得知他的经历。
贝塔离开集中营之后,定居于德国慕尼黑。他和两位同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免于难的狱友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我们在奥斯维辛”的小说,并在1946年广为流传。那本书是题献给美国第七军的,他很肯定地写道:“美国第七军把我们从达豪-阿拉赫(DachauAllach)集中营里解救出来。”后来,贝塔从慕尼黑回到了华沙,这部短篇小说得以正式出版。
我读过许多描写集中营的书,但是没有任何一本像贝塔的这本书那样令我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贝塔没有愤怒,只是——不厌其烦地叙述集中营的生活。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集中营环境”里,很快就会出现几类特殊的社会等级:最高层是集中营的管理者,他们之下就是受到集中营管理者信任的囚犯,再下一层就是那些比较精明的囚犯,他们晓得怎样为自己找到食物,以便维持精力;处于最底层的就是那些身体孱弱而头脑死板迟钝的人,因此,这些最底层的人境遇会每况愈下,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维持身体机能,他们没有力气卖苦力,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在集中营里,他们不是死于石炭酸针剂的注射,就是死于瓦斯房。当然,除了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还有大批一被运送到集中营就直接被送往瓦斯房熏死的人,这些人都是不太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贝塔在小说里清楚地描述了自己的“阶级”属性:他属于那个精明而健康的人群,并且他还吹嘘自己的精明和足智多谋。他说,在集中营里生活,头脑里时刻要绷紧一根弦,因为生死一瞬间。人必须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必须知道何时会遇到危险,同时更要知道怎样规避危险,有时候要表现出某种盲目服从,有时候要故意疏忽,有时候还要采取必要的欺诈或者行贿手段。在贝塔的一个短篇小说中,他详细地描写了他在一天之中化险为夷的种种经历:
1.有一次,一个卫兵要给他一个面包,但若要拿到这个面包,他必须先越过防护沟,这条沟是条警戒线,如果发现有人越过这条线,在那边站岗的卫兵就有权开枪打死他们。一个卫兵打死一个人,便可获得三天假期,外加5马克奖励。贝塔知道这个卫兵的意图,便拒绝了这一诱惑。
2.还有一次,一个卫兵听见贝塔在向其他囚犯讲述有关夺取基辅的消息。贝塔为了防止这个卫兵去告发,给自己招惹麻烦,他就通过一个中间人给这个卫兵送去了一只老式手表作为贿赂。
3.后来,贝塔通过迅速执行命令,从一个非常狡黠的集中营的监工眼皮底下溜走了。我在下面将引述该书中的某些段落(这里说的是希腊囚犯们的事情,他们个个身体羸弱,但为了让他们能一起列队行走,为了惩罚他们,德国人就把棍子绑在他们每个人的腿上,监督这些人的是一个叫安德烈的俄国人):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撞到了我。我跳开了,摘下帽子。监工翁特斯哈尔夫·赫莱尔,曾是一位来自哈尔曼兹的地主,跳下自行车,满脸通红,愤怒地说:
“你们这个疯子劳动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些行走的人脚上都绑着棍子?现在是上工时间!”
“他们不会走路。”
“如果不会走路!就毙了他们!先生你知道吗,又有一只鹅死了。”
“你为什么像个傻狗一样站在那儿?”那位监工冲着我大声喊,“叫安德烈赶紧收拾一下他们。滚!”
我赶紧趁机抄小路溜掉了。
“安德烈,干掉他们!”监工命令着!
安德烈抓起一根棍子,打得他们头破血流。一个希腊人用手捂着头,尖声嚎叫着,终于跌倒在地。那时,安德烈就把棍子插到他的喉咙里,开始来回搅动。我很快回到了我自己的地方。
这就是贝塔描述的、他为逃避危险而经历的一天。同时,贝塔还描述了他与其他囚犯,即与俄国人伊万之间进行的复杂游戏。最先是伊万偷了贝塔的半块肥皂,贝塔为了报复他,耐心地等待时机。他有意识地通过非常复杂的渠道(因为不想让伊万猜到是他所为)告发了伊万,说他偷了鹅,引起一番搜查。后来鹅找到了,但是伊万却早已被德国人杀死,这事就此摆平。
贝塔为此感到非常自豪,说他成功了,而那些头脑不够精明的人,死亡很快就会临头。贝塔在自己的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说,自己一直穿得很得体,身体很健壮,同时还有足够的食物,他的这种自足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他写道:“人们不停地扭动着身体以避免挨打,为了果腹、没有饥饿感,他们就去吃草和泥巴,他们总是失魂落魄地行走着,简直像是行尸走肉。”——他就是这样形容曾与自己关在一起的囚犯们。贝塔描写自己时,是这样说的:“如果早饭时,我吃了夹着半块五花肉和大蒜的面包,外加一罐炼乳,那我劳动起来就有力气。”贝塔在描述自己所穿的衣服细节时(在他周围大部分人都是半裸着身体,衣衫褴褛)说:“我走进树阴时,我把上衣放在下面,为的是不弄脏我的丝绸衬衣着重号是我加的。——切斯瓦夫·米沃什,这样才好入睡。我们谁能得到片刻休息,那完全看个人的本事。”这正是一幕不同“阶层”的鲜明对比。另一名囚犯贝克尔将被扔进焚尸炉中烧死,因为他太虚弱了,毫无用处:这时,在双层木床的边沿一个白发苍苍的大脑袋从下面升上来,两只眼睛不安地看着我们,还向我们眨眼。后来看出了是贝克尔,他的脸是扭曲的,显得尤为衰老。
“塔戴克,我想求你一件事。”
“说吧!”我弯腰对他说。
“塔戴克,我快要进烟囱了。”
我又把腰弯得更低一些,离他很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是安详而又空虚的。
“塔戴克,我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你给我弄一点吃的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晚上了。”此时,卡吉克在我膝盖上拍了一巴掌。
“你认识这个犹太人?”
“他叫贝克尔。”我悄声回答。
“你,犹太人,爬到床上来,给你吃的!等你吃饱喝足了,你再带着残羹剩饭到烟囱里去。快爬到床上来吧!我不会在这里睡觉,在这里睡觉会招虱子。”然后他对我说:
“塔戴克,”他抓着我的肩膀,“你过来,我这里有一块好吃的苹果派,我妈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