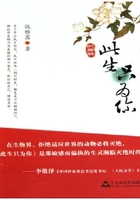胤愼出言要为弘历许配藩王之长公主,言语间斩钉截铁,毫无半点可以转圜的空间,连大婚日期都已经定下,弘历没想过会是这样消息,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只愣愣地看着胤愼。
胤愼又说道:“雅格公主乃是藩疆长公主,从小博览群书,心思不凡,深得其族上下爱戴和恭敬,正福晋要首选贤良淑德的女子,其他都是小事,至于侧福晋,我也已有过打算,军机大臣马齐的女儿还不错,性子随和,没什么是非,有这两个人给你辅助,我能放心些。”
大殿一时静极,郭公公见弘历只傻站着,看看他,又看看胤愼,忙小声笑道:“阿哥还不谢恩。”
弘历不动,只是他的双手却开始握紧,眉毛也深深皱了起来。
只见其定定地看着雍正,说道:“为什么要谢恩?我几时说过我要娶她们了?”
郭公公脸色大变,胤愼也蹙起了眉,说道:“你说什么?”
弘历一字一句地说道:“谢皇阿玛好意,只是这两个好福晋,孩儿无福消受。”
说毕,转身便走。
胤愼喝道:“站住。”
弘历只得站身,却不回头。
胤愼坐起了身子,微微喘息,看他说道:“你的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只是你要记住你的身份,自古以来,皇子婚姻向来皇室来定,岂能由你自己说风是风,说雨是雨?雅格公主的事我已经和藩王商议妥了,你若不娶,怎么收场?”
弘历脸色悄然涨红,侧头说道:“是皇阿玛商议的,不是孩儿商议的,皇阿玛若觉得不好收场,就干脆替孩儿娶了她两个,她二人一步登天,想必也更喜欢些!”
“放肆!”胤愼忽然从龙椅中站起身来,起得太猛,险些跌倒,郭公公见胤愼要下来,忙小心翼翼搀扶着,一边宽劝胤愼,一边叫‘四阿哥’,眼睛紧张地盯着这个,又看看那个,心跳如鼓。
胤愼站了半日,走下龙椅,走到弘历身边,喘息了喘息,说道:“你听好了,这事就此定下,下月初六,皇宫将举办册封福晋仪式,这是皇令,如果你还想当这个阿哥,就按照我的旨意做事,没有商议的空隙。”言毕,厉声对郭公公说道:“扶我回去!”
弘历眼冒血丝,银牙暗咬,胸中一股激越澎湃的情感冲涌外撞,忽然沉声说道:“孩儿宁可抗旨不尊,宁可不要这个阿哥身份,也决意不娶她二人为妻!皇阿玛如果执意要孩儿从命,就请现在下令,撤销孩儿阿哥之尊,贬我为庶民!”
说完,将衣衫一拦,‘嗵’的一声跪在地上,声音在寂静的大殿闻之惊心。
弘历一字一句,让胤愼大为震撼,顷时又气又惊,又悲又怒,不由回身瞪视弘历,指着说道:“好个撤销阿哥身份,好个贬为庶民,我费尽心力,养你这么大,就等来这样一个结果,好!好!——”
方说到此,忽觉一股悲戚冲进脑中,值气恼,震惊,怨恨,失望,许多滋味共同涌至,瞬间天旋地转,身如棉絮,双眼一翻,向后便倒。
郭公公大骇,忙勉励撑着,口中大叫:“圣上!”
弘历还怔怔听着,忽见胤愼竟晕倒,忙三步两步抢至身前,叫了几声‘皇阿玛’,胤愼只紧抿双唇,脸色铁青,弘历不由心中生悲,此时此刻,便是有万事也只得先放下,一把将胤愼背起来,背到大殿之后的暖塌上放下,这边一迭声地忙叫人找太医来。
胤愼并不是什么大病,乃是一时情急冲心,只是如今其年渐老,前时每常也病,又兼此一悲,便有些禁不住,太医开了一些养心安神,退火顺气的汤药,弘历见胤愼于病榻上虚弱气短,满头花白发丝,大没往日气宇轩昂之状,不觉也心中生愧,悔自己一时冲动,生出决绝之言,‘若皇阿玛因我一气如何,我何以自处?’少不得每日殷勤伺候,虽心中坚定不娶公主等人之意,却再不提前话。
此一事生,皇宫渐知弘历决意不娶藩疆公主,和圣上顶撞,藩王因族地尚有事务,此来耽搁已久,不日便带着公主回去了,面上依旧不乏礼数,是否得知议论,旁人也不得而知,只是藩王一走,宫廷暗中的话语开始悄然多起来,如渗船之水,止都止不住。
且说亲王府这边,黛玉这日因梨蕊初放,一时动了诗性,便命紫鹃铺纸研磨,自凝神作了几首梨花诗,方写了两首,因忽想不得一词出处,向书架上翻了半日,奈何拿来的书甚少,一时也没有,因想起亲王一早便宫里去了,此刻并没在家,何不去他那边查阅一番,遂放下毛笔,摇摇至亲王书房找去了。
因亲王此前早将书房独对黛玉开放,黛玉也常去看书,并没避讳,一时悠然来至书房外面,方要推门,忽闻屋中似有人声,仔细听去,正是福晋,亲王两个,黛玉心中生思:原来阿玛早回来了,为何如此悄悄,没人报知?
见他二人似乎有话要谈,便要先行回避,忽闻福晋一声长叹,中杂哽咽,说道:“我只叹这两个孩子命苦,明明是佳眷一对,此事一成,定然再难见面了,叫人怎不伤心。”
此音幽然,黛玉还是听了个分明,虽福晋并未明说是谁,其心中却忽然一动,知多半与己有关,脚下难以再动,且先不走,只痴痴站于窗下,静听其言。
亲王声音低沉,小声说道:“历儿为不娶藩疆公主,不日前违拗了四哥,说出不作阿哥的话来,四哥此病,也是由此悲怒而发,这些阿哥里面,四哥向来是最看重历儿的,今番闹到这步田地,也难叫人不叹。”
福晋忙说道:“可还有转圜的余地?——实在不行,我就宫里去一趟,求求裕妃和齐妃等人。”
亲王苦笑道;“四哥的性子我清楚,只要他认定值得的事,不会有丝毫商议余地,历儿这一点也正是像了他,才有今日之事,——他父子这回杠上,定不是小风雨,真真不知如何收场。”
言毕,默叹一声,又说道:“此事我再想办法,且先别让玉儿知道。”
福晋不言,唯闻幽泣。
黛玉听到‘娶藩疆公主,违拗圣上’几个字,只觉如雷击电掣的一般,瞬间将眼睛凝住了,许久,才依稀知道发生了何事,一时步履轻盈,脚如踏绵,幽然出了院子。
此时日影中移,渐起春风,将许多还没有来得及开绽的花朵扯下枝头,粉红的花瓣漫天飘舞,飘到黛玉头上身上,静静坠落脚下,空气中淡淡花粉香气,沁人心脾,黛玉只茫然前行,浑然不觉,似若未闻,一时脑中怔怔痴痴,不知从何处来,亦不知要向何处去,只是茫然地走。
并不知过了多久,还是湘儿处一个端茶伺候的小丫头看到黛玉,因和她笑着问好,见其形容古怪,心中诧异,便跑去告诉紫鹃,只说:“林姑娘正花园那边逛呢,叫她也不应,问话也不答,眼中痴痴的,欲哭不哭,欲笑不笑,也不知道何故。”
紫鹃听了,忙循着丫头所说之地寻黛玉去,彼时黛玉已经走出花园,来到荷花池边,春风悠悠,卷起其裙裾衣衫,飘飘荡荡,似仙凌波,脚步轻盈,茫然前去,半点没有止歇意思,遥遥看去,竟似要去池水中一般。
紫鹃心中顿时大骇,忙叫一声‘姑娘’,跑上前来,一把将其搀住,笑道:“姑娘做什么去。”
黛玉悄悄歪头,悄然一笑,说道:“我去看看他去。”
紫鹃一听,心中便有些纳闷狐疑,只觉黛玉有些不对,忙扯着黛玉往回走,笑道:“姑娘才不是要去亲王书房的?”
黛玉方才脑筋混乱不清,如纸苍白,如今听紫鹃说起‘去书房’几个字,渐渐将混乱的心智清晰了几分,好半晌,方微微一笑,幽然说道:“不去了,扶我回去罢。”紫鹃不知内里乾坤,只得又扶其回去。
一时到了家,黛玉竟半丝力气也无,软软向桌边一坐,双臂轻轻搭在桌边,便如雕像一般,紫鹃忙沏了一杯热茶放了桌上,在一边站着,小心翼翼伺候,黛玉笑道:“我且略歇歇,你们去罢。”
紫鹃见状,‘哎’了一声,一步一回头地去了,那边念红也早见黛玉古怪,只门外直向紫鹃招手,好询问何故,不提。
且说屋内煞时安静,窗子半开,风吹过黛玉鬓角,头发,粉绣纱衣,黛玉眯着眼睛,一动不动,许久,方在心中暗暗叹息一声,说道:“还是来了,躲不过的。”
一时目光痴凝,渐渐有水雾丝丝缕缕弥漫而上,脸上却仍是淡淡的笑,许多个声音在心中交乱错杂,争吵不止,而这一次,黛玉渐渐偏向了一方,心中自道:
‘如果四哥哥真向圣意妥协,立时福晋,侧福晋皆环绕身旁,到那个时候,你又是谁?纵他真的恪守承诺来接你,那时无数佳丽,千百粉黛,每日与你争宠寻隙的人无数,许多妻妾,和你共同分享一个夫君,纵两情相悦,又有何趣儿?’
转念思之,‘若四哥哥铁意为你脱离皇家,被贬庶民,今后必定身背不忠不孝之罪,终日遭人非议,便是他果真情系于你,并不计较,想他自小锦衣玉食惯了的人,今后布衣粗食,锈水冲茶,受尽其苦,你见在眼里,心中又焉能过得去?’
左右不妥,进退不能,不忍为,不能为,不愿为,一时心中酸楚无限,哀绪百生,只觉事到如今,一切混乱,都是因自己而起,不由将泪珠滚滚而下,大为灰心黯然,长叹一声,自语道:“若没了你,一切就好了。”
“什么都是刚刚好,只你是多余的。”
此一句幽幽咽咽,如同鬼哭。
便见其悠然站起,行至窗边,窗上一盆怒放的兰花,黛玉自用小勺慢慢自花盆中翘出一方手帕来,轻轻打开,现出一粒黑色小蕊,正是妙玉当日所赠双蕊中的一个。
黛玉不由得想起当日妙玉所说‘黑者有怪毒,便沾上一些,定立即无知无觉,长眠不醒’一话来,不觉幽然一笑,叹道:“可是为我今日所赠哉?”
便含泪慢慢将黑蕊置于口中,将桌上温茶吞下,心中哽咽道:“阿玛,额娘,原谅玉儿不孝罢。”
悄悄回到床上,自盖上被子,眼神飘然,许久,心底悄然一句:“四哥哥,玉儿走了,你不要再为难。”
许多过往旧事开始在眼前一一浮现,呼之欲出,栩栩如生,黛玉又看到弘历初进贾府的那一刻,看到他初见她时,似曾相识的痴然,看到弘历大踏步子走进潇湘馆,呵呵笑着说他来了,衣袂生风,唇间带笑。
她又看到那日,弘历突然抓着她的手,手臂上青筋爆出,眼中藏火,哑声说出一句‘不能这样——’,靠着树,那样孤单地滑坐下去。
黛玉闭上眼睛,眼泪悄然落进枕上,瞬间无踪。
“你若喜欢,咱们就这府里一直住下去,不闻外事,不见外人,就只你我二人,如何?”
“你放心,到了时候,我会和阿玛请求婚事,今日的举动,我会负责——”
黛玉的脸上微微一笑,细若不见:四哥哥,我以为只要坚强,就不会有过不去的事,现在才终于明白,你我皆是凡人,很多事情,我们左右不得,包括自己的命运。
五指悄然打开,手中帕子一点点垂落地上,长风涌进,将帕子吹赶至床脚,如断线的风筝,飘簌无依。
这一日弘历右眼一直跳个不止,心中总是狂躁烦乱,不知为何,此时方于胤愼处出来不久,正欲回去,刚行至钟翠楼边,猛然似觉心口如被人猛击一锤,双眼忽然昏黑一片,一股腥甜瞬间涌至喉咙,‘哇’的一声,竟吐出一大口血来,扶着朱红檐柱,才勉强没有晕倒,心却惊天动地的狂跳。
身边侍女小厮无数,见弘历突然吐血,顿时大惊,忙上前搀扶,口舌纷繁,殷勤询问。
弘历脑子嗡嗡作响,身子忽然虚飘飘的,周身无力,双手微颤,下人无数错杂之声,远得如在天边,一句也难听真切,只是冥冥中,似有一个声音,幽幽叫着他,似有一个人,正在渐渐离他远去,这种分离之感如此真实,令其只觉如肝肠寸断般,疼痛难忍。
下人们见弘历眼睛呆呆的,脸苍白无血,都有些吓坏了,许久,方见一小太监悄声说道:“四阿哥且先回寝宫去罢,咱们去请太医来。”
弘历迟钝地摇摇头,说了一句:“不用。”
忽似乎想起什么一般,便拨开众人,意欲外面去,走了几步,忽然又觉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大家忙又簇拥上来,紧紧搀着,弘历喘息一阵,突然哑声说道:“叫四喜来。”
宫女们面面相觑,那太监赔笑道:“四阿哥可是有事吩咐?——且先看了太医不迟。”
弘历未等他说完,情绪忽然激动,吼道:“废什么话!”
那太监周身一震,见弘历眼睛发红,忙敛神垂目,一叠声地说‘是’,慌忙跑下去了,弘历定了定神,想到自己这边一堆人聚着,被人看见,又未免多事,便慢慢向寝宫行去。
早有人告诉浣纱,绣儿情况,未到寝宫,两人便已经迎出来,见弘历神弱气迷,悠悠然有不支之像,心中大惊,一时便手忙脚乱铺垫打扇地伺候,弘历只说‘没事’,口中没有别的,只是让‘快叫四喜来’,一时四喜来了,跪问何事,弘历吩咐道:‘速去亲王府,看看林妹妹怎样了’。
四喜微微一怔,见弘历催得急,忙答应去了,浣纱,绣儿等见弘历破天荒地在这许多人面前提起黛玉,关心之情,毫不掩饰,也觉诧异,一时面面相觑,却也不能多说。
这边四喜去了,弘历只觉焦心似焚,坐立难安,心中如有千万牛毛细针戳扎,不得安宁,好容易等到半夜,方听丫头报说‘四喜回来了’,弘历忙亲迎出去,急问怎样。
便见四喜白白脸儿,眼神飘忽不安,犹豫不敢说话,弘历再三相问,方听其垂头敛气,小声说道:“回爷,林姑娘不好了。”
弘历心忽地一沉,便看着他问:“怎么不好?”
四喜声音更小,说:“林姑娘吞了药,现在昏迷不醒,亲王府现在都乱了套了。”
弘历愣了片刻,一字一字回味四喜话中意思,想到最后,只剩下‘吞了药,昏迷不醒’几字。
便见弘历忽然大步跨出门去,自去马厩中将白马牵出来,一下跨将上去,几个小太监跟出来,陪笑道:“阿哥且慢,待咱们回禀了圣上,阿哥再出门不迟。”
弘历理都不理,马鞭一甩,便听一个太监‘哎哟’一声,脸上着了一下,又一鞭落于马身,只见骏马嘶声扬蹄,一路向宫外奔去,其他拦路的太监见这架势,深恐自己被马蹄践踏,哪敢再拦?忙堪堪避开,弘历衣衫烈烈而动,双臂青筋泛出,一语不发,疾驰而去,如有鬼催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