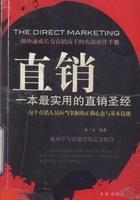我与谦益彼此安静,立于树下。此刻静下心来,我方觉身旁不远处有一道小小的溪流,溪水包裹在夜的静谧中悄悄流淌而去,如同讲故事的老人有着永远不急切的节奏,平缓而平静。
我转头看谦益,他的脸忽而闪出一种奇特的光,一闪一闪,面庞的棱角越见分明,映衬着他最后那句“且看鹿死谁手!”别有一番言语难尽的狂狷诡秘。
谦益眼射冷光,拧眉挥袖,向空中扫去,我惊觉他的意图,不假思索的大叫,“别伤它!它只是想找它的妻子——”
他骤然停手,僵硬的滞在半空,错愕的回眸看我。一只小小的、闪发亮光的萤火虫全然不知先前的凶险,在谦益脸旁又盘旋滞留了片刻才翩翩飞去。五月的夜晚,潮湿的溪畔草地,一只孤零零的萤火虫,忽闪着亮光,施施然渐飞渐远。
我想起了小时候,哥带我去乡下捉萤火虫……
“它或许迷路了。”我不无感伤的自言自语。
谦益极不自然的收回手,声音有些古怪,“丫头怎知它在找自己的妻子?”
我陷入儿时的记忆,“曾经有人跟我说,每一只萤火虫身体里都住了一个战死沙场的男人的魂魄。夜里,每当男人思念自己的妻子,就会燃烧自己,照亮找寻妻子的前路。”
这自然是当时的“战争片谜”——哥臆造的故事,但那时却深深打动了我小小傻傻的心。我将这个故事珍藏进心,但凡见到萤火虫,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它。
我后来知道,萤火虫夜晚发光确实有求偶的功能,并且大多数萤火虫的种类中,雄虫有发光器,而雌虫无发光器或发光器较不发达。因此人们看到的那些发光的萤火虫多为雄虫。哥编造的故事倒也不失其合理之处。
我轻轻一笑,抬起头来,顿觉气氛不对,谦益正用一双眸子紧紧瞅我,眸中激荡着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前所未见,似融化的星辉就要流霰出来……我本能的后退。
谦益真诚的,向我缓缓伸手,“丫头,回到我身边来,好吗?”
“不……不可能。”我敛笑迎视谦益。
谦益迈步,“丫头,你是我的妻……该回到我身边来。”
我边退边摇头,坚定道:“不可能,那场大火之后,世上就没有了慕容植语,也没有了你的景王妃,你的妻。”
“丫头。”谦益缓步向我靠近,“你我都知道,你仍是我妻,为何拒绝回来?”
“你问我为何?这时候你还问我为何?”我有些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只能发出嘲讽似的冷嗤,“发生了那么多事,你到现在还来问我为何?你不觉好笑?”
“丫头,过去的事便让它过去……”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强求我回到你身边?就让我成为你的过去,不好吗?”又何必用那温温柔柔的姿态唤我回到你身边?
谦益直直的看我,他眉微弯,似不懂我在想什么,他认真的考量,“丫头,你想我怎样?你还要何?”
我苦笑,你不懂我,我也不懂你,你不是已将一切看在眼里?又怎能问我还想要什么?“我只想你放过我,我什么都不要,只求你放过我。不要再来招惹我,我什么都不要。”
“包括我的心,丫头也不要了?”谦益沉默一刻,低幽幽似随意问起,声线却难掩颤意。
我心里忽震,不说话,不敢轻易说话,顾左右而言他,道:“其实现今很好,你争你的大洛皇位,我做我的淼水公主……‘心’之一字,太过沉重,不如两袖一甩,潇洒释怀……”
“掏出我的心给你,丫头也不要了,是吗?”谦益没等我说完,又状似不经意的溢出一句,执着,不容我回避的相问,加重了尾音。
我霎时乱转眼珠,不知该如何应答才好。
“回答我,丫头!”见我眸光闪躲,久久不回话,谦益重音震我。
经这一震,我浑身一个激灵,蓦地有了勇气。对自己说道,既然你要说,那就索性把所有的事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铿锵道:“是,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可以当发生过的事不存在,你可以若无其事的当那是一场梦。但,我不可以,我满心欢喜期待的孩子没有了,我全心全意等待的你的心也早就属于别的女人了,我是什么感受你知道么?你……”
“丫头,”我话未完,谦益抢道:“孩子没了,我也难受,但你我还年轻,总还能再有孩子……”
“呵,你难受?”我冷哼,“你根本不曾期待过我怀上你的孩子,何来难受?我知道你一直在避孕,你在睡前的饮品里添加浸过地血的子午草,你用地血来避孕,以为我不知么?”
这样的指责谦益并不惊讶,他必然知道我发现了药房里那只隐蔽的机关药柜,我与磬儿离开时,并未粉饰太平。
“是,”谦益坦然承认,“我确在服用地血避孕。只是丫头,我大业在即,了无胜算,如何能添个孩子受人制肘?那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但无论怎样,他总是我的亲骨肉,他没了,你伤心,我又岂会不难过?”
“至于我的心,丫头想说我给了宁毓儿?”谦益急切的看着我,“没错,我是喜欢宁毓儿。她的楚楚柔弱,温顺乖巧……大多男人不会不喜欢这样温柔善良的女子。我接近她,对她好,有一半原因也是喜欢她给我的宁静感觉。但喜欢不是爱,丫头,我不爱她,又岂会将心给了她?更何况她在我眼里只是……”
“不需说了!”爱?喜欢?还有什么可解释?我冷冷道:“说这些还有何意义?又能挽回什么呢?心死了就是死了,冻死的心,还能回暖吗?你不要我肚里的孩子,你不爱我,你可以有理由,可以有借口,我只是伤心,只是难过。可你知道我为何死心吗?因为我发现,你从头到尾都不是我爱的那个竹谦益!我在王府花园遇刺,你就在我身边,你就微笑着看着我,你只要一个动作,一句话就能救我……”
说道此处,谦益脸色大变,我讥诮的冷笑,“但你没有,你什么都没做!我那时,那么爱你,爱你的火焰几乎能将我自己融化……而你呢?你只是眼睁睁看着我死!”我一字字强调,“你可以眼睁睁看着我死!其心之冷,其人之狠,我如何不寒心?面对如此冷酷无情之人,我还有何理由说服自己重回你怀抱?”
听到我的话,谦益一脸不能置信,讷讷半晌无语,“丫头,你……”
我扬首,“我其实看清了,那一箭本就是刺向我的,箭头对准了我的左胸……以你的武功造诣,你难道不知那里有个刺客?景王府的花园并不易找,王妃的行踪外人更难知晓,那个刺客如果不是景王府的人,如何能自由进出,来去无踪?然而,以你的能耐,几月过去,却仍查不出那名刺客的踪影?除了有心放纵,还能如何解释?”我句句逼向谦益。
谦益面呈痛色,始终不说一句话。
“你说话啊,你告诉我,是我想错了,事实不是这样。”我直视谦益,倒真希望这一刻他能告诉我,我想错了。可他别开了头,他没有否认,他不敢再看我。
我深深呼出口气,了然道,“你说不出,对吗?我说的是事实,你无话反驳,对吗?”我曾希望是我想错了,我曾希望谦益不是那样一个冷酷无情、见死不救的人。
然,事实又一次证明,他确实冷酷无情。
我长叹一声,转身离去。
谦益仍矗立在原处,造一道萧索孤长的背影。他没有唤我,没有说一句话。直到我的身影快消失在他眼前,他猛然大叫一声,“丫头……”后面的话,他低了下去,我没能听见。
我没有转身,我的裙裾滑过脚下草叶,奏响“咝咝”的声音,我一步步走着自己的路,心里载满说不出的感觉。似轻松,也似沉重。我的双眸,激荡出青碧碧,黑沉沉的夜色,浸透了山峦青石的坚毅,眸光折转在脚下草地,再遥远飘去。
就这么结束了吧?
就这么结束。
之后的日子,我再不肯与谦益单独交谈,再也不重提那个夜晚未完的话题。
每日,他仍亲自下厨为我做膳食,为我煲汤,仍是淡泊自然的与我闲聊。似乎不久前的那个夜晚已然自他记忆中删除,那夜的话语也已被他抹去的干干净净。
他开始每日忙碌起来。他在他的军帐内,会晤他的将领与我的将领。军营里每日飞来飞去的信鸽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我一直不知道谦益在忙什么,他有意将我与他做的事屏蔽开。
直到有一日,他终于允许索里见我,我方明白他在做什么。
恍然记起,某一夜,睡梦中,有人在我耳边嘀咕的话,“丫头,你看着,静静看着,我一定将你想要的一切双手奉送到你面前,你只要看着,我为你做一切。”
原来,什么都还没结束,他还在处心积虑的帮我抢那张淼水国的龙椅!
索里谈及谦益时,眼中全是崇拜,虽偶尔对他的毒辣手段稍有微词,但从头到尾没停止过崇拜。
我不知道谦益用了怎样的方法,在尔水制造了各种神怪事件,竟令淼水国民深信不疑。譬如尔水河惊现金身淼水神像,神像有文,预示我乃淼水神转世。又譬如天空无端端出现无字天书,书中载有天机,天机中暗指淼水国的真龙天子就是妮雅公主。
淼水国民本来就极端信奉巫蛊鬼神,谦益利用这点,巧妙的蛊惑了民心,又令军心大乱。
接下来,他令几万大洛士兵换上“青”军军服,以奇袭的闪电战巧夺十数城镇。每个城镇都由他精心挑选而定。再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使得假“青”军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攻陷城镇之后,兵士们又以作秀方式尽现良好军纪。
这样,短短时日之内,谦益不仅将我“神化”,为我的“青”军塑造出一个军纪严明,军民一家亲的亲民形象。更亲手打造了一个“百战不败”的战神级人物——索里将军,威震淼水。就如盛唐时期的“战神”李靖,未开战已能令对手闻风丧胆。
一切功绩最终划归到我的帐上。
不知不觉中,谦益的所作所为,将原本的皇位争夺战变成了正义与邪恶之战。我的“青”军也立时变身为清剿伪皇叛臣的正义之师,威武之师。一时间,前来投军报效的人争先恐后,多过星辰。就连三次攻打尔水失败的离耶,一回头,竟又多出数倍的叛军前去投奔。那些原本都在观望徘徊的朝臣兵将们更是纷纷“弃暗投明”,转投我麾下。
一时恢弘景象令人难以言语尽述。小小的淼水国在短时日内,似乎斗转星移,乾坤就要移位了。
看着谦益以霹雳手段打开新局面,我不禁摇头,他可以利用怪力乱神,控制人心。他也可以利用威慑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更可以为得民心,先施毒,再解毒……小小的淼水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种种手段,他无所不用。
可日后淼水国史书上只会如此记载:青帝妮雅,天命所授,雄才伟略……青军气势如虹,携谨仁之心攻伪皇之恶,势如破竹……
这就是他为我做的一切,然,这些是我想要的吗?谦益,是你不懂我,还是我不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