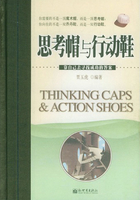不知又睡了多久,再醒来,榻前坐着双手托腮,因困乏疲惫而频频点头的磬儿。我出声唤她,她揉了揉眼,方清醒,突然噌噌跑出帐篷,稍顷端来一盅炖品,央我喝下。
我浅尝了口,笑道:“你怎会煲紫河车炖鹿胎?”我又细品了品,赞道:“加了熟地黄、枸杞子、巴戟天……你几时学了这一手?这绝妙味道怕是天下没几人追得上了。只是太过费时费事,真真难为你了。”
我细喝而尽,磬儿接回盅钵,眨眼一笑,“公主要谢便谢王爷吧。奴婢只负责看好柴火,这炖品可是王爷的手艺。就连您今儿的膳食也都是王爷亲手做的。”
“你说什么?!这是……?”我眼珠圆睁,怕就要掉出来。嫁予谦益半年,我从不知他会厨房事务,岂知他竟有如此精湛绝妙的手艺。
磬儿掩嘴痴痴而笑,“公主,奴婢初时也是吓了一大跳,可是王爷会的事实在太多,奴婢都吓不过来了。”
我神情微滞,不觉间顺口问道:“他还会什么?”
磬儿挨我坐下,细细说来,“那个荣沐老上假王妃的陵墓来问您的事,他与奴婢聊天时说,王爷上懂天文,下知地理,诗、书、礼、乐,文治,武功无一不精,不过这些奴婢都没见过。奴婢就见过王爷在您……在假王妃墓前坐了几个时辰,在树叶上刻诗。刻完后树叶两面的诗文都不一样。听人说后来王爷让祝管家把叶子送到了帝都的‘聚宝斋’,原本一个傲慢无礼、拒不见客的石姓老头,居然躬身出迎。”
雕叶子?……心型紫金笺……使用双面镂空雕法的诗词……天啊!那些哥赞不绝口的东西,难道出自谦益之手?
我甩了甩头,出自他手又能如何?我在乎这些吗?
我显然不在乎。
我现在在乎的只是……我一把抓住磬儿的手,“磬儿,跟我说说这几月来,大洛发生了什么事,帝都发生了什么事,还有楚……”
“奉王爷令,请公主殿下出帐一叙。”我话未问完,一个洛朝士官在帐口大声宣告。
我只得端庄威仪了声音,起身对帐口道:“请回禀王爷,本宫稍后即到。”
士官未走,又道:“王爷命属下恭候公主殿下金驾。”
我无法,只好让磬儿快快帮我梳理妥贴。
端庄了仪表后,我走出帐外,只见天似墨盘,玉珠繁繁。
士官与几个侍卫提灯引路,领我出了营地,上了一座浅浅小小的山坡。山坡平缓,脚下有一条似刚被人清理出来的小路。
我走微微倾斜的斜坡,眼前一树一灯一人。
一人席地而坐,盘膝之上置了把琴,琴声袅袅,丝滑如绸若缎。又似行云流水,天籁梵音。曲调渐高,我心随音去,心中展开一卷画轴。
万丈海崖石上立有一青衫渺客,睥睨天下,长风梳裳,衣裾飘扬。惊涛骇浪压不住他指点江山的咄咄之势,暴风骤雨冲不走他目空一切的狂狷不羁。他带着独步天下的淡泊儒谦,一笑却如罂粟花开,绝美绝毒。花开致艳,他敛色一跃,长剑轻挥,漫天花雨旋他身侧簌簌而下,阔袖划过,天地间浪残石碎……
这一刻,曲音嘎然而止。树上灯下盘膝而坐的谦益起身回眸一笑。他沐于灯光中,缥缈夜空,星辰黯淡。他低低唤我,“丫头来了?可愿奏上一曲?”
我摇头走近,“你唤我来,只为奏曲么?”
侍卫们早悄然隐去,谦益临风而立,不答我话,幽然道:“数月以来,丫头受苦了。”
“不苦。”我望着繁星言语极度不善,任山风吹撩裙裾。肉体之苦苦不过心灵折磨。
“丫头恨我?”谦益走至我身侧,侧脸瞅我,良久方得这一句。
“我为何要恨你?”我曾经恨过自己,现在怕你,却没恨过你,这是实话。
“我……不是——丫头心中的好人吧……”谦益自问自叹。
我冷雅而笑,“我,也不是好人。”
谦益跟着一笑,“是啊,你我都不是好人。这世上原本就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为欲念操控之人。”
我不苟同,“人若为欲念操控,做了违心之事,岂不已是坏人?又怎会没有坏人?”
谦益谦和摇头,“丫头,只做违心之事算不得真坏人。坏人哪那般容易修成?真正的坏人,要抛身,抛心,抛情,抛义,抛人性……没几十年苦心修行成不了。所以世上真坏人其实不多,最多的,是欲成坏人偏未能功德圆满的恶人。”
“那么,”我冷淡看着谦益,“你自认是坏人还是恶人?”
谦益没有看我,兀自凝视远天,答非所问,“世上没有谁天生就愿做恶人,不是被自己的欲念逼迫就是被旁人的欲念逼迫,走上无法回头的为恶之路,开弓总是没有回头箭……到最后成全的只是那句至理名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轻轻一笑,不置一词。谦益迎风跨出一步,回眸,混着邪恶的气质,罂粟花般笑得颠倒众生。我一愣,忽而想起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波德莱尔说过的一句话,“邪恶中开出的花朵,才更加美丽,更加打动人,因为它的不易。”
这是否也可以解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呢?
致毒之物,总有着难以名状的致命诱惑。致坏的极品男人也一样吧?我荒诞的想着,谦益似毒药,泛着诡异无害的迷人光彩,引人沦陷。潜光似解药,撞破人心中沉沦的迷罩……
服了解药之人,还会中毒吗?
我思绪未止,谦益已再度出声,无尽的感叹勾出自嘲似的一笑,“我大抵还只是个接近坏人的恶人,怕是这辈子也修不成真坏人了。”
我没深究谦益的话,心里始终盘算着如何能从他口中套出帝都发生的事,套出潜光的消息。
我寻思良久,出口时转移了话题,“你既无事,明日,我令人将你送我的遗物物归原主。”那里面的东西,即便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也不动分毫,为得就是“完璧归赵”。
谦益稍有不悦,挑眉,“送了你,便是你的,无需还我。”他若有所思的看我,旋即似乎会意我问出那话的目的,浅浅一笑,“况我夺嫡大业胜败终未定论,言我无事,为时过早了。”
我紧紧追问,“胜负还未在你掌握之中?”
谦益脸上挂着了然的笑,“丫头想知道什么,旦问无妨,不需拐弯抹角。”
我以为他不会轻易告诉我帝都发生的事,没想竟这么畅快,我直接问道:“我想知道帝都究竟发生了何事?”终是没敢首问潜光的消息。
谦益顺口接道:“太子拥兵弑上谋逆,致父皇于逸莲山遇袭驾鹤西去,皇后与左相力护太子登基,未成。太后矫诏拥立七弟为帝,扬言肃清叛臣逆将,右相护之,亦未登基得逞。此双方各自为政,正攻伐不让……”
“矫诏?”皇上早有立楚王之心,怎会是矫诏?
谦益不当回事的笑了笑,“所谓矫诏,不过天下文人虚言之,做不得真。”
“天下文人虚言之?”我一惊,“莫不是你做的手脚?”
谦益大笑,“傻丫头。父皇去时,太过匆匆,未能留下只言片语,断不会有遗命。再遥想此前,他虽惯宠七弟,却也从未透露过废嫡立庶之意。如今太后贸然请出父皇遗诏,诏令曰,皇位传予七子楚王。而皇后亦能请出父皇立太子为储的诏令。试想,此非常时候,太后与皇后两道传位诏令,谁人是真,谁人是假?天下文人又非庸才,谁人肯信?而我,只是在旁扇扇风罢了,我又岂能左右天下文人的笔头?”
我紧蹙眉,谦益无疑承认了他煽动文人笔头作乱——果然好狠的手段。如此一来,楚王即便日后坐上皇位,也将落得个名不正言不顺。
我转接下一个问题,“那么太子谋逆之事可当真?与你又有何关系?”
谦益敛笑顿了顿,眼中忽闪一抹狠毒的凌厉,言语却依然平缓无波,“我倒将太子炼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不错,皆因我暗中谋划布局,太子方被激,拥兵谋逆。太后与父皇急于引我犯上作乱,就为趁早将我诛杀干净,我岂能轻易称了他们的心?他们毕竟低估了我。他们不是不防太子吗?逸莲山上意欲将我诛灭,没想反遭了太子袭杀,父皇怕是到了下面也难瞑目吧?”
谦益面上蒙上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冷寒之笑,“父皇最终死于他最忠孝仁义的儿子之手,可真是上天作弄呢。”
我追问,“所以你趁势让太子与楚王相争,自己坐收渔利?”
“错了,丫头。”谦益斜睨我,“若无我的支撑,你以为太子能与老七抗衡多久?太子门下百数死士伏击老七,竟只重伤了他!不足一月,老七又重返了庙堂。他可真是天纵奇才。”
谦益的眸光深邃起来,恍似陷入了回忆,“老七自小聪颖,有天人之姿。少时,意气风发,曾以一剑‘天外飞仙’纵横江湖,几无敌手。又以区区弱冠之龄为万军之帅,威震西北,因其睿智仁德之名折服异邦沙陀来朝……此一桩桩,一件件……志大才疏的太子岂是老七的敌手?更遑论,老七背后,可是太后。”
谦益言中,谈及楚王,毫不掩饰的参杂了滚滚而来的浓浓妒意。
他又看向远处,狠蹙双眉,“若非太后老了,太子又是她一手抚养长大,历来也是尽心侍奉着她,她与父皇终是不忍苛待太子。方才百密一疏,失算了他。否则,时至今日,逸莲山就是我的断魂处,我就只是一捧黄土了,哪里还能有我余下的计较?”
谦益停了下来,我没有接话,他不知又想到了什么,言辞竟变得戚戚凄凄,漫出无限自怜自叹之意,“在父皇心中,我却是连太子也不如。”
“你羡慕太子?”我问。
谦益看我,柔和了冷峭的表情,“丫头,天下之大,若说羡慕,我唯一羡慕者,却是老七。”
“楚王?”我略惊,他羡慕潜光作何?
谦益眼中涵着羡慕之光细述,“老七的出生受父皇万般期待,他的成长更受父皇千般重视。父皇为他请来‘天下第一剑’为武师,文才无二的‘桃源先生’为教习……他自小率性而为,无论犯下何等过错,父皇总是一笑而过,不予追究。只因他的母妃是父皇最爱的女人……她死了,父皇便将对她的爱也给了老七。甚至,只要老七愿意,天下至尊的皇位于他都是探囊取物。”
“人人夸他睿智,率性……至情至性。太后、母妃们喜欢他,宫女、太监们喜欢他,朝中百臣及家眷们也喜欢他……他生来凝聚了众人眸光,他什么也无须做,什么也无须忍耐,不需任何努力就可博得所有人的喜爱。他可以鄙视至高无上的皇位。可以轻而易举得到想要的一切……”
谦益的声音,如海上卷来的巨浪,渐涌渐高,终于高至一处,却又轰然倒塌下来,没了大浪滔滔的气势,瞬间幻化成一条平静的小河,河水潺潺流去,无声无息。
我明白,眼前之人又将本欲喷薄而出的一切情绪隐忍下去了。妒嫉也好,羡慕也罢,又都被他忍了下去,如烟云消散。
只剩他眼中精光不灭,口中平和徐缓的继续说道:“父皇仍是将皇位给了他,纵使他不要,却还是给了他。那么,我就让他当得名不正言不顺。他要为父皇报仇斩杀太子,我就偏偏在暗中扶植太子,让他一刻不得清闲。”
“当初,他已将自己与夺嫡之争撇得清清楚楚,如今被太后卷了进来,早失了先机,薄了胜算。这场游戏,他只能依照我的规矩来玩。且看鹿死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