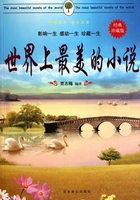李莫展的脸上却没有露出得色,反倒幽声叹了口气。
“莫展为何叹气?”王大爷赶紧问道。
李莫展答道:“我刚回到黑猫岭镇,父亲尸骨未寒,家中三十余口人尽数罹难,正应该是我悲恸欲绝的时候,我却在花前月下唱着不着调的靡靡之音,真是罪过啊!”
听了这话,王大爷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莫展又说道:“如果我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本应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全家人的尸骸,殓装入土,而我却寻思着先给自己盖一座碉楼。我简直是个禽兽不如的畜生!”一边说着,他竟一边狠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声响很是清脆,想必他根本就没有留力。
王大爷赶紧说:“莫展,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节哀顺变吧。”
李莫展两颊已然红肿,他又抱了抱拳,说:“王镇长,我刚才失态了,真是抱歉。但这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不能一错再错下去了,房子可以不忙着盖,但法事却一点也不能耽误。我想请王镇长帮忙,今天就把藏龙山归来寺的圆通法师请来,为我惨死的全家老小做最次最隆重的法事。”
王大爷握住了李莫展的双手,说:“好的,我马上就派家丁赶到藏龙山延请圆通法师,你就放心吧。”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甚是诚恳,但站在一旁的陈郎中却发现王大爷的眼神很是闪烁,心中似乎藏着什么难以言说的秘密。他同时也发现,神探赵麻子那满是脓疱的脸上,也浮现出古怪的神情,仿佛哭笑不得一般。
为什么当话题牵涉到圆通法师的时候,王大爷和赵麻子的表现都是如此诡异呢?难道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秘密?陈郎中的心中,不由生起重重疑窦。
王大爷当即就召来了一个信得过的家丁,吩咐他立刻动身前往藏龙山的归来寺。而赵麻子则去了义庄,探查那具在野狗沟里发现的无名男尸的情形。李莫展回了李家大宅,请来佃户为他掘地搜寻家人的骨骸。
寻思着再呆在王家宅子里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陈郎中回到了西医诊所。刚处理完几个头疼脑热的乡民,收了一点散碎银子之后,诊所的布帘忽然一扬,从外面走进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王大爷。
陈郎中赶紧站了起来,作了个揖,说:“王大爷,您找我有事?”
王大爷点了点头,然后努了努嘴,示意换个隐秘的地方谈话。陈郎中只得将王大爷带入了张秃子惨死的那间病房中,此时张秃子和那个乡民的骨骸已经被团丁送到了义庄,但屋里依然弥漫着一股怪异的血腥气息。
王大爷直接开门见山道:“郎中,我知道你的观察力很是敏锐,想必刚才从我和神探赵麻子的神色中,看出了一点蹊跷?”
“呃……”见王大爷如此直接,竟有些让陈郎中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确实,王大爷找到陈郎中,正是想谈谈关于圆通法师的事。其实,王大爷明白,陈郎中冰不清楚他和赵麻子与圆通法师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他之所以会如此开诚布公,正是想让陈郎中不要再胡思乱想。
现在这个时候,王大爷最怕有人胡思乱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十年前圆通削发为僧前,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同时也是王大爷最好的朋友。圆通遁入空门前,设计并主持修建的最后一幢宅子正是王家大宅。
他作出出家的决定很是突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前知道这个消息。当王大爷听说后,赶紧跑到了圆通家,询问详情。圆通什么都没说,他只是从手指上摘下一粒绿玉戒指,交给了王大爷。他说:“王大爷,你是镇长,想必日后镇里一定会发生古怪的案子。如果遇到了连你都无法解决的案子,就让人带着这粒戒指去省城找一个叫赵麻子的人。只要他到了黑猫岭,绝对可以替你解开一切难题。”
在那个时候,赵麻子并不出名,王大爷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出于对好友的信任,他还是接过戒指,戴在了手指上。之后,圆通走进自己家里的密室中,半个时辰后,王大爷觉得有点不对劲,踢开了密室的铁门,才发现圆通已经用钢针刺了自己的眼睛、耳朵,并喝下了哑药。圆通遁入空门后,王大爷还派了几个亲信去省城打听赵麻子的消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省城里有这么一个人。
但让王大爷没想到的是,仅仅只过了一年,省城那边就传来消息,说一个刚来到省城警局的外乡人,竟连破大案,成了警局里的神探。而这个人,正是赵麻子。
说完之后,王大爷正色说道:“郎中,我想你一定也猜到,圆通与赵麻子之间,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不然,我也不能用圆通给我的绿玉戒指请来日理万机的神探赵麻子。但是我没想到张秃子的死竟会牵扯出病房下的地道,地道又牵扯出圆通,现在我也不知道赵麻子会不会秉公处理这起案子……”
圆通法师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才被那个亲信家丁背来黑猫岭镇,直接送到了点着油灯的镇公所中。圆通五十多岁,很瘦,瘦得皮包骨头。要不是他还喘着气,乍一看上去,就和那三个死状惨烈的死者没什么区别。两个眼眶中一片空洞的圆通,身披一件很是肮脏的红色袈裟,袈裟很大,看上去不像是他穿着袈裟,倒像是袈裟穿着他。
一看到圆通,王大爷就不由得叹了口气,对陈郎中说:“这十年,圆通过得太苦了。出家前,他可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啊。现在瘦成这个样,他真的是以身在伺佛啊!”
这还是陈郎中到黑猫岭五年来第一次见到圆通,不由向王大爷问道:“圆通又聋又哑又瞎,你的家丁是用什么办法把他叫来的?总不至于一到归来寺,就将他背在背上带回来吧?”
王大爷笑了笑,说:“家丁只要用手指在圆通法师的手掌上写字,就能让他知道要做什么事。”
原来如此。陈郎中走到了圆通身边,虽然明知圆通看不见他,但他还是毕恭毕敬行了个礼,用手指在圆通的掌心写了几个字:“法师您好,我是镇里的西医师陈郎中。”
圆通的面上却毫无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陈郎中本还想问问圆通,是否知道王家宅子地底的秘道,这时他却听到身后传来赵麻子严厉的喝斥:“圆通是最有嫌疑在王家宅子里修建地道的人,陈先生,你不能单独和他用指画的手段说话。所有的问题都得由我亲自来问!”
本来赵麻子这么说倒也是无可厚非,毕竟他才是侦探。但他的语气却是太过于严厉了,这让陈郎中心中很是不舒服,他没好气地回敬道:“谁都知道你和圆通法师颇有渊源,让你一个人问,谁又敢肯定你能够秉公执法?”
这一句话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般,赵麻子勃然大怒道:“真是岂有此理,我在省城混了近十年,就算是皇帝老子我也敢拉下马,从来没一个人说过我贪赃枉法。人正不怕影斜,就算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呵呵,我们都知道张秃子死在了你的病房里,谁又能肯定不是你在租下了王镇长的偏院后,没有偷偷挖一条地道呢?”
“那王大爷能够凭借圆通给的一枚绿玉戒指请到你这大名鼎鼎的神探到偏远的黑猫岭镇来,你和圆通法师又有什么关联呢?”因为知道圆通法师听不见自己所说的话,陈郎中说起话来也是毫无顾忌。
“哼!”赵麻子拉长了脸,他满脸的脓疱顿时显得更加骇人。他顿了顿,朗声说道:“不错,我以前是认识圆通法师,他出家前是我的表哥。幼时我父母双亡,正是靠他做泥瓦匠挣钱抚养我长大。不过,我赵麻子向来都是认事不认人,如果王镇长宅子里的地道确实是圆通修建的,几起命案也与他有关,我定然会亲手捉拿他,绝不会顾及半点面子。最多不过在他伏法后,我自断双腕,以补偿他的抚养之恩!今日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为我赵麻子做个见证!”
此话一出,倒让陈郎中感到了不好意思,他赶紧道歉,说自己只是基于公正的立场上,才误会了赵麻子,请神探收回刚才所说的话。赵麻子却冷冷地望了一眼陈郎中,掷地有声地说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当着王大爷和陈郎中的面,赵麻子坐在了圆通法师的面前,用手指在圆通的掌心写着字,一边写,一边对王大爷和陈郎中解释道:“我这是在问他,知不知道王家宅子的地底有一条地道。为了避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身份,他并不知道我就是他的表弟。”
话音落下之后,他也停下了手指的动作。而这时,圆通忽然露出了笑容,尽管他不能说话,但也能看出那是一种欣慰的笑容。但只是一刹那,他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激动的表情。他满脸通红地一把捉过赵麻子的手,使劲写着什么。
赵麻子凝神分辨着圆通所写的字,等圆通写完后,赵麻子才悠悠长叹了一口气,说:“圆通告诉我,他早已一心伺佛,过往的事他都记不得了。”
王大爷和陈郎中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赵麻子又伸出手指,在圆通的掌心上写着什么。他说道:“我现在告诉圆通,这条地道或许关系着三条人命,希望他看在人命关天的份上,告诉我真相。”
三个人都在等待着圆通的回答,可圆通却蓦地缩回了手掌,藏在了肮脏的袈裟袍子中。他本来就没有眼珠,此时眼皮耷拉了下来,不再理会赵麻子了。
赵麻子无奈地叹了一声,说“唉,要是换了旁人,或许我早就大刑伺候了,饶是再刚强的汉子,在我设计的大刑之下,也不怕他不说出心底的秘密来。可惜,就算圆通不是我的表哥,我也不能对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老人动刑,那是会触犯天颜折寿的。”
这句话在陈郎中耳中听来,倒是别有一番滋味。他认为赵麻子所说的大刑应该不是什么酷刑,而是用坊间传说的安眠针来诱问。不过圆通是哑巴,注射了安眠针也没法说话,更不能用手指写字,安眠针对于他来说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赵麻子并非他口中的“不愿为”,而是“不能为”。
眼看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陈郎中只好和王大爷、赵麻子走出了镇公所,就在出门的时候,听到从长街东头李家大宅那边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抬眼望去,长街上出现若干火把,由远及近,正是李莫展带着一群帮他修房子的佃户向镇公所走来。
见到镇公所外的三人,李莫展连忙抱拳道:“刚才听包子铺的李二娘说,她看到圆通法师已经被请到了镇公所,我在李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豆油炒制的素斋,想请法师过去。”
“哦?这么快就修好了厨房?”王大爷问道。
李莫展波澜不惊地答道:“一想到圆通法师今天会到黑猫岭,我就让佃户们没有急着建碉楼,倒是先修好厨房和饭厅,买来了豆油和素菜,又请李二娘帮忙烹饪。不管怎么,我都不能亏待了法师才是。”
王大爷还是略感有点失望地说:“呵呵,本来我让小女娇娇为法师准备了一桌精致素食,还想请你和郎中、赵神探一起来吃的。不过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那还是让法师到你那里去吧,千万别浪费了好菜。”
说话之际,王大爷看到了穿着一身黑衣的包子铺老板娘李二娘,提着一个竹篮,正从镇公所外经过,向镇口她自己的包子铺走去。他不禁向李莫展努了努嘴,暗示怎么他没留李二娘在大宅里一同晚餐。
李莫展明白了王大爷的意思,只好无奈地说:“李二娘做好了饭食执意要回她的铺子里,她还要为婆婆煮晚饭,怎么也不肯在我那里一起吃晚饭。”
王大爷叹了口气,说:“唉,李二娘真是个苦命的人,十年前土匪攻打黑猫岭镇,也就是前任镇长罗大爷死的那时候,她的丈夫李二哥神秘失踪了。那时我还没到黑猫岭,她还被乡民们称为李二姐呢。听说李二哥是个老实人,大棒都敲不出一个屁来,乡民们都说他被土匪拉去不是做了下等苦力,就是当了土匪练马刀的活靶子。”
这事陈郎中倒也有所耳闻,知道李二娘为了照顾李二哥的母亲和与李二哥所生的两个小孩,才在镇口开了一家包子铺,每日起早贪黑。如今两个小孩都已十五六岁了,李二哥的母亲也还健在。镇里人都说,日后一定要为李二姐立上一面贞节牌坊。
圆通法师去李家大宅的时候,是李莫展亲自背着他的。李莫展在离开镇公所的时候,对王大爷说:“王镇长,我那边现在只修好了厨房与饭厅,卧室与厢房还没有修建。一会儿吃完了素餐,我还得叨扰一下您家。请您为我准备一间卧室,还为圆通法师也准备一间。”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王大爷豪气爽朗地答道。
陈郎中无意中朝李莫展背着的圆通法师望了一眼,忽然发现圆通此刻浑身正剧烈地颤抖着。似乎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恐惧。
圆通心中究竟是恐惧着什么?陈郎中不禁暗自猜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