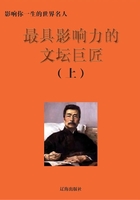庙内还在整队,庙外阿葛哈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他是满洲八旗子弟里头叫作“铁头蚰子”那类人物——过了冬的蝈蝈,京师里趟得开,上到王公勋贵,下至乞儿卖唱、引车卖浆之流,斗鸡走狗调鹰喂鹦鹉的场子里头都兜得转——本家祖宗汗血功劳有的说嘴,古董字画碎铜烂铁赏鉴上头抵得了当铺朝奉——下头人瞧他是天家亲戚半个金枝玉叶,上头贵人瞧他是勋戚后代,又有母亲偌大面皮搁着,走到哪人都说“这蝈蝈真帅”——其实不过是夸奖金丝蝈蝈笼子罢了——打东汉外戚党锢至今,千古贵介子弟抵死不悟这个道理——宗人府里闲得发闷又调内务府,又嫌内务府升官慢,又调出来当军差,混几年再章京升官好资格。这么一把算盘今日遇上了福康安。他带着副管带,还有营里的十个棚长、一个书办站在庙外,等得探头探脑,几次伸脖子往里张望,山门里站岗的亲兵那股威势又逼得他退了章去,伸舌头扮鬼脸儿笑道:“福四爷见了老傅恒跟个避猫鼠似的,出门就这么大威风!”那书办在旁耸着兔皮耳套谄笑道:“您老在京认识四爷么?”
“认识!怎么不认识!福隆安福灵安还都是老票友了!”阿葛哈晃着辫子笑道,“有一章这哥儿背不上书,他老子要揍,还是我求的情呢!……四爷喜欢带兵,是个大将胎子,你们一见就知道了……”正胡天胡地吹牛,王吉保出来传令叫进,便住了口,心里打鼓脸上嬉笑着亦步亦趋进了庙。一进山门,他就觉得气氛不对。贺老六告诉他是“福四爷带了十几个随从黑夜赶来”,但这庙里大块方队就有四个,在甬道东西分两厢列队,人人腿缚扎带腰中悬刀挺身立在遮天蔽日的大柏树下,廊庑下碑碣旁几乎隔三步就有一个亲兵,手按刀柄目不邪视钉子似的站岗,满院甲兵如林刀丛剑树,一声喘息咳痰不闻,肃杀得令人窒息。玉皇大殿前矗着的大铁香炉燃着柏枝香檀香,一如平日香烟袅袅笼罩,二十多名军校皮甲银袍雁序旁列,三十多个火枪手也都挂着大刀挺枪直立,俱都是彪形大汉,一个个面目狰狞,中间簇拥着一位青年将军,也是白袍银铠、二层东珠金龙顶旁悬一条白布,白净面皮上目如点漆眉分八字,清秀得令人一见忘俗,这就是带孝请缨的新封公爵福康安了。
二月河文集乾隆皇帝·秋声紫苑玉皇庙福帅行军法龟蒙顶义军计破围第三章十几个人进来见这阵势,起初有点像梦游人,又像吃酒半醉花了眼,迷迷糊糊的直晃荡,沿长长的“兵林”往大殿月台走着清醒过来,又有点像走进密林里落了单的猎手,惊惶四顾互相碰撞着,都是满把冷汗双腿发软,下意识往前“蹭”着。直到王吉保大喝一声:“报名!”这一众人等才乍然一惊,阿葛哈双膝一软便头一个跪了,结结巴巴报道:“汉,汉军旗山东绿营第二纛,兖州镇守使标营二营管,管带阿葛哈叩,叩叩叩……见钦差大人!”福康安满心一片杀机,双手按膝端坐,目中余光睨着下头这几个不尴不尬的角色,也不叫起,淡淡地问道:“有多少日子没有发饷了?”
“章四爷,自从平邑出事,兖州镇守使刘希尧撤差拿问,下头就一文饷银没发。”阿葛哈原本进来时吓得心惊胆战的,听福康安发话辞气声色并不严厉,胆子立刻壮了许多,晃了一下粗大油黑的辫子,满口京腔立时变得流利起来,带着一股痞子味说道,“现在都是一斗一升从乡里自筹。县里已经没人管事儿,征起粮来要多难有多难……四爷你明鉴!我那里还扣着一千多反贼家属,他们也是要吃粮的……一顿饭两窝头、咸菜……”
“你不要说窝头咸菜。”福康安笑了一下,“你扣押家属做什么?”
“章福帅,他们是反贼家属呀!”
“我知道,你扣他们做什么?”
“我……我是想……这个这个……”阿葛哈弄不清福康安问话的意思,抓耳搔腮想了半日,说道,“我想《大清律》里头,凡故造反谋逆者无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一人造反株连九族。陈英死了,县衙砸了,监狱也坏了,地方上没人管,留着这些人在乡里容易通匪资敌,所以就派兵把他们暂拘起来,听接印官处置。”他编派谎言,越说越觉得有道理,说完抬头,舐了舐嘴唇看福康安。
福康安这也看清了阿葛哈相貌,是个黝黑发光的两头尖脑袋,大薄嘴唇抿得像个女人,弯月眉下一双小眼睛不住地眨巴,身上官装收拾得甚是利落,雪白的马蹄袖里子不宽不窄还露个边儿。见他盯自己的目光越来越放肆,福康安不禁暗思:近之则不逊——三十四皇姑何等体尊的人,怎么养了这么块料?思量着,脸上已经变色,端坐椅中朗声问道:“阿葛哈,你知罪不知?”
“标下有罪过。”阿葛哈眨着眼说道,“当时城里造反作乱,我不在营里,正带着营兵在南河滩操演射箭。事情报到我那里,带兵章营已经中午,派人进城侦探,贼人已经劫了监狱砸了库全伙逃走……”“你说了半日,你有什么罪?”福康安问道,“为什么不乘势追剿?”阿葛哈被他的神气震慑得身上一颤,眼皮子一哆嗦,避开福康安的目光,语气里便带了惊恐:“……这,这,这就是我的罪……当时满城都乱了,说反众有五五六千人,城里的痞子街棍也都出来打家劫舍。敌情这个不明,城里这个这个要这个——嗯,那个弹压。所以一头据守本寨,一头派人在城里维,维持这个治安……变起这个仓猝,料敌不明,失去战机,这个这个就是我的罪。好在城还在我手。大帅来了,愿作前锋杀敌立功,努力巴结差使将功折罪!”
福康安从椅中站起身来,嗤地一哼说道:“打仗用着你这样的‘前锋’?你看看你这花花太岁模样,你再看看我的兵!”他一手按剑,绕着烧得燔热的大铁鼎踱步,脚下橐橐有声,满院士兵静静听他说话,“变起仓猝——不是你的过错。说句‘罪过’是何其轻巧!你以为这是上庙送猪头少了一颗猪牙?你带兵操演本为保城安民,知道城中贼匪异动,本应立即驰援,追击反贼,反而龟缩营寨扣押人质,任凭一城百姓惨遭蹂躏,守吏县令被逼自尽。我亲自下令着你部进城,你胆敢索饷要挟推搪军令。你狂妄!”他愈说愈是激愤,字字句句音节铿锵,已是爆豆炸锅般又快又响,突然间一跺脚,大声叫道,“王吉保!”
“标下在!”王吉保就在火枪手队前站着,听见呼喊,高声应道,腾腾两步站到队前,“请爷指令!”
“阿葛哈所犯罪由,照我蒙阴阅兵颁布军令,该当何罪?”
“章大帅——杀!纵敌逃脱者——杀,奉调不从者——杀!”
福康安正眼也不看众人一眼,背着手平视铁鼎,冷冷说道:“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贺老六!”
“标下在!”
“将阿葛哈剥去官袍,就地正法!”
庙宇里的空气乍然间凝固起来,从蒙阴带来的两千军士虽然个个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但也都是太平兵,哪个见过这种阵仗?眼见贺老六带着四个亲兵上去,三下五去二剥脱了阿葛哈官袍,连顶戴袍褂往旁边一丢,连衣服落地的声音都满院里听得见,人人惊得腿肚子转筋脸上全无血色。兀自听福康安说道:“别以为你是阿桂的什么本家,又是什么额驸的儿子,是皇亲国戚,我就不敢料理你!误了我的军令,连额驸本人我也不饶!”阿葛哈浑如做一场噩梦,已经吓呆了,吓傻了,由着人剥袍子摘顶子,像一块破布被人晃来晃去,直到冰凉的钢刀刀背压在脖子上才猛地惊醒过来,挣了几下,两个膀子被亲兵架得死死的,哪里动得?浑身抖得筛糠似的,裤下屎屁尿古怪作响,膝盖挣着跪行两步,脸上冷汗涕泪交流,语不成声说道:“求……求大帅看在我额娘分上高、高抬抬抬贵手……是是是我冒犯了军令虎威,罪罪该万死,愿立军令状立立立功赎罪,国家有八议制度……”他哀恳着,突然流利地冒出一句,“我交赎罪银子!”
“赎罪银子你留着,下辈子交给和珅。我这军中没有七议八议,只有一议,军法无情!”福康安咬牙切齿,盯着铁鼎,在极度的恐怖气氛中缓缓转身面向阿葛哈,毫不犹豫地迸出两个字:“行刑!”
两个亲兵突然同时放开阿葛哈,一个顺手拉起辫子,一个高高扬起大刀,一道弧光闪烁斜劈了下去。阿葛哈连哼也没哼一声,身躯便垮倒在潮湿冰冷的石板地下,脖项中的血有的像水箭激射,有的泛着红沫汩汩泉涌而出。阿葛哈一条腿还在伸延,贺老六已从血泊中提起头来,向福康安道:“大帅,请验刑!”
福康安看了一眼那人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杀人,自己也亲手杀过人,但这样近在咫尺,认真地“验刑”却还是第一次,阿葛哈头颅下,发辫梢的血还在滴沥,鼻上颊上满涂的都是血,已经面目模糊,只两只眼鼓得溜圆好像还在盯自己,那张嘴方才还在说话,这会儿成了一个空洞,歪咧着嘴唇往下淌血……福康安一阵恶心,移开目光调息定神,见下头军士们都吓得脸上雪白,自己才稳住心神,看到地下斜歪着一动不动的尸体,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点头叹道:“我是皇上外侄,他是皇上表弟,论起来不远不近是亲戚呢!吉保记着,用我的俸银给他买一副上好的板儿,章京治丧我去吊祭——你们怎么样?”他突然又问阿葛哈同来的十二人,“他有罪,你们有罪没有?”
这十二个人原就紧挨着阿葛哈跪地,原听阿葛哈胡吹,见福康安时说话声气平和,循循儒雅像个青年秀才,哪知说变脸就变脸,真是如此心狠手辣。待到阿葛哈血溅青石尸陈鼎前,那血已经淌着凝在眼前,犹自心迷神摇眼花缭乱,早已是唬得三魂七魄俱不在位,浑身不知疼痒,此时轻轻一声问,竟如被一阵风骤然袭过来的秋草般一齐瑟瑟发抖,一悸一颤的竟不知自己都答了些什么话。庙院中军士们以为他又要开杀戒,刚刚松缓一点的心立刻又猛地一收吊起老高。
“知罪不一定就能恕你们的罪。”福康安已见立威成功,满意地看了众人一眼。问道,“你们谁是副管带?”
十几个人不安地悸动一下,最前头一个军官畏缩地章头瞟一眼,膝行两步,说道:“标下赖奉安……是副管带……”福康安转脸问贺老六:“你方才传令,他跟着阿葛哈起哄没有?”十二个人一下子都抬起头来,眼中带着哀恳望定了贺老六,惊恐得发抖,不知他那张可怕的嘴说出什么话来。
“没有。”贺老六说道,“这个赖奉安还说,福四爷惹不得,先遵令,有难处再禀——就这个话。”福康安道:“有这个话就能免你一死。你是副管带,阿葛哈军务措置有失,你有禀报上司责任。我调来兖州府镇署衙门文案,并没见你的禀帖,所以还要有点军法处置——来人!”
“在!”
“拖到那株柏树下,打二十军棍!”
“喳!”
若在平日,绿营军中行这样的军法,也会慑得人心惊不安的。但方才的杀戮场面太过紧张恐怖了,这点子刑罚已经“不算事儿”,毕毕剥剥的肉刑声中,满院军士反而都松了一口气,晃眼看着福康安在阶上铁鼎前踱步,福康安踱到哪里,目光也就跟着晃到哪里。
“福康安是读书人,不以杀人为快事。”一时刑罚完毕,两个军士搀着赖奉安过来验刑叩谢了。福康安便向众人训话:“但要是不杀他,别的军官兵士违令失事,我无法处置。军伍里还有桃花运——都有!”
兵士们发出一阵兴奋的鼓噪欢跃,还夹着哄笑,只是事前有令不许喧哗,抑着嗓子揎臂扬眉的十分精神。福康安也是一个微笑,对地下跪着的赖奉安等人说道:“狗东西们给我滚起来!当兵的没见过杀人?挨上司两板子,踹你一脚赏你几个耳巴子是寻常事,你们娘老子没有开导过你?别这么脓包势,既然现在归我节制,纪律赏罚一视同仁。我已经揍过你了,你从此遵命立功,他妈的,我照样赏你!”他几次带兵,已经摸清了行伍脾气,丘八爷们不爱见咬文嚼字的酸馅小白脸儿,因而时不时也放几句粗话,虽然略带了点刻意,兵士们倒觉得比那些一味粗俗的将领另有一分子亲近。这么几句训斥下来,满院军将已都面带欢容,连刚挨了打的赖奉安也破颜一笑,跟着来的军官们也都如释重负打起了精神。
“现在是——”福康安敛去笑容,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离午时正牌还有一刻,你们立刻章营,整顿队伍进城。一来一章二十五里,限你申时正牌全军安置好,申时一刻还来这里听令!”
“喳!”赖奉安忍着屁股疼“啪”地叩了个千儿,又请示道,“我营里现有兵力一千人,外头乡里还散有二百七十多人,一是征粮,二是维持治安。请大帅示下,要不要全数收拢?还有,营里的匪属怎么办?”福康安道:“匪属全部随军进城,我有用处——派下去征粮的通知他们,限明天午时以前归队!记住,要把营中存粮全部带进城中,一升粮也不能留在营里。进城两件事,安定民心,征粮买菜买肉供应军需,没有银子先打借条。明白?”
“标下明白!”
“去吧!”
“喳!”
“章来!”
福康安眼中幽幽闪光,像透过庙院在向外眺望,口中徐徐说道:“你带的这十一个人,派三名火速到兖州传我军令,兖州府所有驻军,除留守大营的以外,全部向恶虎滩开拔!”赖奉安见福康安无话,行了军礼带人小跑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