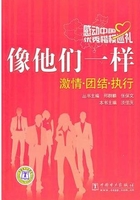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我没问你!”窦泌不甘示弱地吼她,阿妈瘪嘴轻哼,而我,却心虚地哼不出声。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宁可立马窒息得死去,也不要面对着窦泌的质问,撕心裂肺地活着。晌午的太阳,辣得人睁不开眼,窦泌比太阳还要咄咄逼人的架势,让我恨不得用一缕光的锋利刺死我的眼睛,立马瞎掉。
终于,我不敢看她,只好残忍地低下了头,以一个懦弱的姿势,刺痛她。
“所以,你这是默认了么?”她不肯罢休地问我,我保持着一顿无声的沉默,幻想自己是风,看不到,抓不到——自欺欺人地不存在。
“那么,再见了,我仇人的儿子,竺寸金。”她淡淡地回了我一句,甚至没来得及留下个告别的手势,就匆匆离去了。我知道,我们还会再碰面,但是却不再回眸。她的心已经上了锁,我没有钥匙,哪怕我心的门常年为她敞开,她也不会靠近半步,再不会。
你曾经深爱着的,是身着黑衣的人。
摘自竺寸金的心情随笔——《爱在衣冠冢》
土墙上,晒着包谷,胀鼓鼓的饱满。
吃撑了的宾客,也跟黄黄的包谷粒子似的,挺着肚子,朝着暮色而去。
日升日落,温度时高时低地起伏着,蹒跚的晃动,像是喝高了的步子,走得踉踉跄跄。阿妈也是真的醉了,扯着嗓子,趴在屋角的小木床上鬼叫。
“来呀,我们干杯!”
看来真的是喝大了,她抬着空无一物的手,结果把一整个拳头都放到了嘴里。
“唔!唔!喝!”
她嘴里口齿不清地支吾着,哪怕拳头堵了嘴,她仍在不肯罢休地喊着‘喝’。
“姜汤来了。”
我抬着姜汤走过去,就看到她把手塞进嘴巴一个劲儿地干呕起来,然后就真的吐了出来。空气像是腐烂了,散发着死鱼般的阵阵恶臭。我好像闻到了死亡的鼻息,几乎要把我憋闷到窒息的地步。
“喝,你陪我喝!”
她把我拽过去,湿哒哒的舌头舔到我脸上来。
“好好好,来,先把这姜汤给喝了。”
我坐远了些,把手里的姜汤端给她。
“我不要姜汤,你,给我过来!”
她的手高高一打,姜汤就像翻了的墨汁儿,洋洋洒洒地泼到了我手上。
“呀!好烫!”
像是坐到了炭火堆里,我烫得一屁股从小床上跳起来,条件反射地把手摸到耳垂上,哈哈地呼着气。
“你,过来!”她眯起醉得七荤八素的小眼睛,盯着我命令道:“让我好好看看你!”
我的双腿抖得像碗里颠簸的水,根本挪不开步子,她大大地打一个酒嗝,猛地一拉,把我拉到她身边。
“俊,真俊。”
她抚摸着我吓得发白的脸,赞叹的眼神,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空气像是遭了冷冻,慢而僵持地流动。我像是一个木偶,四肢全都捆了线。她开心地摆弄着,我瞪大眼睛,傻傻垂着脑袋,僵硬地在她拉线的手中扭着头。
“阿妈!”
约莫是挣扎了好久,我算是用力地把脸从她手里抽了出来,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竺老爹,别走!”
她扑过来,胖胖的胳膊重得像木桩,死死地压住了我的脖子。
“竺老爹,你不要走好不好,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看来真是喝太多了,她神志不清地抱住我,一个劲儿地喊着我阿爹的名字。
血液开始凝固,我觉得我身上缠着一条肥大的蟒蛇,紧得人喘不出气。
“阿妈,松手,”我憋红了脸说:“你醉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总算推开了她。如是一记章盖过的,天边有了赤霞。她肥肥的脸颊像是上了腮红,露着赤裸的红光。
“竺老爹,你觉得我美吗?”
她伸出比我大拇指还粗的食指,轻轻往额前干燥的卷发上一捋。霎时间风骚成了古籍中虫蛀的文字,腐朽不回。
“阿妈,”我别开头去,坚定地告诉她:“你认错人了。”
“不,不,”她固执地说:“你就是竺老爹。”
“我不是。”
“是。”
“我真不是!”
她再次靠近我,我皱起眉头推开了她。
“你别这样嘛,我好歹也是个女人。”
木窗口处的光像乍泄的春风一样灌了进来,吹起我一身的鸡皮疙瘩。她把衣服低低地拉了下去,露出半个肩头——像一颗老树,扯掉了皮:不要脸的放荡。
“要是在以胖为美的唐朝,我也是个杨贵妃呀。”
她拿手拖住脸,迷离地笑。眼角的皱纹深深的,一直笑到骨子里去。
我跳得砰砰的心,像是忽然浇了一瓢冷水,刷地一下子凉掉。
就着刺骨的寒冷,我扔下醉得一塌糊涂的阿妈,没有方向地狂奔。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儿,可是我也知道,去哪儿都好。
鬼一般的笑,鬼一般的红唇,像是沉睡在倌冢的噩梦,挥之不去。我需要离开,阿妈醒不过来,我就醉下去,找一个天寒地冻的地方,远离她:醉下去。
曲径幽幽,暮色滚滚了流年。
有朝一日,我会走出墨蓝色的游云,天空海阔。
摘自竺寸金的心情随笔——《心驰神往的怅然》
傍黑儿,流云滚滚。我抬手对天,把手印走到路上,于是一个臂膀搭向一个臂膀的距离,就这么悄悄地,拉近了十里坡底的酒家灯火,一路向北。
北角的尽头,是白记牌楼,碧波山最好的酒馆儿。老板娘姓白,当家的老板,也姓白。而这儿最著名的酒,是白酒,和这白记的姓氏一样,也和我空空的心一样,除了个称谓,剩下的:不谓酸,不谓甜,不谓苦,不谓辣,一概自斟自酌。
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快打烊了,白大娘替我把桌子擦干净,搬下一个凳子嘱咐我道“就一盏茶的时间。”我感激地称谢,却没能如愿地喝到我想喝我那种地道的白酒。耳畔一阵翻箱倒柜的声响,白大娘从酒窖里取了一坛子烈酒递给我:“只有烧酒了,才开的封,我给你热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