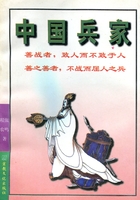想着这些,又容易把日子过成另外一种:早上起来去买杯大的冰咖啡,戴上墨镜走进办公室再换成框架方便看得清楚电脑和同事的脸,中午订廉价卖相难看的盒饭聊以果腹,下午两点有点困意恹恹却在开会的路上,稍微争论一下,就到了晚上七点,要么约了饭,要么继续加班,拐过立交桥下路口的时候,一天就算过去了。
那些暧昧在红灯前的情侣,撒娇的某个看向某个的瞬间,蓝裙子坐在户外咖啡馆自拍,等着男友买来冰茶的那个时候,或者在音乐喷泉下,小孩子还不会伸展手指比出完美的剪刀手,父母站在对面拿着手机拍照,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些都堪被珍藏,它们恰巧构成了我这个阶段暂时没有的部分,让人心生向往,可再继续,又“细思极恐”。
初夏来了,光线变得强烈,在这个时候过生日,被祝福,似乎需要这样的特殊形式以验证有好朋友并被他们惦记。
开完生日party拉着礼物往家走,大概是最难忍耐的时间。生日有个尴尬的所在,就是它提示你有所期待,似乎要获得什么,可其实,你最需要的那个人的祝福从来不会出现,当然,日常时候,这个祝福也从未存在过。
可见,满足想象这件事儿,是非常困难的。
似乎很难见到真正幸福的人,也或许他们真正的恩爱并不拿出来示人,倒是悲伤的故事常听——两个人纠结爱着最后分散的爱情便于传播。坏消息流传时,人总会映照自己的生活下,好像,即便没有爱的,也比有爱却又失去的更好受一些似的。
看微信朋友圈,这是好朋友或者半生不熟人生活形态的斗兽场:有人爱秀菜单,看得让人心里痒痒的,有人爱看生意经,有人爱做自我心理纠正,有的则把这个生生编辑成了一本《读者文摘》——这也不能代表什么,只是一一看下去会觉得有点闹,像在冬日之后迅速苏醒的各种小兽,撒开腿做各种事,并拍照留念。
夏天总像要发生什么,其实和其他季节也没有不同,这个月,好友再度失恋,另一好友正操持她盛大的婚礼,另另一个好友在相自己感觉不错的一次亲,另另另一个好友的妈妈早上被一辆汽车剐倒了,日子倾斜而下,像没法把控的照进阳台的光。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似乎有首歌在这样唱,生动的爱获得起来多不容易,还是爱一些老故事。比如好友讲“文革”时期姥爷挨批斗,楼上的老娘们儿天天在家里大喊“打倒郭永昌!打倒郭永昌!”,姥姥带着擀面杖过去敲门,开门劈头盖脸就往脸上砸,自此无事。
觉得日子无外乎这样,多爽朗,带着擀面杖回来,洗洗做碗手擀面,配上黄瓜丝和芝麻酱,吃上两大碗,能怎样呢?
过。
●哪有那么多好朋友
不要和使用两部手机的人交朋友。
不要和手机经常没电的人交朋友。
不要和手机没有密码的人交朋友。
不要和开会时不静音的人交朋友。
最惊心动魄的爱情
这是我见过的最动人心魄的爱情了。
这天,我们为公司的某个电视节目搞首映,在三里屯的某个影城,公司来了不少人帮忙,其中也包括一个平时不怎么起眼的同事。
他也算负责重要的岗位,有点儿生下来就老了的意思,走起路来像刚军训完的孩子,脖颈挺直,目不斜视,韵律非常适合喊“一二一”,我们就叫他“一二一”吧。
是的,我们就叫他“一二一先生”。他负责的岗位重要,几乎要跟所有部门的人打交道:他负责统计周一早上开例会时候迟到的人次,负责组织生日会,负责在每个年度的时候计算大家的等级和薪金。他看起来永远是克制的,不苟言笑的,虽然年纪不大,但克制让他显得比实际上坚硬一些,老一些。
他有时候也笑,但显得言不由衷,从职场的角度,又容易让被害妄想症的同事觉得阴森森的。我从来不怕他——有些人像我们人生中的分号,你可能和他并肩坐着,但你们表达的永远都不是一个意思。
我坚定地相信我自己的直觉,而后我为自己直觉找事例去证明,以显得自己的直觉很准确,对于这样的设定,我在三十岁前都很擅长。
我们相安无事地工作,在心底,我大概是想随时翻个白眼嗤之以鼻的吧,不会走得太近,也无暇留意他婚否、什么学历、最近在看什么书,即便在我上一本书出版的时候,他买了很多本,还专门告诉我,我依然是礼貌地脊背僵直地说了声谢谢。
我对自己说,不是跟每个人都要成为好友。
一二一先生结了婚,我听说。我还听说,他的妻子有点身体不好,具体的我不知道,说走路有点儿问题,但他还是坚定地结了婚。
我听说了之后,说,哦。
直到这天首映。
结束的时候,我站在走廊里迎来送往,饥肠辘辘的,带着假笑。我看到一二一先生,站在厕所门口等人,挂着他那种笑。我们点了个头,然后我看到一个女人,从厕所里走出来,比较矮,剪着短头发,戴着眼镜,面目很普通的样子,她走过来,一拐一拐的。她尽量让自己自然,但仍然无法掩饰。她走近一二一先生,挎住他,经过我。
她带着那种明亮的笑,我确定,她跟我热切地打招呼,而后说:刚才有人在问他呢,说,你怎么带着你的女儿来了?
她当然是自嘲,我笑了,然后我又为刚才自己的想法不好意思起来。他们看起来不那么般配,可在这一刻,我觉得她足够配上一二一先生。
我突然想起来了,关于一二一先生的补充八卦,说当时和老婆结婚,顶着家里巨大的压力,他不苟言笑也好,走路像军训也好,总算是个,对不起,就是普遍意义上正常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表述,但我真心为自己的庸俗感到羞耻。她明亮地笑着经过了我,像一巴掌打掉了我偷来的苹果。
另外补充的一二一先生,是说他坚定地选择了这个他喜欢的女孩儿,即便有可能,对方会因身体的问题影响生育。
我一个好朋友,总是在做情感节目,里边有各种狗血的剧情。我怕她不能负重,她说习惯就好。我排斥看到这些,总觉得,没有什么天长地久,一切都是暂时的。
当然,一切也确实是暂时的,但一二一先生的暂时可能更长一些。后来我组合了一下脑中的信息,他已经早早地在老家买了房,大概意思等到告老还乡,和这个女人,安享晚年吧。
这是我见过的最惊心动魄的爱情。
虽然她只说了一句话,虽然他没有说话,虽然工作中我们依然擦肩而过,虽然,我还是不能成为他的好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说,这是我见过最惊心动魄的爱情。
风至佛罗
在预定的情境中到达三亚龙沐湾,透过车窗看出去,白云蓝天。
这在北京极为稀有。
空气更好,像被洗过,当地的伴游说,这里每天睡五个小时就够了。
我不信,次日果然在凌晨六点醒来,前来勘景的小辛起得更早,他四点四十五分醒来,坐在酒店的阳台上看天光渐亮。我说他是文艺青年,说他在天光中梳理感情感受独处之美,他没有否认,他说,你看那些层次,是描绘不出画不出的层次啊。
我不爱住酒店,觉得它们华丽、单调,千店一面,这次却不觉得。酒店分成若干幢,我们入住5号,楼宇间被泳池包裹着,旁边是仙人掌、椰树或者其他灌木,绿得不真实,还有自动喷水设备,在热带的阳光下刺刺作响,水花飞溅。
去看海,远处是淡蓝,进入则黄一些,因为还未开发,几乎没有人迹。接近岸边的沙极细,伴游说,这里是落日海滩,夕阳最美,酒店建立时海边尽是虾田,后来才变成这样。
我们看夕阳,远方两个天色,大海尽头,一边晴,一边则闪着雷暴的样子。远远的有霹雳打在海面上,没有声响,所以我们赚到了,一次欣赏到了两种落日,那血红色的太阳,隐在半明半暗暧昧的云里,染红了整块西天。
我提议到镇上去走走,那里叫佛罗。当地人开着机动摩托车来接,像跨子,但比这个大一些。说话听不太懂,像泰语。司机是中年妇女,肤色很深,看不出年龄,似乎也没有表情。
一路上我们没法说话,因为蓬顶风极大,又是天色已黑,没有路灯,仅靠机动车的一束光来照明前路,引来无数的飞虫,啪啪地打在脸上,被撞得生疼。
说是古镇,已经有了翻新的迹象,这大概是中国城镇化的标本,都如出一辙。街上也矮矮地建着一些门脸儿,匾牌错落,各种店,都很开放的样子。门口坐着若干人闲聊,都肤色很深,穿着肉色的拖鞋,男人光着脊背,抖着腿,女人偶尔站起来拍着孩子摇晃,灯泡的光是晕黄的,让人想起八十年代的老家。
伴游说,你看他们,白天就坐在这里,一直坐到晚上。
也有电器店、化妆品店、小的超市,卖的东西和全国差不多。我走到集市里,想看看水果。佛罗被称为“蔬果之乡”,我看了大吃一惊,苹果显得干瘪且小,梨子也不是很健康的样子,葡萄就更别提,像……考试没有考好但硬着头皮回家的小孩儿。
我象征性地买了几个橘子,看着口水都流下来,应该是很酸的。卖水果的妇女招呼我说,小弟你再多买些咯。
光不是很黑,我看着她黝黑的脸说,我哪有那么小,你叫我小弟。
内心还是高兴的,又检阅自己全身,觉得一定是哪里显年轻。
她说,我今年四十。
我放下水果走了。
黑还真是看不清年龄,我说的是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