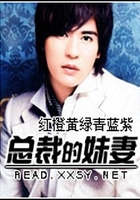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天已经是大亮了。不过这雾却是一点都没有淡去,十步之内,都看不到景物了。
将卧房整理清楚了以后,纤月和碧春都跟在杜从南的后面,另外后面还跟了几个男仆拿着东西去武场。杜从南之所以这样勤奋,为的就是自己庶出的出身,怕给杜从景看不起。总是暗地里与他较劲,所以他无论是文是武都不想输给他。
但即便是这样,杜从景似乎也没有改变过对他的看法。虽然是兄弟两人,平时见面除了打个招呼,便是形同陌路了,连杜从英都不如。有时候杜从景碰到杜从英,还会和他说上几句话。
武场上被浓厚的雾气所笼罩,白茫茫的一片。大家来到了武场边上一个亭子里,杜从南做了一下热身运动,便从男仆手中接过剑,走进武场,开始练习剑术。不一会儿,就随着灵动的步伐,隐没在浓雾里。只听到刷刷舞剑的声音。
由于浓雾,看不清周围的景物,纤月却是对这地方充满了好奇。长久以来,都是被关在听雨轩那个小院子里,没有大丫头的充许,都是不能随便出入的。
现在她的身份可以说是和碧春平起平坐了,只不过碧春年龄比她大一些,在杜府呆的时间比她久一些罢了。这会儿碧春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在雾气里时隐时现的二少爷,纤月马上就趁机溜到一边转悠去了。反正雾大,等会他练完了,她在回来,谁知道她离开过呀!
真不愧是杜府,这练武场也修建得相当的奢华,地面全铺的大理石,平坦又光滑。四面设有休息的亭子,亭子的四周都种了几棵大槐树,夏天里,便会是荫凉的一片。
纤月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似乎已经听不见杜从南练武的声音。不免有些担心,便又寻着路往回走。却见一支剑刷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吓了她一大跳。一边拍着掌嘴里一边说:“哎呀,二少爷,好剑法,呵呵,好剑法!”她已经学乖了不少。
半天没听到回应,抬头沿着剑尖朝后看去,却是杜从景的一张冷脸。吓得她又打了个哆嗦,嘿嘿讪笑着说:“啊,那个大少爷呀,剑法更好!”心底里已经把自己给骂臭了,真不知道自己倒底在说些什么。还有,现在她的状况就是,他只要一挥剑,她的小命马上就玩完。而且还不犯法,因为人家是大少爷。
杜从景脸色很不好看,却也没有搭理她,挥着剑刷刷刷地在她耳边舞得冷风嗖嗖的,吓得她闭着眼睛,高声尖叫起来。
听到这叫声,杜从南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是从纤月的嘴巴里发出来的。碧春马上跑来报告:“二少爷,纤月她不见了,这……”
杜从南立即叫上男仆一起在雾中寻找。不一会儿,便见得杜从景也在这武场上习武。只因地方太大,雾又浓,彼此都没有看到对方而已。
纤月闭着眼睛蹲在地上,杜从景在她身旁舞着剑,见到杜从南似乎空气一般。纤月听到脚步声睁开眼睛一看,大叫道:“二少爷,救我呀!”
杜从南只是抿着嘴,半天才开口叫了句:“大哥!”
杜从景这才停了下来,收起剑,说道:“自己手底下的丫头要管教好再带出来,自己丢脸不要紧,不要丢了我们杜家的脸!”说完,也不给杜从南说话的机会,转身就走了。
谁也没有说话。因为大家都看到杜从南的那双眼睛像刀一样,如果再多看上他两眼,说不定就会死在他的眼刀之下。
纤月自己心里也有数,今天虽然才刚开始,自己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惹恼了这位二少爷。如果她今天想皮肉完好无损的话,那一定都是她前世积的德。
杜从南愣愣地站了半天,才从嘴巴里挤出两个字:“回去!”
众人都大气也不敢出地跟在他身后。碧春在后面不知道给了纤月多少个白眼了。从这丫头刚来到现在,不知道惹了多少祸了。像她们这种因为疾苦而被卖进杜府的丫头们都一直是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出点什么岔子,轻则会被送进妓院,重则性命不保。
回到听雨轩,杜从南也没有给她动粗,只是让她跪到木屋外的走廊上,而自己则回了书房。这回纤月乖了不少,只不过心里还是不服气。想想自己其实也没犯多大错啊,又不是杀了人,也不是放了火,搞得人人都像是要把她生吞活剥了一样。
直到中午,这雾才算退了去,风轻日朗的,让人觉得懒洋洋地。若是平时,纤月肯定会偷偷找个地方躺着睡个午觉。可是今天,都跪了一个上午了,而且连早饭也没吃,现在都大中午的,院里的丫头们都去厨房吃饭去了,就她一人还跪在走廊上,饿得她是头昏眼花,前胸贴后背。
那些个小丫头们都没一个有良心的,各自吃完了饭回来便该干嘛干嘛去了,没一个人理会她。让她不由得开始想念起晚春,若是她在的话,肯定会想方设法给她弄点吃的。
这时,刚好碧春下来了。见四下里没人,纤月小声地叫道:“碧春姐姐,碧春姐姐,这里这里!”她一边招着手,一边左右张望着。
碧春没好气地走过来说道:“怎么了?”
“碧春姐姐,有没有什么吃的,我肚子好饿啊!”
碧春眼一翻说:“你活该,谁叫你总是这么胡来的?看你把二少爷气得,到现在也没去吃饭呢!”
“哎呀,我的好姐姐,我这不知道错了吗?你帮我想点办法吧,我都快要饿死了!”纤月苦着脸说道。
碧春却是不买帐,冷着脸说:“不饿你一回,你就不知道历害!”说完转身就走了,根本不管她的死活。
纤月跪得脚都发麻了,浑身扭个不停。长这么大她就没跪过么长时间。心里直骂这碧春太绝情。也不知道自己还有跪多长时间才算是个头。心里又冒出了逃跑的念头,可是屁大点的地方住着几十个人,她目前又犯了错,太引人注目了,能往哪儿逃呀。
这时午膳时间早已经过了,却见得刘管家带着个丫头,提了个大篮子进来。碧春忙过去将篮子接了过来,和刘总管一起上了二楼去了。
这篮子里提的当然是二少爷的午膳了,今天中午他没过去用膳,自然就会有人送过来了。但平常他若不去吃饭的话,都会提前差人过去禀报一声,只是今天一声没吭地也没打个招呼,于是这刘管家便亲自过来了一趟。当然这肯定是杜老太爷派遣的。
须臾,这刘管家便下来了,和碧春站在外边说了会儿话,又向纤月这边看了看,边朝她走来。
一定是碧春在刘管家面前说自己的坏话,纤月在心里琢磨着,不然,他好端端地照着她干嘛?
果然,这刘管家一过来就说:“你这个丫头,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杜府岂是你能随便放肆的地方,你随我来一下!”
“哦!”纤月赶紧站了起来,再跪下去,她都想直接自尽算了,真不是人受的罪。可是这一站起来,两条腿早就麻了没有知觉,若不是眼急手快,扶住了旁边的柱子,差点就扑到刘管家身上去了。她可不想让这个老东西占了便宜,长着两撇小胡子,活像个汉奸。
碧春一直在楼上看着,没有吭声。说实在的,她心里就是不服二少爷如此偏坦这个小丫头。虽然心里明白,若是哪个院里的丫头落在刘管家的手上,就是不死,也得扒层皮。但她一点也没觉得内疚。
纤月哪里会知道这刘管家的历害,一瘸一拐地跟在他的后面。心里想着,他究竟叫她去干嘛!
杜府里,大大小小的房屋有数千间之多。当然,家仆也不会少,光是刘管家手下,就有上百人。而且这刘管家在杜府里的地位也不算很低,杜家居然也给了他一套小院,供他一家几口人居住。
当刘管家把纤月带到自己院里时,看到那一套刑具,纤月总算是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了。当场就觉得头皮一阵发麻,免不了要受皮肉之苦了,奶奶地,也太缺德了吧,可是来都来了,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刘管家命男仆给她十大板,并对她说:“念你年纪尚小,且打你十板,长点记性,下次若还敢胡来,必不轻饶!”
纤月马上跪在地上直求饶:“刘管家,我错了,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昨天还被抽了几个大嘴巴,今天又要挨板子,还让不让她活命了。
刘元胡子一翘,轻哼一声说道:“杜家家规向来以严厉著称,若是这么随便让一个丫头没大没小的,还不是我这总管没当好!既然知道错了,以后就长点记性,给我打!”
凄惨的叫声在刘管家的院子里飘荡。惊得树上的小鸟扑拉拉地全都飞走了。刘管家摸着他那两撇小胡子说:“你这丫头嗓门还真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里杀人呢!”
纤月本想破口大骂,但她知道这是自找苦吃,俗话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好汉,但再怎么也不能再给自己找罪受了,还得留着这条小命继续活着不是。
自己本来活得好好的,才只有十三岁却突然得了个什么白血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结果还是挂了。谁知道再次睁眼一瞧,竟附在一苦命的小丫头身上被人贩子贩来卖了。本来想卖就卖吧,能活着也已经不错了,哪里知道在这里还真是比得白血病还恐怖,随时有可能被人拿来当只鸡来宰了。
屁股上挨了十大板,现在她是连走路也成问题了,趴在那儿一动不也动的。莫不是要爬回去不成?正想着这个问题,突然,院门口,杜从南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当杜从南看到趴在地上的纤月时,一张俊美的脸上立即是怒不可遏,大声叱道:“刘管家,谁让你打她的?”
刘管家见杜从南来了,急忙弓着腰低着头说:“二少爷,这丫头性子野,小人只是替你稍微地管教管教!”
纤月一听,这杜从南好像还是向着自己的,马上又开始在那里大呼小叫起,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哼,本少爷的丫头怎么轮到你来管教了!”说完又转身轻声问纤月:“你还好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纤月哭得是稀里哗啦,眼泪汪汪地说:“有!屁股!”她这眼泪是真的,因为确实很痛,但本来她是可以忍住的,听到有人为自己抱不平,自然而然就流出来了。
刘管家一听,一个姑娘家竟在男主子面前说出屁股两个极为不雅的字出来,皱着眉头说道:“荒唐,如此没有礼教!”但看到杜从南极为不悦的神色,也不好再次发作。
其实杜从南现在也觉得颇为尴尬,为难地问道:“那你现在还能走路吗?”
纤月摇了摇头泪珠子滚滚地掉落说:“不能,不过二少爷别担心,我还可以爬!”在他没有来之前,她确实想过要爬回去,可是现在她知道,她绝对不用爬了。
果然,杜从南又转过身对着刘管家说道:“刘管家,让你院里的丫头扶她回去!还有,随后让天容也过来一趟!”
这天容是杜府里的专用医女,一般都是为杜家的夫人和小姐看病的,而府里的丫头要是生病的话,顶多到外面去看大夫,病得太严重的,都直接送出了府外,怕留在府里传染给了主子。刘管家见杜从南竟然要天容去为一个丫头看病,不得不硬着头皮说道:“二少爷,一个小小的贱丫头,岂能劳烦医女呢?”
杜从南是真的生气了,怒道:“让你去就去,怎么那么多废话?”
刘管家见这个二少爷怒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然二少爷是庶出,生母又已经亡故,但在府里仍然深得杜老太爷和大老爷的宠爱,就算他在杜家再怎么老资格,也还是要敬他三分。忙悻悻地回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