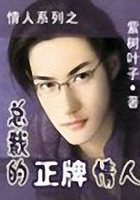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之所以具有文学艺术的因素,是因为它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特性存在又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而出现的。新闻里面有大量的事实,可是这些事实太单纯,太枯燥,太密集,太芜杂,缺少艺术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小说等文学形式里,有较强的艺术性,可是,它们所提供的事实却加进了虚构的成分,没有可靠的生活依据。一个缺少欣赏性,一个没有可信性。但是,读者在这两方面所有的欠缺感,又恰恰被报告文学这种既是真实的还是艺术的文学样式给弥补了。因为,报告文学为人们提供和文学艺术地表现了一种可信的真实,就对读者有了一种特殊的诱惑和感染力量。尤其是在社会生活出现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人们不易辨识自己的生存环境,不便进行生活选择的时候,报告文学的这种真实性就显得更加的可贵,就更加有吸引人的作用。真实既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原料,也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魅力所在。试想,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里若不表现陈景润生活和科研事迹的真实;鲁光在《中国姑娘》里若不表现女排运动员英勇拼搏的真实事迹;胡平、张胜友在《世界大串联》里若不表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纷纷走出国门的真实状况,那么,这些作品还会有如今这样的作用和力量吗?
报告文学中的真实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因素而存在的。人们很难把它和其他艺术手段清楚地区分开来。因为,如果离开了真实谈艺术,是无法进入报告文学的殿堂的。许多作家、理论家,之所以反对把报告文学看成是新闻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简单相加,原因就在于,认为在报告文学里真实和艺术实在是无法分开的一个整体。麦天枢在《西部在移民》里有这样的描写:去年,不,是前年,我们陪北京来的一帮记者去定西县黑山沟,随便进了一户人家,那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想哭:破屋里,炕上躺着个老大爷,不住嘴地吭吭,说是病了,好几天了就这么躺着,吃了几片阿司匹林,还是从队长家里借来的。身上盖一床被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堆,已经辨不清是什么颜色了,一问才知,这是1974年周总理说了话,兰州军区来挨户救济的军用被子。地上跪着一个老婆婆,怎么劝也不起来,好不容易把她扶起来,才知道老人家穿的裤子只有半截,裹过的三寸小脚没有袜子,她是怕人看见了丢人。姑娘18岁了,一直躲在土坯砌的厨房里不出来,我跟两个女记者挤进去说话,女娃娃哭了:大热天,她穿个棉背心,膀子露在外面,腰也露在外面——背心太短了;穿条好几种颜色的裤子,已经说不上是穿,像个门帘子,挂在身上——像这样严格的白描文字,表现出的严酷的真实,你能说它只有真实而没有感染力吗?这样贫穷的情景谁看后都是无法忘记的。报告文学艺术化的过程和目的,实际上就是使真实更加充分和更加有说服力。在这里,真实既是文学艺术性的起点,也是文学艺术性的终点,更是文学艺术性的基础和舞台。离开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谈论、要求和判断其文学艺术性程度如何,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谈,既不能有助于建设,也无法进行可信准确的评价。
四、典型形象的表现真实社会生活
文学艺术的特点是通过典型的形象表现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报告文学尽管表现的是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但它属于文学范畴,所以同样也应当具备这样的特点。只是报告文学在实现这个特点的过程和方法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完全相同就是了。
小说是通过艺术虚构的方法来塑造典型,用个性分明的情节和形象来感染读者。而报告文学作家的艺术活动范围就要小得多了,他只能在严格地真实范围内来实现典型化,形象生动性。人们不能对来自真实的报告文学在典型性、形象生动性方面有太多的苛求,但是,报告文学作家却不能放松在这方面的努力。因为,报告文学若是忽略或放松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就等于自觉地放松、放弃了文学的追求,这同样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取消。
报告文学的典型化,是通过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了解、研究之后,在反复地对题材对象的选择中来实现的。波列夫依在《论报纸的特写》一文中说:报告文学作家在创造典型、塑造形象时,和小说家完全不同,“他们要从生活在自己周围同时代的人们之中,找寻出一个人,这个人的生活要能够完完全全体现出他的创作意图,能够反映出时代的最最典型的特征”。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事件和人物,报告文学不可能都进行报告。报告文学作家要选择的,只能是关联着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突出的人物等方面的题材内容。在这种选择什么和不选择什么的过程中,就开始了典型化的活动。例如,乔迈的《三门李轶闻》,所报告的虽然是吉林农村的一件有关党员作风、党群关系的事,可是,因为它典型性强,就非常引人注意。乔迈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第四生产队的五名党员,在群众自愿结合,划分联产计酬作业小组时,因为多年形成的漂浮作风,“见椅子歇腿,见酒盅开胃”,严重脱离群众,如今无情地被群众冷落一旁。此后,他们认真反省,组建“党组”,一年后又赢得群众信任,和群众联合一起,共同致富的消息。
出于一个作家的敏感,乔迈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题材。对它进行报告,可以真实充分地使人们看到,党员的作风建设和榜样作用是多么的重要。很快,乔迈就深入到当地去进行认真采访,不久就写出了这篇名重一时的作品。这个作品出现在1981年那个农村社会生活刚刚开始发生新变化、新组合的环境中,发生在那个群众可以有限地左右自己的命运,一些党员干部却还在旧的思维和不健康行为轨道上滑行的时候,就有很强的震动力和启发性。《人民日报》1983年3月24日,全文予以转载。《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加的“编者按”中称,该作“表现了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难能可贵的敏感和热情”,“从党群关系方面提出了共产党人在四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做什么榜样的问题”。中共黑龙江省委,吉林省委接连发出通知,把《三门李轶闻》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整党教材”。之后,又改编为电影《不该发生的故事》在全国上映,同样引起强烈的反响。《三门李轶闻》在当时那个群众对党员存在着抱怨和期望的环境中,有着分明的典型性,所以,它的创作是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内容是否具有典型性,是作品能否引人关注,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因素。这是许多成功的报告文学一再证明了的事实。因此,也是作家必须重视的问题。
选择了具有典型价值的题材,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紧跟着的工作,就是要考虑如何形象生动地表现这个题材的问题了。报告文学表现真实的生活,是有许多方式和手段的,茅盾说:“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茅盾:《关于“报告文学”》,1937年2月20日,《中流》,第11期。(关于更加具体的表现艺术,在后面还将会作出阐述)这就是说,除过在真实性问题上不能动摇之外,报告文学的艺术天地也是十分广阔的。问题在于,作家是否能够很好的把握和运用所有的艺术手段。例如,夏衍在《包身工》里为了表现“包身工”的生活环境,他作品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浇在脸上。
这是“包身工”生活环境的逼真描写。从这个环境和她们的生活起居的一个场景,读者在还没有接触“包身工”的工作时就对其生活的艰难有了一个初步的感觉和印象。在这些描写文字中,有白描,有声音,有动作,有评论,是多么的富有形象性和现场气息啊!是多么的富有感染人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具象性的描写。还可以有比较虚泛但却也是形象的描写。例如,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里,为了表现陈景润生活科研的大环境,但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复杂的、混乱的现象又难以作具体的描写,因此,徐迟就把它虚化一下,用一种比喻的文字作了恰当的说明。作品写道: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弦。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啊。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英雄豪杰,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
这些文字,是多么的灵动美妙。它既形象,又深刻。既是凝炼的诗的语言,又是有高度概括力的评论语言。很富有文学艺术的表现力。从以上两个例证,我们足以看到,报告文学在表现真实的过程中,是完全可以实现生动形象的表现的。问题就在于作者是否有形象化地表现真实的本领。但是,不管如何,人们必须重视文学以上的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性这一点不可。因为,这一点是报告文学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主要内容,也是报告文学不同于新闻信息的明显地方。作为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无论如何也缺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