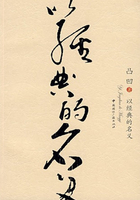就全世界范围来说,最近的这五百年(从文艺复兴算起)是社会历史大转换的时代。而后二、三百年,中国也卷了进来,近百年来尤甚。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包括它的精神文化、思想、学术……)都处在这种急速转换之中,而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甚至现在这个转换也未最终完成--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然强调要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任务;今天我们仍然把实现“现代化”、达到“小康”、以至下世纪中基本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目标。
这种转换始终伴随着“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是世纪之争,从上个世纪一直争到现在,仍然争得不亦乐乎,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争不完。当然,今天的“中西”之争同上个世纪及本世纪初,在内容和强弱对比上已大不相同,如果说当时西方文化是强势、东方文化是弱势,那么,现在二者至少在力量上处于平等地位。东方决不屈从于西方,当然我们也不要求西方屈从于东方。中西体用,古今厚薄,随时势而不断变换。
这种转换无疑还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经济上的体制更替,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的搏杀,总之,各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
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运行的。不联系着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你就不能理解许多理论命题之所以能够提出来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长时期政治和学术分不清楚,为什么学术的独立自由需要费那么大力气去争取。
因此,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历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血和泪。既充满着学术范围之外在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学术同非学术的冲突(常常是学术向非学术投降屈从),也充满着学术范围之内的中西、新旧的不同哲学立场、价值取向、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学术思想、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等等的相克、相生、争斗、融合。这中间,有强奸,也有恋爱,有死亡,也有新生。
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就是这样诞生、成长和发展的。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
它是个“混血儿”。
“内史”与“外史”结合
不少学者指出,学术史的研究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某种学术本身的内在运行轨迹,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有人称这种研究为“内史”研究;一是注重学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如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政治权力、地理和人文环境、学者个人的才性等等对学术的影响,有人称这种研究为“外史”研究。
我认为,应该“内”“外”结合,而且必须“内”“外”结合。而且学术史的客观历史本身证明,“内”与“外”总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难把“内”与“外”截然分离开来。在我们上面谈的怎样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意见当中,有的是属于所谓“内史”的内容,如“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有的则是属于所谓“外史”的内容,如“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我们是把这两个方面作为不可缺少的内容来谈的,两个方面,缺了谁都不行。单纯的“内史”研究或单纯的“外史”研究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准确把握学术运行的真实轨迹。所有学科的学术史研究都是如此,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从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一方面,文艺学学术研究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前后承续关系,不同学术流派及学术思想观念之间也的确有着内在关联,或者相互影响,或者相克相融。如果细细检索,我们会发现梁启超、王国维们文艺学学术研究足迹在后来的延伸情况,甚至一直延伸到今天;也会找到某种学术思想(如关于艺术形象问题、艺术典型问题、艺术方法问题等等)的发展、运行脉路。
学术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内在理路。必须重视研究这种内在理路。而且,学术本身应该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学者应该有抵御世俗功利浸染的能力,作学术研究应该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另一方面,文艺学学术研究又不可能不受外界社会条件、时代气息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尤其在中国,政治对文艺学的影响十分强大;其他文化因素如道德、哲学等等也对文艺学研究发生强有力的影响。当谈到外在因素对二十世纪文艺学研究的作用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看到二十世纪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变化最剧烈的一个世纪。单以中国而言,二十世纪就经历了三个朝代的更替:清帝国灭亡,国民党的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思潮运行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和发展,都是本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伟大事件;最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转型),更需引起历史性的关注。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在这种动荡和巨变中行进的。
“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有着怎样的运行轨迹?可否为它画出一个鸟瞰图?
我们之所以研究和撰写“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主要任务就是力图把握住并且描画出百年文艺学的运行轨迹,即这一百多年来古典文论(诗文评)怎样转换为现代文艺学,现代文艺学怎样生长、发展、变化,以及这中间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要想知道我们所把握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运行轨迹的具体线路,只有请读者阅读全书。然而,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想在“全书序论”中先大而化之地描出一个鸟瞰图,并且随之也顺便勾勒一下全书的结构。
根据这一百多年来文论-文艺学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把“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全书分为四部(五本,第二部分上下两卷),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四部书也可以称为四部曲,每一部有它自己丰富和复杂的内容和相对于全书来说的分主题,而在每部书的丰富内容中我们还可以分别找出其最突出的特点或“第一主题”,作者所要完成的最主要的任务。中国文论中论诗讲“诗眼”,论词讲“词眼”,论曲讲“曲眼”;现代导演说戏讲“戏核”。我所说的每一部书最突出的特点或“第一主题”,就是每一部书的“书眼”或“书核”。就是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抓住并且突出每部书的“书眼”或“书核”,即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当然每本书的内容不只是这一点,不限于这一点。那么,这四部书每部的“书核”或“书眼”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第一部:蓄势;第二部:蜕变;第三部:定格(或叫定型);第四部:突破(或叫“反叛”)。
下面稍微作一点解释。
蓄势
这是“史前史”,即“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史前”部分。这是“正史”之前的“序篇”。主要是讲文论转换的“能量”是如何积蓄起来的。
为什么要从“史前”说起呢?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文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自于宋。”为什么不以这“三百年”的开头为起点,而要追溯到宋?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因有果、互相联系着的。这“三百年”,汉学与宋学争得不可开交,倘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这样处理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我们治百年来的文艺学学术史“何自始”呢?由钱穆得到启发,我们同样不能以这百年的开头为研究的起点。
某种社会历史事物,包括学术活动、学术运动,它的发生、发展都会有其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根基,以及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起先,它可能在地下运行,或者在其他的掩体底下悄声悄气的孳生;到了一定的时候,才钻出地表露出自身面目,或摆脱掩体而独立成形。“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作为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换、以及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有“看不见”的地下运行或在其他掩体中悄然孳生的阶段。它的受孕和胚胎形成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呱呱落地之前。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在娘胎里孕育的过程。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追述近代学术思想历程时曾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我思想界亦自滋一变也。”他认为,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左右的龚自珍、魏源是“新思想”(包括文论思想)“萌蘖”中值得注意的人物。的确,龚、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上,对传统文化(包括文论)作了某些批判性的反思,对“诗教”、“道统”之类持守千余年的文学原则提出质疑,期待“大变”。其实,“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看不见”的部分,还可上溯到龚、魏之前,明末清初某些新的学术因素的出现;以及十八世纪的文论格局(乾嘉时期的学术活动和袁枚等人的诗论、文论)。还要更加注意龚、魏之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中、下叶,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睁开眼睛看世界”,传统文化遇到来自外部的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挑战和来自内部觉醒者的怀疑、批判走向终结。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正是从古典文论的终结之中蜕变而生。古典文论的终结,同时也是积蓄向现代文艺学转换的能量的过程。因此,我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第一部,它的特点(“书眼”或“书核”)用“蓄势”两个字概括。就是说,这一部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出在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之前,这种转换的“势能”是如何积蓄起来的,中国文论的内部如何在外力的冲击下造成了不得不变的趋势的。
这一长时段里已经逐渐积蓄起越来越强烈的“求变”势态和呼声,加紧做着变革的舆论准备:那些时刻关心着民族命运的志士仁人认识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们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他们提出“师夷”而“制夷”,而且,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还在思想观念及议会制度,倘观念和制度优越,则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他们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文明。例如,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留学生容闳,从1847年起在美国留学八年,中西对照,使他更加感到清王朝之黑暗腐败:“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未年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能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能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这样,经过长时期的积蓄,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变革势在必行。特别是“甲午”战败,更是一个强刺激,令人感到变革的刻不容缓。于是有“公车上书”,有“戊戌变法”,有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变革的先驱者们提出必须“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疾呼“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怜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岂能服膺”!
正是在中华民族不得不变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氛围之下,才不能不随之有文论“革命”,有新美学的萌生,或者说积蓄了文论和美学变革的巨大势能。
当然,文论和美学变革还有它自身的内在理路。
总之,用比较形象的话来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文论的转换已经是“箭在弦上”了。那么,这“箭”是如何上弦的?这“弓”是如何拉开的?这个不得不发的将要射出去的弦上之“箭”是如何积蓄能量的?这就是第一部所要讲的最突出的内容。
蜕变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至于二、三、四十年代,才真正算得上我们现在所作的“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正篇开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这时“蝉”才逐渐“蜕皮”、“出壳”,“蛹”才逐渐蜕变为“蝴蝶”,即中国现代文艺学才由“诗文评”的母体挣脱出来,发芽、生长、成型。所以,这一部总的特点我们用“蜕变”两个字来概括。
“蜕变”期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两个高潮。
从世纪之交到本世纪最初十余年是第一阶段。这是现代文艺学的草创阶段,它刚从“蛹”中往外爬。或者说它正处在从“诗文评”母体降生的过程中,脐带尚未咬断,还带着血迹;然而它的第一声啼哭是响亮有力的,露出无限生机。这也是现代文艺学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阶段,与传统的“诗文评”相比,中国文论已经从诸多方面发生明显变化。这时,文论的关注对象已经开始发生位移,小说(包括戏剧等叙事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小说的作用甚至被夸大到它自身难以承受的程度,在许多学者眼里,小说和戏剧等叙事文学已经取代诗文而成为文学的主角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的哲学基础和美学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西方的认识论哲学、进化论思想和某些美学理论已经引入,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或反映,有的学者还从真善美统一的角度对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界定;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以及范畴、概念、术语也逐渐表现出新的特点,理想、写实、悲剧、喜剧、主观、客观,新名词越来越多。总之,学术范型已经不同于以前。这阶段的成就最突出、最充分地表现在小说理论的领域里。小说理论变革的先声,是1897年严复、夏曾佑发表于《国闻报》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作者界说小说的性质是“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其事”,是“人心所构之史”;但“今日人心之构营,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不可“因其虚而薄之”。作者还从人性论的立场出发,提出小说因描写“英雄”与“男女”这人类的两大“公性情”,才“易传行远”,可以“使民开化”。该文作为第一篇试图运用新观点论说小说的长文,实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