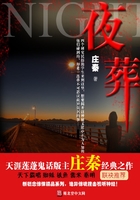细想想,四姑奶那场灾难可以避免,事后多诸葛亮,为不被人讽刺我是自作聪明放马后炮的人,不高谈阔论她老人家如何避免灾难,毕竟灾难发生了。
四姑奶来前院找我奶奶,嘴里哼着情歌《手捧伊勒哈穆克》,路过罗雀者门前,她自顾唱:
手捧伊勒哈穆克,
送给巴图鲁阿哥。
饿了你就当饭吃,
渴了你就当水喝。
鲜果放着不抗搁,
吃到嘴里甜心窝。
阿哥问我要点啥,
也要伊勒哈穆克。
阴谋者可不是把她当野草莓,当一只鸟来捕。方法有些原始,但在三江居民院常见。方法是,在门前雪地打扫出一块空地,撒上谷瘪子(未成的谷子)做诱饵,用一个大号筛子,支上一根棍子,将绳子拴在棍子上,待鸟儿进入陷阱--筛子下面,一拉绳子扣住它们,这就是成语说的门前罗雀。差异是用网和用筛子,使用的工具不同,目标一致捕鸟,日军联队长既不用筛子,也不用网,命令他的亲信军官山本五十七直接用手抓过来,四姑奶是人不是鸟,抓到的效果更好,总之她老人家在劫难逃。
“队长,今晚机会最好。”山本五十七说。
“幺细!”
“他们大部人去看电影,院里人不多。”
“她不去看电影?”吉原圭二关注窥视已久的鸟,问。
山本五十七侦察好了,今晚放映《雨暴花残》电影,索家人能去的都去了,有两个主要人物没去。四姑奶没去看电影的原因她看过这部电影,手头有一朵芙蓉花没绣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我奶奶没去,原因听来可笑,她不敢看电影,幕布上出来的人还会眨眼、说话、吃饭,明明是鬼嘛!他说:
“没去!天气不好,院子里人少……最佳时机。”
当夜清雪在西北风中飘落,雪花很小很细碎,没去看电影的人躲在屋子里做着素常做的事情,护院的炮手进了炮台,留下照顾院子的管家冷云奇,时常出来走走,院外停留工夫很短,天冷急忙回屋去。
我爷是被大家劝去的,要不然晚上他不怎么出院。去看电影不主要,看看大戏院,好多天没去那里。
“幺细!”
山本五十七马上布置,两个士兵配合他,只要鸟从门前一经过立马撇网,肯定逃不掉。等她一定时间不出现,就到她的房间直接抓人。联队长馋鸟红了眼。
四姑奶独自一个在屋子里做针线,女红稍稍好一点儿,不至于给手头的活儿难住,绣了一阵觉着不可心拆掉,再绣,花瓣怎么看都不像,今晚非要绣好它。求援,想到我奶奶,手拿花撑子(绣花工具)直接到头道院子来,正好经过吉原圭二的房间。
雪花中四姑奶唱浪漫的情歌,厄运突然降临,军人的手臂勒住她的脖子,像捉住一只毫无反抗能力的小鸟,她发不出声音,嘴塞满毛巾,眼睛也给蒙住,按倒在炕上。有人在剥她的衣服,还不是一只手,什么都没有时身体一个部位遭到侵略,听到一个男人说话,用日语说的:
“哈伊洗忒鲁依!”
四姑奶挺不懂这句“我爱你”哈伊洗忒鲁依,侵略者说的日语,自己给日本鬼子侵略了。嘴堵着喊叫等于没喊叫,在自家的大院里遭强暴却不不能呼救,反抗只是心里。
侵略者侵略累了喘息一阵,第二次侵略跟第一间隔时间不长,再次遭侵略,侵略进行时还是那句话:哈伊洗忒鲁依。
我爷好像有什么预感,心里发慌,电影没看完便独自来家,进大院见到管家,问:
“云奇,家里没什么事吧?”
冷云奇愣怔地望着东家,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呢!消消停停(安安静静)的,没出什么事儿。要说有事,先前山本五十七找他,问:“会长回来没有?”
“电影还没散场,没回来。太君有事儿?”
“他回来,马上去见联队长。”山本五十七说。
我爷一听吉原圭二找他,推测是他们回山里的事。昨天联队长说他要回白狼山。
“太君,您的脚?”
“复原了,谢谢你的照顾,你的艾蒿大大的好药!”联队长说他已经命令山里来车接他回去,车什么时候到他什么时候动身。
大概是明天车到,爷爷这样想。告别什么的,联队长吉原圭二很客气。一向聪明的爷爷现在是自作聪明,自作多情,一个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即将摆在面前,挑战他的良心和考验他老人家的智慧。
爷爷去联队长的屋子前还是先回堂屋,奶奶说:“麻溜过去吧,联队长派三七二十一来找你两趟啦。”
“山本五十七。”他纠正道。
奶奶老是发不准音,以为就是三七二十一。心想,日本人起了这么个怪名字,像是跟谁斗气似的。她说:“不管多少一,像是有什么急事找你,快去吧!”
爷爷出去,奶奶不催促他也要去。联队长叫,怠慢不得。他迈进屋子,眼前的景象他倒吸一口凉气,穿便装的吉原圭二,泥像一样坐在一张桌子前,一把抽出来的军刀横放在一块洁白的手帕上面,刀刃特别亮晃花他的眼睛,心给人攥了似的一阵比一阵紧,打招呼的声音雨淋湿墙一样胎软:
“太君队长!”
“すみません!”吉原圭二说。
爷爷对死米马森恩或狗没那撒一听懂些意思,是对不起,令他老人家迷登的是联队长突然说这话?
“すみません!”吉原圭二又说了一遍,然后瞧山本五十七,示意他翻译给他听。
“会长,队长向你道歉。”山本五十七说。
胳揪人(抓挠腋下)嘛!我爷怎么也笑不出来,没看是什么人胳揪的,日本联队长啊!老虎胳揪谁敢笑?
吉原圭二咿哩哇啦一阵东洋语,说得快加上爷爷紧张,基本听到是一阵鸟叫。
山本五十七翻译道:“队长说了他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向你谢罪,请求你制裁!”
爷爷给推到大雾里,什么也看不清。吉原圭二做了件什么事?让我制裁?借我两个胆子我敢吗?纵然我是只豹子也不敢,他有些口吃地问:“太、太君,我没明白太君的意思。”
吉原圭二这次没咿哩哇啦,只摆下头,山本五十七走向小里屋,拖出捆绑着手脚、蒙着眼、堵着嘴的人。爷爷顿觉天旋地暗,他看出那人是谁啦。
咿哩哇啦,吉原圭二日语道。
山本五十七翻译道:队长酒后失控,伤害了她……山本五十七指一下军刀,说请你当哥哥的制裁!
天哪!这不是胳揪,逼你打碎牙让你咽下去啊!制裁,真心不真心且不说,我敢拿刀捅日军联队长?那样做了,全家上几十口恐怕没谁能活成。他心里悲怆地呼唤:四妹啊,我可怜的四妹这种倒霉,倒血霉的事咋叫你摊上啊!
“你怎么还不动手?”山本五十七催逼道。
吉原圭二平静地闭着双眼,双手放在两膝上,真像等待制裁。
“杂种馅儿的!”我爷心里大骂,他老人家从来不说糙话,看来是愤怒已极。能不愤怒吗?待嫁的妹妹给祸祸(糟蹋)了,还有几天举行婚礼,这是什么事儿啊!
故事讲到这儿,我的心哆嗦,不太会讲了。狗日的吉原圭二,我非劁了你!这是三江地区最狠的刑罚,一条牛骟了就是犍子;一头猪劁了就是克朗;一个男人阉割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丧失雄性功能,把日军军官统统骟掉,省得祸害人。
多恨也没用,那时还没有我,即使有我也到不了联队长吉原圭二跟前。爷爷站在吉原圭二面前又能怎样,面对的是一块石头,自己是一只鸡蛋,撞的结果没悬念,粉身碎骨!我猜他老家不是惜命怕死,深得罪日本人丢命的是全家啊!
“索会长,你到底动不动手啊!”山本五十七逼问。
爷爷的脸变形难形容形状,丧尽天良小鬼子玩人还咋玩?劁猪割耳朵--两头受罪嘛!明知我不敢动手,偏要来这一套。逼着瓦着(又催逼又使手段)……尊严纸一样给你们折皱,非要再撕碎?
“唔,这么说你理解了这件事,那就翻过去!”山本五十七代表一个不说话的人发言,“你带她走吧!”
爷爷拉起捆绑着的四姑奶,离开日寇的房间,身后传来吉原圭二的骂人一样的道歉话:
“すみません!”
我爷拖拽着四姑奶进了当家的堂屋,直接进了自己的卧室,奶奶一个人在,他急火地说:
“插门,撂下窗户帘,吹灯!”
“你?你咋绑了四妹?”奶奶尚未从惊怔回过神来,她以为当家的绑了四姑奶,问,“她犯了什么错?”
“磨咕(磨蹭)!”爷爷嫌奶奶动作慢了,亲自吹了灯,屋子一片漆黑,责怪道,“出这么大的事,还能不让你知道吗?”
“不明不白的,急死人啦!”
“你声音小点儿,这事不能传扬出去。”爷爷说,眼睛适应一会儿黑暗,走向四姑奶准备掏出堵她嘴的毛巾,说,“四妹,你向我保证不要大喊大叫,什么事儿咱慢慢想辙。”
四姑奶使劲点头,嘴堵着发不出声音。
爷爷弄出毛巾,四姑奶大喘口气,呜,呜……憋坏啦。她稳当下来,哽咽起来,拱在奶奶的怀里孩子似的委屈起来。黑暗中沉默半天,爷爷问:“怎么回事,四妹?”
“芙蓉花绣不上,我来找大嫂,经过西屋门前,蹿出两个人勒住我的脖子……”四姑奶战惊地讲述自己被强暴过程,“眼睛蒙着,我没看清是谁,在那个屋子肯是吉原圭二。”
“是他!”爷爷说。
四姑奶又落一阵泪,问:“大哥,你说怎么办?”
唉!爷爷的叹息声好长好长。咋办?还能咋办?日军祸害中国妇女家常便饭,谁管得了他们,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天下啊!如果是一个普通士兵,凭自己三江商会会长的地位,还可以到他上司那里去控告,有没有效果还难说。吉原圭二是联队长,大佐这么高的军衔你告他,不是讨没趣,而是找祸端。
“吃红肉拉白屎……”奶奶骂吉原圭二是只白眼狼,狼才吃红肉拉白屎,她愤愤不平道,“可也不能就这么的不明不白……”
“跟小鬼子讲里表(是非)?他们嘴大咱嘴小……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
四姑奶平静下来,坐在索家里,她的勇气上来了,说:“他们只五个人,我一个人对付得了。”
“你要干什么,四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