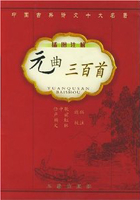首先,那次“方法论”热给予已经受到重创的庸俗社会学方法以急风暴雨般的沉重扫荡。大家知道,庸俗社会学曾经在前苏联某个时候的学术界、美学界、文艺理论界很时兴了一阵子,随后又在中国相应的领域肆虐有时,“文革”期间更加得志。庸俗社会学在中国文艺学中的突出表现是政治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而且是直接决定),给人物贴阶级标签,给作者划阶级成分,用僵硬的甚至粗暴的“进步”还是“落后”或“革命”还是“反动”的社会学判断,去代替对极其复杂的艺术现象进行艺术分析和美学分析,只对作品的内容进行简单的社会学比附而忽视对作品形式的美学和艺术研究,并从而判定作品价值的高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想的清算,对其惯用的庸俗社会学方法也一并予以批判。但这种庸俗社会学方法是一种多年痼疾,很难清除的,似乎非用“虎狼药”不可。而在“方法论”热中引入的方法可以说大都是庸俗社会学方法的“置换剂”,它们联合起来造成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一起对庸俗社会学方法进行“置换”,给予致命一击,比起以往的批判和其他的医治药方更有效,可谓对付庸俗社会学方法的一剂“虎狼药”。因为,西方来的诸多方法,虽然可能有其他毛病,但就是不会有庸俗社会学的毛病。譬如在西方很时兴过的心理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方法、语言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现象学方法、存在主义方法、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解构主义方法以及其他后现代的方法等等,还有从自然科学那里移植、借鉴来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熵定律、测不准原理等等方法,它们与庸俗社会学方法不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且大都同它格格不入,同它是“异己”,有些则几乎是它的“天敌”。它们的进入就是对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全面置换,当然也就是对庸俗社会学的消解。
其次,这次“方法论”热,造成百年来文艺学学术史上研究方法的空前活跃和从未有过的丰富多彩。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起,文论(文艺学)研究方法随着西学东渐也不断有所开拓,梁启超已开始运用建立在西方认识论基础上的的社会学方法观察文艺问题,王国维也借鉴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的思辩方法对文艺现象进行美学分析。之后,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鲁迅前期的进化论方法和后期的阶级论方法,刘西渭(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方法,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方法,周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方法,胡风的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蔡仪的思辩性的历史与美学的方法,等等,都对中国现代文艺学学术研究方法有所丰富。自四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和社会学方法逐渐在中国现代文艺学学术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到五、六十年代更获得了一种排他的独尊性。“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把认识论和社会学方法推到极致,也单一化到极致、僵化到极致、庸俗化到极致。于是,改革开放之后,事物开始向它的反面转化,不但开始跳出庸俗社会学的藩篱,而且打破了文艺学研究中千军万马走认识论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独木桥或双木桥的僵局,开辟出广阔的天地。到八十年代(特别是八五年“方法论”热)乃至九十年代,出现了文艺学学术研究方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上面提到的从西方引进和从自然科学借鉴的各种方法都试图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施展身手,而且,连中国传统的的考据学方法、知人论世方法、以意逆志方法、直感印象式的经验评点方法等等也被加以改造运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新时期的文艺学家们方法论意识被唤醒,他们自觉地追求和运用新方法(或自认为的新方法)来改造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并且提高到学理层面加以认识。例如,有的学者在谈到文艺学研究如何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时,从学理上探讨了自然科学方法对文艺学研究可能具有的意义(虽然他的探讨意见并不一定正确),认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深化了人们对客观世界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不断运动的认识,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思维方法,从而也就给予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以启发:如,从对象自身进到系统整体的把握,就使得文艺美学对艺术本质的研究不是就艺术而论艺术,而是把艺术审美活动放到人类活动的大系统中来把握,把艺术审美活动、科学认识活动、伦理实践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三个子系统,在其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中把握艺术作为第三王国、作为物化的自由的审美意识的独特本质;用自然科学的模糊思维,正好可以论述艺术的“可喻不可喻”、“可解不可解”的双重性;用耗散结构的从有序到无序、从无序到有序的理论,可以说明美和艺术历史发展的形态更替;等等。
有的学者指出,文艺学研究方法应由普遍性(辩证逻辑方法)、特殊性(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个别性(美学文艺学方法)三个层次构成,现代科学方法论处在文艺研究方法论的中间层次上,它对文艺学美学的渗透使其发生了从片面性到整体性、从封闭性到开放性、从无序性到有序性、从本体研究到关系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等一系列重大变革。更为可贵的是,在科学主义十分时兴的时候,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主义的局限。有的学者说:“‘科学方法’有点象一柄解剖刀,它是锋利的、便捷的,却也是冷峻和无情的,其操作运用的结果,在弄明白了机体的某些构造和组合的同时,常常夺取了机体的生命,它得到了艺术的躯壳,失去了艺术的精灵。”有的学者警告,不要在输入其他学科的努力中淡忘了‘文学’的涵义,躺如此,则“活泼泼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却可能重新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僵化”还有的学者呼吁扞卫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在引进自然科学方法的时候,要充分注意到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特殊性,决不能放弃文学作为“人学”的本体论价值。
再次,这次“方法论”热,大幅度地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思维途径和思维空间。以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现在是诸路神仙,各显其能。文艺社会学方法、文艺认识论方法、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等等,对于分析研究文艺与社会、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与历史等等,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分析研究文艺的内在结构、分析研究文艺的诸形式要素,则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候,新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符号学方法,则大有用武之地。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也自有其特长。文艺学家们现在已经逐渐懂得了充分发挥文艺学研究主体的多种思维途径,利用诸多不同研究方法各自的长处和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多角度、多侧面、以至于全方位地对文艺现象进行研究。文艺学家的思维,过去象鸟儿被绑住了翅膀;现在“方法论”热给翅膀送绑了,把广阔的思维空间还给了文艺学家,真有点海阔纵鱼跃天空任鸟飞的味道。有的学者以《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为题,描述了文艺学思维方式“由外到内”、“由一到多”、“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的变革趋势,对“方法论”热的成果给予积极肯定。
复次,通过“方法论”热,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有些文艺学家运用新方法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新成果。譬如林兴宅用系统论方法分析阿Q性格,虽有某些牵强之处,但也确有独到的地方。他总结出阿Q性格系统的三个特征:两重人格、退回内心、泯灭意志。在考察阿Q性格的系统质时,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其乡村流浪雇农的性质;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其作为专制主义的产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其轻度精神病患者的表征;从思想史角度看到其庄子哲学寄植者的特点;等等。再如肖君和运用系统论方法从“人对艺术的需要”这一“艺术的缘起”出发,依次考察构成艺术系统的十个层次,也颇富启示。运用引进的方法考察文艺学问题比较成功的,我认为是那些借鉴外国的某些人文学科的方法分析文艺学问题的文章。譬如王一川的修辞学美学的研究,陈晓明的解构理论的研究,吴予敏运用语义学诠释传统文论,等等。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