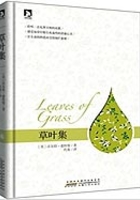各种各样的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美学译文丛书”,一套接一套地出;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或不大有名的人物甚至无名小辈),从维科到尼采、从韦勒克到佛克马、从卡西尔到苏珊朗格、从伊格尔顿到杰姆逊、从哈贝马斯到加德默尔、从罗兰巴特到福科……轮番出场或同时登台,拥挤不堪;各种各样的文艺观念,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现代派的、后现代派的,认为文艺可以定义的、认为文艺不可以定义的,等等,在各种场合反复展示;各式各样的方法,老三论、新三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也在中国文艺学的场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演练。西方文艺学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历时地出现的众多“流派”、“思潮”、“主义”,共时地出现在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场地上。上述这一切,就其积极方面来讲,的确大大拓宽了新时期文艺学的思维空间,丰富了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改造和更新了文艺学的思维结构。而且,的确取得了许多可喜的具体成果。譬如,张黎、朱立元、金元浦等的接受美学译介和研究;杨义、傅修延等的叙事学研究(特别是杨义最近出版的《中国叙事学》吸取西方叙事学研究的学术经验和方法,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的叙事学思想,获得某些突破性进展);王一川等的“语言学转向”、特别是“修辞论美学”研究;鲁枢元等的文学言语学研究(《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胡经之、周来祥等的文艺美学研究;金开诚、童庆炳、鲁枢元等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吴予敏等运用语义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诠释(1998年第3期《文学评论》吴予敏《论传统文论的语义诠释》);郑敏、陈晓明等的解构理论的研究;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等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等。
我尤其想说到对外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大家着作全集的译介所取得的成就--我指的是最近由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巴赫金全集》。这是一个好的起点。它适时地把以“对话”为中心的的非常切合当前时代特点的理论思想介绍给中国,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文艺学和人文学科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发生重要影响。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的一面。就是说,别一国家、别一民族的思想文化,是产生于别一国家、民族的土壤里,有它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适应性,在它们的国家和民族本是“会念经”的;但陡然间把它拿来直接诠释中国当前的文化问题、文论问题,难免会有“嗑嗑吧吧”、“念不成句”的情况发生。在新时期,我们所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文论、美学思想在中国“念经”时,“念”得“嗑嗑吧吧”、“念不成句”,甚至“念”得“驴唇不对马嘴”,已经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后现代”理论的引入。“后现代”在那些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具有“后现代”语境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可能是适用的;但是,不分青红皂白,硬把它拿来阐释甚至动手解决连“现代”还没有“化”好的中国情况,硬叫它对着“前现代”,“念”“后现代”的“经”,那就“驴唇不对马嘴”了。因此,借鉴外国学术文化思想,一是要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二是要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不然,它们将不只“念不成句”或“驴唇不对马嘴”,而且会得病,会“水土不服”、“呕吐腹泻”,甚至会一命呜呼。
“方法论”热
当然得“伺候”好“外来的和尚”,尽量不叫他拉肚子;另外我们也得结合中国国情来听经。
“外来的和尚”到中国来念经,其成败得失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典型。
当时中国的哲学界、美学界、文艺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求新求变的心情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急不可耐。如何实现新变?大家认为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方法的更新,以为有了新方法,就会做出新学问、写出新作品(关于创作上对西方各种各样的艺术倾向、艺术主张、写作手法的移植、模仿、学习和借鉴,如意识流以及现代派其他的各种“主义”,从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到荒诞派、黑色幽默、大地艺术、行为艺术,乃至后来的后现代的平面化、表层化、快餐化、拼贴和复制等等,姑且不论;此处只谈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于是,各界争先恐后,纷纷引进新方法、或者自以为新而在外国已经不新的方法。而且,什么样的方法都要。首先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身的方法;其次,如果认为本学科的方法不够了,那就向外学科“借”方法,例如向自然科学“借”方法,而且还要“借”那些在我们看来“最新”的方法,如所谓模糊数学的方法,耗散结构的方法,“熵”定律,“测不准”原理,等等。短短几年,几乎把西方曾经有的新的老的方法都拿过来了。不管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学”情,先拿过来甚至强行移植过来再作理会;不管对文艺学好用不好用,先用了再说,甚至有时不甚理解也要强行“征用”--这里大约用得上“文革”中常说的那句话了:理解的也执行(运用),不理解的也执行(运用),在执行(运用)中加深理解。
1985年,就是中国的文艺理论界从西方引进方法、向自然科学“借”方法、大谈方法、大用方法的最集中最热闹的一年,人们称之为“方法年”。这一年,举行了三次方法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三月厦门会议,四月扬州会议,十月武汉会议。就拿笔者所参加的扬州会议来说吧,老中青三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界,科研教学不同行当,各路学者会聚一堂争谈方法。我记得当时还特地邀请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专家(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位建筑学院的教授)、“思维科学”的研究专家(前几年才去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步研究员)与会做专题报告,陈步先生关于思维方法发生学的讲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会上谈论最多的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的借鉴和运用,大部分人持积极的赞赏的态度,有的还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借鉴和运用的体会,可以说,当时的“科学主义”倾向明显地压过了“人文主义”倾向。但是就在那次会上,也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反抗”。刚刚出道不久的宗白华教授的弟子刘小枫,风风火火赶来,听了许多颂扬“科学主义”的发言,颇不以为然,他在发言中泼了一瓢冷水,认为在文学领域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属于“末流”,人生的问题是不能靠自然科学来解决的,哈姆莱特的“活着还是不活”的问题,任何计算机也解决不了。他撂下这个发言让大家思考了好一阵子,自己匆忙赶往谋职的深圳大学。
从总体上说,我认为那次“方法论”热虽然不是没有问题,甚至今天看来有不少可以吸取的教训;但我仍然给予积极的评价,肯定它在新时期文艺学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