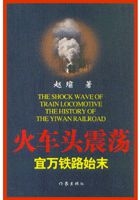很显然,韩玄子实际上在不断地拖着时代前进的后腿,起着消极的促退作用。但是,同样很清楚,韩玄子的行动从一开始到小说结束,政治色彩都不是十分浓烈的,而个人间的争持痕迹却相当突出。我们如此判断韩玄子的思想行为,是否就缩小了这个人物的作用,减弱了他的典型性,降低了他的社会意义呢?笔者以为是不会的。一个典型形象价值和意义的高低、丰富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言行中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色彩,他的行动有多么直接的政治企图,而在于他的思想和动作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代表了哪种势力,对生活起了怎样的作用。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未庄一个落后的农民,他愚昧无知,浑浑灵逦。从他的身上,我们是很难分辨出多少鲜明的政治色彩的。然而,他确实又以他“阿Q式的革命”活动于辛亥革命前后,并在当地发生着影响。后来,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在引导和发动农民工作方面的失误,这不正是这个典型的价值意义所在吗?阿Q式的革命行动是辛亥革命对他的影响所致,反过来它又反作用于辛亥革命,这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阿Q与革命之间,他的自觉性、明确性联系实在模糊得很。阿Q只管我行我素,至于自己的活动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效果,他是绝不会去考虑的。韩玄子的情形自然不能与阿相提并论,但韩玄子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的活动情形及其作用,却并非与阿Q没有某些相近之处。如果韩玄子处在政治活动的中心,有非常强烈鲜明的政治主张和目标,那么他站在社会前进的对立面,疯狂地反对革新,这自然也会成为一种典型。可现在《腊月正月》里的韩玄子不是这样的典型。这里的韩玄子是个由于多年来主客观两方面的诸种因素造就的一个坐在小地方宝塔顶上的人物。如今,当他发现别人着手建造起比宝塔还要高的楼房,并准备住上去的时候,他自己不是主动地改建宝塔,却设法去挖别人的墙砖,从而造成别人不能居于自己之上的事实。可惜,韩玄子使用的工具过于陈旧,他无力对付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型建筑材料,结果人家的高楼毕竟是建起来了,他只好望楼兴叹。韩玄子挖别人的墙砖的目的在于防止别人居己之上,并不是绝对地一概反对盖楼房;而他的工具陈旧却是导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说韩玄子不愿屈居他人之下是出于他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话,那么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去挖他人墙脚,这却就是明显的破坏行为了。这时,他行为的对立面不光是楼墙的主人,而是整个社会的公理和正义。尽管他对后面种种恶果的认识还处在朦胧状态,可事实上恶果已经造成。韩玄子是一个从极端落后自私的思想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落后陈旧的武器抗御别人对自己的威胁,并把这种行为推向极端,造成对新事物的破坏,最后使自己成为冥顽不化、被新的历史生活无情淘汰的人物。韩玄子虽然是生活在一个山区小镇上的具体人物,但类似韩玄子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却不在少数。在其它地方,人们是并不难见到这种人的。有些人或许不像韩玄子这样开始只是为了住得比人高一些,可能是不愿意让出一个什么“长”、什么“书记”的交椅;他们只是为了做成几宗赚钱的生意,或是想给子女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等等。可是,为了实现这许多不同的目的,他们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采取韩玄子那样的行动,具有韩玄子那样的心理特征。韩玄子是这类人的化身,他凝聚着一些很有普遍性的心理特征和行动特点。韩玄子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性格内涵的人物,是一个不易多得的艺术典型。这个形象较之那些打上了分明政治色彩的改革反对派的形象性人物来,更多地带有普遍性。这样的人虽说时时处处都在对社会进步起着羁绊作用,可他又不易被人们所察觉。把这样的人通过文学作品形象化地描绘出来,它的社会意义无疑要深广一些,价值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地会得到提高吗?
任何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的创造无不同作家细密的观察认识和真实生动的艺术描绘联系在一起,同作家把对具体人物的把握与对整个社会矛盾内容的认识结合在一起。贾平凹成功地创造了韩玄子这个典型,正是他长时期对农村现实生活感受剖析的结果,是他把农村生活的过去、现在进行了一番比较认识的结果。因为有了这么丰厚的生活积累,韩玄子这个形象在他的笔下才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附着物,他的思想性格、言语行动在纵横两方面的触角都是宽而又长的;既不虚泛,也不呆滞,鲜活具体,清晰可感,在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中达到了较深的层次。
贾平凹的笔墨一向轻盈、清丽、古朴而富于泥土气息。这一次,作者在保持这所有长处的同时,又溶进了浑厚和肃穆,所以作品的分量大大加重了,形象也变得十分毕富了。有些人的小说是“做”出来的,可贾平凹的小说似乎自然天成,作者的功夫只在于如实的叙说描画。在《腊月⑩正月》中,我们极少看到人为的雕琢,一切都是生活一般演进,风土人情、悲喜的命运像画一样徐缓展开,悦人眼月,启人心灵。这次我们结识了一个韩玄子,下一次又是个什么人呢?我们期待着贾平凹的艺术回答。
(1984年10月27日)
田家祥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
评《拂晓前的葬礼》
如果是为王兆军的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写一篇一般性的推荐文章,显然已为时过晚。可是,这种情形并不妨碍我们继续研究分析这部小说,因为,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一篇信息通报式的推荐文章就能交待过去的。
多年来,在我们的小说创作中,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不仅数量大,思想性、艺术性也十分突出。谁要在这个领域中有新的开拓,有较为明显的突破,是相当不容易的。读了王兆军的这部小说,我确实感到有新的开拓和突破。最突出的一点是,作者的深邃的眼力穿透生活的底层,写了一个并非弱者的农民的悲剧,给人以颇为深刻的启示。
《拂晓前的葬礼》中的主人公田家祥自小生活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充满艰辛和不幸。在大苇塘村,田家总是受人欺侮的对象。不留心,田家的猪跑了出来。如果是别人家,会一点事也没有。可这事在他家,猪会被民兵逮住,还会被罚20斤小麦或10块钱。如果说,肉体的痛苦尚可以忍受,那么来自精神情感方面的种种轻视和欺凌就很难忍受了。物极必反,田家祥不愿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地活下去,他决心从一个很可能使人变得颓唐卑琐的环境中跳出来,立志使自己变得强大威严起来。田家祥发誓,以后他非得成为“大苇塘村顶厉害的人不可”。几番奋斗,多年风雨,田家祥的誓言变成了现实,他真的在大苇塘村树起了自己的旗帜,以自我的意志左右着这里近两千人的命运和行动。然而又到了一个物极必反的时刻。正当田家祥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时候,他却没有觉察到,群众正从他的身边悄悄地散去,他的思想行为与前进着的社会潮流出现了偏差。新的农村政策使农民的心动了起来,明媚的晨曦在向人们招手。可是,田家祥这时却紧紧地把握着自己得来不易的权柄不忍撒手,甚至用它去欺压别人,抵制时代的脚步。终于,田家祥从他生活的顶峰上失落下来,坠向灰暗的一角。
过去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过不少农民的悲剧一李顺大的悲辛,李铜钟的不幸,许茂老汉的哀怨,乃至以卖米豆腐为生的芙蓉镇居民胡玉音的坎坷遭际,都曾给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以很大的震动。这些人物的遭难或因社会的失损所致,或由不正确的政治路线生起。但是,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来说,他们都是纯洁善良、高尚美好的。他们的悲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人在看到善良遭涂炭时生起许多义愤和伤痛,对于外来的恶势力多有责难。可是,田家祥的悲剧却不同。田家祥的道路自然是同社会环境不可分离的,但是他开初的喜、后来的悲都更多带有历史的积淀和个性的色彩。假如说给李顺大、李铜钟、胡玉音以平和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悲剧就不一定会发生的话,那么同样的社会环境就不见得使田家祥摆脱悲剧。田家祥正是在春风吹拂的时候显出悲相的。因之,田家祥的悲剧根源似乎要深一些。这就是田家祥的悲剧不同一般的地方,也是作者新的艺术发现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