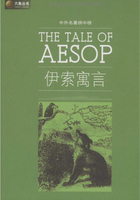论贾平凹笔下的韩玄子形象
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是及时深刻地反映农村现实生活变革的小说中十分出色的一部。这部小说最突出的成绩是它很好地创造了韩玄子这样一个典型形象。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千姿百态,洋洋纷呈,但真正可以成为艺术典型的人物仍嫌稀少。如今,在乔光朴、陈奂生、陆文婷、李铜钟、那五、魏天贵等人物形象的后面,贾平凹把韩玄子的名字列了上去,这是他对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十分突出的贡献。
韩玄子是居住、生活在商州山区一个小镇上的退休教师,可他在这里却是个大人物。他教了30多年书,“桃李满天下”,学生中有的当了县委书记、地委部长。长子又是全镇第一个大学生,现今在省城当记者。为了小儿子能早点吃上公家的粮,他找了个门子,提前办了退休手续,让儿子接了班。退休了,本当隐居家中,静养天年,可韩玄子不甘寂寞,他受任公社文化站站长职务,还“参与公社一些事”。韩玄子“有文墨”,又经多见广,结交不凡,所以这里的人甚至把他当作当今的“圣人”。镇上如有人家庭不和,就请他去评判调解;谁家要办个红白大事或别的活动,也忘不了请他参加。在这地方,韩玄子自视不凡,对内对外显山露水,忙得很,影响也大得很。可是,自农村的生产方式由过去的集体化改为个体责任承包以后,形势开始剧烈地变化。起初,韩玄子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倒也是支持的;但他慢慢发现,随着这种新政策的逐步推行,自己在镇上的地位和影响正在削小和减弱,他就再也沉不住气,忍耐不住地站起来为维护已有的地位和影响进行斗争了。过去,王才在镇上是个十分卑微的人物,在韩玄子的眼里“王才是什么东西”“什么角色”“他能办成什么”?可就是这个不断遭到韩玄子睥睨的王才,在新政策的感召下,先做买卖,生意不成,继又办起食品加工厂,经济收益渐渐增大,在小镇上越来越显出了兴盛的气候。多少年来,王才一直是把韩玄子当成先辈、智者相待的,即是自己现在有了一点转机,他对韩玄子也从未有过稍微的非礼之处。然而,韩玄子却固执地认定,王才如今的行动是有意和他为难、与他作对,是对自己的挑战。为了抑制王才,韩玄子几乎丧失了理智,毫不顾惜自己多年来形成的那种自以为风雅的习惯作派,费尽了心机,使尽了手段,可斗争的结果却大出他之所料一王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道义上都占了上风,而他却四面楚歌,只好一个人坐到四皓墓旁的坟丘顶上做痛苦的呻吟和“到死不服”的哀叹。从腊月到正月,时光多么短促。然而,在如梭的世事变革中,韩玄子从宝塔顶上跌下来。原本满腹才学、气宇不凡的韩玄子如今却落下这样一副惨相,将要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长久地留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悲剧。作者对韩玄子似乎并不薄情,在小说的一些地方对他的命运遭际甚或无意流露出些微的伤感。可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思想的引导下,作者却无法回避严峻的生活现实,终于如实地、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韩玄子难以挽回的败迹。《腊月正月》犹如一曲哀惋的挽歌,在这凄恻的哀惋声中,一个不屈的灵魂无可奈何地离去了。它留给人们的印象也许不无英雄气概,但这终究是失败的记录。韩玄子的形象正是在这个失败者的记录中显示出他的不同凡俗处,变得很有价值了。
韩玄子是个“聪明”人,可是面对既成的事实,他依然死不服输,还要同王才“走着瞧”。这使我们知道,韩玄子对于自己失败的根源一直是没有认识清楚的。韩玄子总是把自己与王才之间发生的这些冲突看成是他们个人间的事情。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他再三权衡自己与王才在各方面的实力,感到王才哪里是他的对手,怎么可能会超越他,进而取他而代之呢?其实,韩玄子哪里知道,自己的悲剧正是从这种错误的认识开始的。知书识理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会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知书识理又会使一些人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从而干出一些愚蠢的事情。世上许多悲剧发生在极聪明的人身上,正是这样形成的。韩玄子的遭际又是一例。韩玄子总以为自己有学问,鉴古通今,在镇上为人处事无人能及,还不无自负地说什么世事我看不透?”“我不是共产党,可共产党的事我经得多了,是不会让他(指王才)成了大气候的。”另外,在客观方面,别人多年来对他的敬服也加重了他那自负清高的性格,滋长了他固守己见、惟我独尊的习性。正因为以上原因,韩玄子就把自己的尊严和在当地的影响作用看得非常重要,不容许它产生一点点动摇。王才求他躲他还求不到躲不及,但他却敏感地以为王才的所有动作都是对着他来的,是有意识地侵犯自己的领地。这种近似神经质式的敏感和强烈的维护力,正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思想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造成的。到后来,他竟是那样地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以破家为赌注,采取威胁、恐吓、走关系、打黑枪等恶劣手段扼制王才,这更是他封建传统观念和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韩玄子是从维护个人精神利益出发而与王才进行较量的。
然而,事实上韩玄子与王才之间无形中发生的这些矛盾冲突决不纯粹是他们二人间的纠葛,而是一种历史转折关头新旧两种社会思想观念、两种生产力、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斗争的反映。王才确实是个小人物,但他的思想行为顺应了谋求革新、进步的社会潮流,所以他才渐渐地由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变得显眼突出起来。但韩玄子只看到王才的兴起,却没有看到或没有去细究伴随着王才、又是从根本上改变着王才面貌的这种社会潮流。或者即使看到一点,也不愿意承认它的正确性和永久的生命力。这样一来,他表面上是同王才争高低,实际上却把自己置于社会进步潮头的对立面。这种对立的情绪越是强烈,他的失败就越是凄惨。在我看来,-韩玄子这个形象不应该被认作是那种自觉自愿地抵制社会进步的顽固派的典型。假若这样认识,那就会把这个十分复杂的性格形象简单化了。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不少作品中,已出现过一些反改革、千方百计阻拦改革顺利进行的人物形象。可惜,在有些作品中,由于作家未能深入准确地认识并描绘出人物之所以反改革、阻挠改革的思想基础和性格逻辑来,因之形象不免显得苍白,流于脸谱化,给人留下的印象自然就不很深刻了。韩玄子不是这样的,作家是很充分地认识并把握着他的思想经历、性格特点,并写出了他最后走到社会进步潮流对立面的特异性和内在逻辑性的。所以,韩玄子这个人物形象具有比较高的典型性。从他的身上,我们见出现实生活中某些人对前进着的生活总抱有偏见和抗拒情绪的心理状态,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清楚贾平凹创造这个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在小说中,王才似乎大都处在一种惶恐之中,甚至有点可怜巴巴的样子。他多年来家贫气短,被别人瞧不起,再加上生性软弱,所以在韩玄子面前就显得分外怯懦、拘谨了。而韩玄子呢?他完全是一种气势逼人的架势,似乎指挥若定,稳操胜券。他说公家的房子要卖,不能说谁能拿出现钱就可以让谁去买,要用抓阄来定,结果就真的按韩玄子的意见办了。秃子和狗剩刚到王才的食品加工厂干了几天活,就挣了十几块钱,得意极了,跑到镇街上巩德胜的酒店显摆,结果在酒桌上与气管炎话不投机,引出一场打闹。为了整治秃子和狗剩,进而打击王才,韩玄子到公社找张武干(武装干事的称呼说说,结果张武干就不分是非,把秃子和狗剩整治一顿,让其如数赔上巩德胜十几元钱。这不是作家故作欲抑先扬之笔,而是真实生活现象的艺术再现。韩玄子以他那样的地位影响,在这小小的山区小镇上自会来去自如,呼风唤雨。可是,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韩玄子可以不让狮子队到王才家的门前“喝彩”,但他却无法阻遏王才食品加工厂的扩大和发展;他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让各队出社火队,并拒收王才自愿捐助的钱,但他却又不能不为筹备闹社火的经费花心思。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要依靠权威和人缘生活,而且更重要的还要依赖不断发展生产、提高物质和精神产品过日子。韩玄子威信高,可他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切身的利益;他人缘好,可在他面前,别人好像总低他一头。而王才能给别人看得见的好处,让人家生活得心情舒畅。所以,不管韩玄子本身有多么大的本领,他的这种本领到底还是在旧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它同今天的社会生活实际、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需求、同历史的发展已很不适应了。他的倒运正在于他的背时。不是韩玄子较早些年变得无能了,是历史决定他必然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从某一方面看,韩玄子也是受害者,是因袭的传统观念和沉重的历史包楸损伤了他那颗始终好强的心。小说后面在矛盾一时不见明确走向的时候,写韩玄子想在丰盛的家宴上大请乡邻,招待上级领导,以达到冷落王才、唤起人们对自己的崇敬的目的。却没料到县委书记突然专程给王才拜年,不上自己家门,结果人心突变。韩玄子兵溃如山倒,王才信誉骤起。这些情节和描写虽说不无戏剧化的痕迹,然而它在显示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社会前进的脚步不可阻挡这一点上,仍然是有力量的。韩玄子的性格也正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口变得突出强烈起来,更富有启人深思的作用。
韩玄子这个形象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他使我们具体地看到,当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地位和威严受到削弱,即将成为过去的时候,他会如何毫无畏怯地进行殊死的搏斗,甚至不惜与社会进步潮流为敌。韩玄子是个虚荣心极强的人,他为自己的经历和才智而自豪,为丰厚的家境、体面的儿辈而骄傲,为自己能结交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而喜悦。在涉及到自我尊严和地位这方面,韩玄子非常敏感。小儿二贝夫妇看不惯他那些陈旧的作派和习性,不大听他的使唤。他十分不满,以至与其分家单过。为此,他竟当着二贝夫妇的面“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说“我太丢人”,“我活这么大,还没有人敢翻了我的手梢”。自家的照壁掉墙皮,想修补,当时又没白灰,老伴说王才家有,不妨先用上。这一下子又触动了韩玄子那根敏感的神经,他大发雷霆,说是“丢人了,宁肯这照壁塌了,倒了,也不去求乞他王才”。韩玄子从他特殊的心理意识出发,时时把自己看作是“在人面前走动”的人,凡事都要不同俗众,高人一手。也许因为他总是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所以他也最怕丢脸面,被人瞧不起。本来是居家过日子中一些正常的交往,到了他那杆天平上就失去了平衡,引出一番是非来。说实在的,韩玄子并不是没有感到新农村政策的威力,看到社会生活中那种不可拦截的力量,但他划分正误的标准不是这政策、这力量对广大的社会人生是否有益,而是看它给自己到底带来了什么。当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正在因新政策的实行而渐渐变得微小起来时,他就牢骚满腹,忧心忡忡,直至为了自己的虚荣心理什么也不顾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