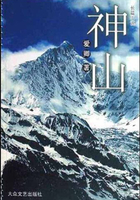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郝老板。”项点脚低估了郝眯缝眼的能力,根本就没想他会沾日本人的边儿,他认为日本人绝对瞧不起郝眯缝眼的。其实不然,日本人,具体说是林田数马看上了郝眯缝眼,恰恰是他其貌不扬,外陋者多内险,这是林田数马的经验。
林田数马还精通中国的神相术,郝眯缝眼生着一双阴阳眼:“两目雌雄眼大小,精神光彩视人斜,心非口是无诚意,富积奸谋诡不奢。”他看中的正是这种心术不正的人。
项点脚不失精明,但不懂人长什么龟眼象眼牛眼的,眼下他急需一名兽医,郝眯缝眼曾是亮子里有名的兽医,所以就请他来医马。
“昨晚的太平鼓咋样?”郝眯缝眼问。
“不错。”项点脚赞赏。
“来日何不请到绺子上演几场。”
郝眯缝眼探听虚实,项点脚没听出来。
“唉,倒霉的事一宗接一宗,哪还有心思娱乐。”项点脚怆然地说。
“怎么?”郝眯缝眼装出惊讶。
“咦,不顺,不顺啊!”项点脚叹气。
“你们绺子历来是局红管亮啊!”郝眯缝眼转弯抹角地探询。他有他的目的,嘱托每月要从守备队那儿领两块大洋的,花膀子队的动态就是情报。
“八月节,给狼群包围了……”项点脚和盘托出那顿狼肉大宴惹出的祸端。
一马树匪巢,郝眯缝眼见到一派败落的景象,昔日威震荒原的花膀子队,现在只剩下十几人,残兵、败将、病马。
马误食了一种致其昏迷的醉马草,郝眯缝眼不愧为医马高手,他没走出几步,在草甸子弄到一种相克、攻毒的草药给马服下,马很快就站起来了。
郝眯缝眼返回亮子里,连家门都没进,直接来到守备队部。半路在街上买了只老母鸡和两棵草参,来见林田数马。
“幺细!”
林田数马此时最想知道的就是花膀子队的情况,郝眯缝眼的情报是及时雨。
“他们打算去香洼山打白狼……”郝眯缝眼说。
林田数马听着,大脑过滤着情报,挑拣有价值的东西。
郝眯缝眼把所见到的,所听到的,通通报告给日本人,尽一个嘱托之责。
“卢辛没被狼吃掉?”林田数马关注匪酋的生死。
“他最近从哈尔滨回来,带回一个俄罗斯女人。”郝眯缝眼说。
“卢辛没死,那个项点脚呢?”
“活泼乱跳的。”
花膀子队剩下他们俩,实力就不可轻视。怎么说花膀子队也到了穷途末路时期,狗落水了,正是追打的好时机。
林田数马表扬了嘱托一番,多赏了两块大洋打发走郝眯缝眼,决定马上部署清剿卢辛的花膀子队再好不过。
“借刀杀人。”林田数马反复琢磨这句中国成语。他不出面去做这件事,并非因为不便,而是他算了一笔经济账,成本上不合算。借谁的刀呢?
“韩把头!”
林田数马选定了目标,卢辛与狩猎队有宿仇,新近劫获白狼皮,杀死了韩把头的磕头(结拜)弟兄刘五,结了新仇,挑唆和指使他们去打花膀子队。
林田数马和韩把头见过一面,小松原领他为大青骡子的事找过自己,接受了韩把头送的五张白狼皮后,放了擅自闯入满铁禁地的大青骡子。他看出韩把头对放过他的坐骑很满意自己,更看出小松原和狩猎把头的友谊。
“带小松原去见韩把头。”林田数马打算亲自出马。
去玻璃山的路上,小松原猜测队长去见韩把头的目的。越想他心里越发毛。
“那只狼眼睛……”胆虚的小松原频率很高地想他和韩把头干的那件事,真的怕带自己来玻璃山找韩把头对质。当然,韩把头死也不会出卖自己,这一点他心里有底。
两匹马在玻璃山间毛毛道上前行,蹄子叩磕石板的声音,令小松原惴惴不安。
“怎么啦?”林田数马问他的士兵。
“我……我怕狼。”小松原编出谎言。
玻璃山有狼出没,灰白的狼屎随处可见。
“大白天的,怕什么狼。”林田数马责备道。
小松原宁可承受责备,甚至是责骂。队长认为自己怕狼好,起码没发现他心里的秘密。
“我们这次去找韩把头……”林田数马在半山腰上,才对他的士兵说出此来的真实目的。
小松原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你要帮我说服韩把头消灭花膀子队。”林田数马抬了下右眼,说。
小松原发觉队长置换的右眼,老是往下看,他不得不随时调整视角。缺乏狼的知识,就难解释这种现象。
到了狩猎队的驻地,韩把头并不在他的把头堂屋里。
“找你们的韩把头。”小松原说。
“哦,我们把头在后山驯鹰。”老姚说。
“叫他回来。”小松原说。
老姚迟疑不决。
“就说小松原找他。”小松原说。
老姚听过这个名字,去后山驯鹰前,韩把头有过交代,要是有个叫小松原的日本人来找他,就带他到后山驯鹰房来。
“走吧,我带你们见他去。”
驯鹰房搭建后山的一悬崖绝壁上,远远望去倒像一只巨大的鸟巢。为何把驯鹰房搭建在这种险峻的地方与海东青的刚烈性格有关。
韩把头驯鹰技术是跟爹学的,尽管爹后来不想让他成为猎人,还是把驯鹰的技术传授给了他。
一只海东青在爹的桦皮小木屋里,十一天没闭眼。
“还得几天啊,爹?”韩把头问。
“它不被驯服就一直驯下去。”爹说,“儿子你白天,我晚上熬它。”
爷俩儿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守在海东青身边,用根棍子敲打拴在鹰腿上的铜铃铛,不让它睡觉。
“盯住它的眸子,只要它一闭眼,就捅铃惊醒它。”爹交代。
韩把头按爹的吩咐,一丝不苟地去做,盯着鹰那透明的眸子,只要它一闭就吓它睁开。
三顿饭吃在鹰身边,他发现鹰的眼里满是乞求,在街头他没少见到这样的目光。
“你饿了吗?”韩把头动了恻隐之心,将一块馒头送到鹰的嘴边,正巧被爹看见。
“干什么?”
“它饿啦。”
“饿也不能给它吃。”爹说。
“十一天不给吃的……”韩把头嘟囔,心里说,“残酷!”
熬鹰必须这样残忍。
熬鹰,故顾名思义,就是熬尽它的精力,让鹰向人屈服。
“等熬得鹰黑了眼圈,瞳孔里没了神采,它的野性就快耗没了。”爹教诲儿子。
再往下的岁月里,韩把头也是这样教授他的徒弟的。
“只耗尽它的野性还不成,同时要给它强制减肥。”爹说。
给海东青减肥,驯鹰者有一套独特方法:将猪精肉剁碎,拌在苋麻皮中,做成橄榄果形状,鹰误当肉丸吞下去。苋麻皮吃下去消化不了,最终还要吐出来,带出肠子油,鹰就消瘦下去……
韩把头对爹的驯鹰方法改进了许多,驯鹰房建在悬崖绝壁上,就是他的发明。
“鹰击长空俯瞰人间,不能熬尽它这一天性,那样对打猎不利。”韩把头说。
“老把头!”老姚在山下喊。
“什么事?”吴双出现在驯鹰房窄下的窗口,山太高的缘故,他的脸很小,缩小了几号,“把头在睡觉。”
“有人找他。”老姚指指身边的小松原。
吴双看清是小松原,便缩回头。
韩把头直接走下山来。
“老把头。”小松原上前打招呼。
“太君找我?”韩把头睡眼惺忪,问。
“我们队长找你。”小松原说。
一马树的傍晚有了索菲娅,便有了生机。她的笑声如泉如溪,踏着草尖传向远方,是那样无忧无虑。
秋天晒干狼屎泥颜色的土坨上,卢辛和项点脚坐得很近,瞻望遥远的地平线,耳朵灌满索菲娅的笑声。
“女人真是水做的。”卢辛慨叹。
“但愿不是祸水。”
卢辛直愣愣地望着项点脚。
“莫非二弟看到什么,她……”
项点脚摇摇头。
“你是不是认为我把她带回绺子,破坏了规矩?”卢辛不能不在乎水香的话,尤其是在花膀子队背累(背时),他的话更不能不重视。
项点脚拔出嘴里的一段干草,橙色的涎液流出嘴角。
“女人是雪不是水就好了。”项点脚说出句没头没脑的话。
卢辛更加迷惘。
一只被惊起的沙鸡几乎是贴着头顶,突突飞过,他们感觉到了翅膀带起的风。
“啊呀!”卢辛惊呼。
一摊稀白的东西落在卢辛荒丘一样的头顶上,是沙鸡屎。
“母亲的!”卢辛狠骂一句,他总用这样的词汇骂人。
鸡屎突然间落到头上,胡匪视为不吉利。
“一马树不能待了。”项点脚说。
“哦?为什么?”卢辛惑然。
“我有预感……”项点脚说,“郝眯缝眼的眼睛滴溜溜转,我心没底呀!”
“一个吓破胆的扒子,小泥鳅还能翻起大浪?”卢辛问,“我们不去香洼山打白狼?”
“我看还是不去的好。”
“好不容易碰上白狼群,不打可惜喽。”卢辛说。
“眼下保住队伍要紧啊……”项点脚说服了卢辛,“走,立马走。”
“那我们去哪儿?”
“离开爱音格尔荒原,钻大青山。”项点脚说出自己的想法。
一时半晌,一言半语很难说服卢辛离开的。爱音格尔荒原对卢辛,对花膀子队是避风港,一个土丘,一条河流,一片草地,一个村镇都了如指掌,环境的熟悉就意味着安全。
说心里话,项点脚也不愿意离开此地。
“可是我们只这匹马几杆枪,又面临着几家仇人追杀,好汉不吃眼前亏。到大青山养精蓄锐,壮大队伍,等东山再起……”
卢辛和项点脚谈到很晚,狼屎泥颜色的土坨上完全被黑暗覆盖,他们才走下坨子,分别回到宿处。
此时,花膀子队的人和狼夜宿极其相似,分散到各处。
卢辛和索菲娅的宿处,有了女人显得活力和浪漫。一墩红柳丛,经女人的手装饰,变成了美丽的建筑,树枝上系满野花。
他们甜蜜在柳丛里,仰望秋天的花朵。
“今晚你怎么冷冰冰的?”索菲娅感觉异样。
“没呀?”卢辛否认。
“你没叫我马。”
卢辛习惯叫索菲娅马,尤其是那种时候,他更喜欢叫。骑马驰骋的感觉在他看来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今晚,卢辛从跃上去,到跳下来,他都没骑马的感觉,没吭一声,默默做完事。
“亲爱的,你没叫我马。”索菲娅抱怨说。
“我们要离开爱音格尔荒原。”卢辛告诉她。
“这里不是好好的嘛,为什么要离开?”索菲娅觉得他的决定太突然。
“这里我们不能待啦,得走。”
索菲娅情绪立刻低落下去。她不愿意离开一马树的原因,是一个秘密,一个连卢辛都没告诉的秘密。
索菲娅想给卢辛生个孩子,她正在拜仙求子。
在叶老憨家她从养母那儿学会求子的方法,供奉送子娘娘“晚上一炷香,清晨三叩首”。
“我求子呢。”索菲娅道出实情。
“求子?”卢辛眼光没离开她的腹部,身子更靠近她一些,说:“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哪里有庙啊?”
“我自设的神坛。”索菲娅抓起他的手,“走。”
他们来到一个土丘上,卢辛看到一盏燃着的灯,灯光昏暗,几样面食供品和已燃尽的香灰。
“跪下,”索菲娅先跪下,叫卢辛:“给娘娘磕头。”
很少受别人支配的卢辛,此时意志完全受她支配,乖乖地跪在索菲娅的身边,双手合一作揖,随着她念叨祈祷语。
然后,他们离开。
“需要二七一十四天,我已经求了九天,还有五天。”索菲娅半路上说,样子十分虔诚。
“你怎么不供佛像,而供一盏灯?”卢辛问。
“这不是一盏普通的灯,是一盏神灯。”
“神灯?”卢辛无法理解那只破旧的马灯,是什么神灯,供奉它,给它磕头烧香做什么?它真的能送子吗?
叶家有一盏神灯,是索菲娅的养母从庙里“窃取”的,9岁的索菲娅参与了窃取。娘和她到观音庙烧香,趁身边没人,娘用事先准备好的包袱皮,裹住佛桌上供奉的莲灯,急匆匆地逃回家。
“娘,偷灯干啥?”9岁的索菲娅问。
“不是偷,是请。”娘纠正女儿的说法。
索菲娅不明白娘偷--请一盏庙里的灯做什么?正像卢辛一样不解。慢慢长大,她才明白娘整日供奉它,是祈求观音送她子女。在民间,“灯”和“丁”谐音,偷来观音的神灯,就会添丁。
同卢辛来一马树,她忽生要一个孩子的念头。自从被养父叶老憨霸占,几年里,有几个男人来耕作,都没有收成。她想起养母,祈求观音让她的肚子里有动静。
“哪里去弄‘神灯’?”索菲娅遇到难题。
附近没有人烟,也没一座庙宇。养母说过:信神有神,信鬼有鬼,不信是土坷垃。她向项点脚要一盏旧马灯,把它当神灯供奉起来。
“我和水香的定好了,后天挪窑(转移)。”卢辛说。
“那你们走,我不走。”索菲娅说。
“不行,一起走。”卢辛口气有些生硬。
“求子还有六天……”
“风紧拉花,一天也不能拖延。”
“风紧拉花?”
卢辛见她不懂这句土匪黑话,解释道:“就是事急速逃。”
索菲娅迷惑不解,什么事那样急需迅速逃走呀?
“你别问了,做好准备,后天离开一马树。”卢辛的口气不容违拗。
“后天什么时候走?”她问。
“干什么?”
“我再给神灯烧最后一炷香。”索菲娅说。
“鸡叫头遍,挑(走)。”卢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