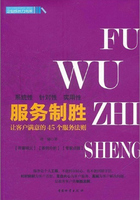独眼老狼终于见到了香洼山。
晨曦中,香洼山间缠绕着雾气,斑斑点点倒像一片片绿色的叶子在水上漂浮。
几天里,独眼老狼突然苍老了许多,身体失去水分一样枯萎下去,极度的疲惫、饥饿,它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实在没力量将大角马鹿拖上香洼山,它又没放弃拖大角马鹿上香洼山的打算。事实上,他实在无力将大角马鹿拖上香洼山去,寻找伙伴帮忙是唯一的办法。
嗷呜--嗷!
独眼老狼几乎用尽最后的气力,嗥叫缺乏往日的雄风,飘过秋天原野的声音嘶哑而悲凉。
嗷呜--嗷!
并没有一只狼出现。
狼王啸聚山林、呼风唤雨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独眼老狼似乎不承认,也不愿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族群中没谁在拿它当一回事啦。自然就没一只狼跑下山来帮它,欢迎它。
独眼老狼哀凄地怀念前呼后应的年代。
韩把头正跟踪着狼的蹄印,痕迹表明是只狼,它正拖拽着较大的猎物。他判断捕杀了大型动物,定要拖到洞里去,或在洞的附近埋藏起来。狼是储藏食物的高手,它会把一时吃不完的食物藏起来,饿时再弄出来吃。
独眼老狼的行为,把自己孤身一人的情况泄露给经验丰富的狩猎队的把头。寻找一只狼,而不是一群狼是韩把头最理想的。为给小松原弄狼眼珠,必须擒住狼,在爱音格尔荒原,找到狼不难。香洼山就有一群狼,一群白狼。
现在正是狼喂养幼崽儿的季节,亏情是不能打的,打了就犯了狩猎帮的严密的规矩。
打亏情--把本不该打的动物打了。春不打母,秋不打公。韩把头决定冬天打香洼山上的狼,眼下连一根狼毛都不能动。
小松原要的狼眼珠怎么办,寻找到一只鳏寡孤独的狼,它既不会在香洼山上的族群里,又没儿没女。
韩把头想到昨夜从猎鹰场地回来遇到的蹄印,决定沿着它寻找狼。痕迹是一只狼拽一头猎物,看得出它很吃力,走走停停,几个深陷的蹄窝里掉下了毛,可见是一只老狼。
他加快了追踪速度,陈旧的蹄印说明离狼还很远,必须在狼到达洞穴前捕获它,不然进入洞穴里就难捉住它了。
香洼山脚下有一条河,属裤裆河的支流。独眼老狼在河边喘息着。此刻,它连喝水的力气都没了,眼巴巴望着清亮的河水喝不到嘴。
“它在身边就好啦。”独眼老狼强烈地想一只狼--年轻的狼王后杏仁眼。八年为王的岁月里,先后几位王后,末代的王后是杏仁眼,它们在一起如胶似漆,只是时间太短暂。
公狼们站在一起没辈分,独眼老狼和杏仁眼卿卿我我时,蹓蹄公狼看上了杏仁眼。它向曾经含辛茹苦打食哺养自己长大的父亲挑战,它要做狼王,要娶杏仁眼为妻。
老夫少妻的日子甜蜜而短暂,在这短暂而甜蜜的日子里,独眼老狼享受到了被少妇之爱的幸福。
有一次,独眼老狼一觉醒来,眼前发黑,站不起来,口渴得厉害,嗓子呼呼拉起风匣。
杏仁眼跑出洞去,来到小河边,用带食物的方法喝下水,再急急忙忙跑回来,嘴对嘴地喂给独眼老狼。
那是世界上最甘甜的水,独眼老狼终身铭记。
现在,物是人非,杏仁眼已经听不到它的呼唤,听到了又能怎么样?杏仁眼在新狼王的怀里,即便它不忘旧情,蹓蹄公狼也不会容忍妻子去怜悯一个失败者。
狼族的残酷独眼老狼无法改变,它想自己只要能喝到水,干枯的躯体得到滋润,就有力量把大角马鹿拖上山。
韩把头穿越一片草地,知道离狼很近啦。他停下来,做捕狼的准备,双筒猎枪装上子弹,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多了几件不属于狩猎应必备的东西:一只液氮铁罐和准备摘掉狼眼球用的医疗器械。
猎人到了走狼步的时候,就离猎物很近了。
韩把头分开眼前的蒿子叶,望见河边有一只枕着死去大角马鹿的老狼,一只白色的大狼。
观察,韩把头仔细地观察目标,确定是一只狼,一只风烛残年的老狼,它的身边没有第二只狼,正好逮它。
韩把头瞄准狼的额头,端着枪靠上去,已靠得很近,老狼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奇怪,能捕杀到马鹿的狼反应竟然如此迟钝。再近一步,与目标已不足两丈远的距离,韩把头准备开枪。
这时,独眼老狼微微抬下头,望一眼韩把头,挣扎几下,马上耷拉下头去,躺着不动。
“一只垂死的狼!”韩把头手指稍稍离开扳机,一个堂堂的猎人并不是赖狗,他要打的是雄壮的动物,不愿向老弱病残的动物开枪。打住快要病死的动物,是一种耻辱。
一步步地向前接近,离狼只剩下三步。生死的界限,如果那只狼陡然而起扑向韩把头,他仍然有丧命的危险。
韩把头端着枪,没敢懈怠,保持警惕,走得离狼剩下一步远时,他完全放下心,独眼老狼已奄奄一息,睁开眼睛的力量都没有了,眯成一条缝,身体抽搐着。
爹咽气前就像这幅景象,依恋不舍。
独眼不肯撒手狼寰!
韩把头放下枪,蹲下身,向对待一个同类,听它最后的遗言。
一个生命即将结束,就如一盏灯就要熄灭。此时,人和动物,生命穿越了天敌的界线,冰与火融为一体……独眼老狼睁开眼睛,眸子纯净得如一颗露珠,没有一丝的敌意和恐惧,泪水涨潮一样漫上来,嘴唇颤抖着发不出声音,它要说什么呢?
几只乌鸦飞过来,落在枯树枝桠上嘎哇地叫。它们大概闻到死亡的气息,等待饱餐一顿。
韩把头盯向老狼的眼睛,这是一只极其美丽的独眼,正是他寻找的眼睛啊!
一袋烟的工夫,老狼仅存的一只独眼的眼球在液氮罐子里了。
嘎哇!嘎哇!嘎!
乌鸦越聚越多,那棵树已变成黑色。
韩把头面对一具白色大狼尸体寻思,他只要一离开,数以百计的乌鸦就会分食它,把它叨成碎片。
“这样一只狼,死去应体面!”
韩把头掏出腰刀肢解狼,为它举行天葬。
一块狼大腿肉抛出,乌鸦蜂拥而上,顷刻之间吃光。
剖开狼腹,膛内空空如也,剩下鸡蛋大小的胃,里边只有一撮尚未消化的干草。
“守着肥大的马鹿,老狼为何饿到这步田地?”韩把头大惑。
“你看,那就是野狼沟。”
索菲娅在马背上直起身来,顺着卢辛马鞭所指的方向瞻望,苍茫一片,她什么也没看到。
“是吗?”
卢辛掏出手枪。
“你做什么?”她疑惑。
“告诉弟兄们我回来啦,让他们来迎接压寨夫人。”卢辛朝天鸣枪。
砰!砰!砰!三声枪响,划破荒原傍晚的静寂,附近一对野鸭被惊起,带着哨响从他们的头顶掠过。
周遭静悄悄的,没见一个人影出现。
“嗯?”卢辛觉得不对劲儿,又朝天空放了两枪,还是没任何回应。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路,前边不是野狼沟。”索菲娅说。
卢辛猛加马几鞭子。
真实的野狼沟就在面前,一片凄惨景象--
草丛中散落着块块人骨,无数具骷髅裸在光天化日之下……十几名弟兄葬身狼腹的悲怆事件发生在卢辛在哈尔滨期间。
“快过八月节啦,是不是尽早准备一下。”炮头大块头对项点脚嚷道。
花膀子队在关东为匪多年,已入乡随俗,也过中国的传统节日。
“大当家的不在家,我们简单地过过。”项点脚说。
“不行,我们要喝酒,要跳舞。”大块头狂躁地喊叫。
大块头是炮头,前打后别,花膀子离不开他,在队里很有威信。遇事大当家的卢辛都让他三分,项点脚轻易不会得罪他。
“好吧,叫搬舵先生去操办。”项点脚让步,卢辛不在绺子别出什么乱子。他叫来搬舵先生苏尔东,吩咐:“你去亮子里镇,购买些吃的,躲开点日本人……酒菜要丰厚些,今年弟兄们都很辛苦。”
“哎。”苏尔东照吩咐去办了。
一天后,苏尔东把八月节的安排详细向项点脚说明:“按六六大席准备的,老粗(牛)横川子(三头),爬山子足(羊10只),尖嘴子(鸡)……”
“黑心皮子(狼)呢?”大块头问。
“我查看一遍,狼油火把还有四十多个,加上松明的,猪油的,点通宵足够。”苏尔东说。
“不是用它上亮子(点灯),让弟兄们吃顿狼肉。”大块头说得咬牙切齿。“我要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八月节,吃狼肉的事我看就免了吧。”项点脚说。
“你别管了,我带人去打。”大块头一意孤行。
“至少弄回满把子(五条)!”大块头恶狠狠地说出狼的数目。
并非花膀子队有过节必吃狼肉的规矩,鸡鸭鱼猪狗牛羊,甚至山珍海味也能弄得到,大块头干嘛偏要吃狼肉呢?事出有因。
那次,大块头带三个人去边远小镇抢劫归来。行至荒原时月已升上中天,荒原一片灰蒙,一座座牧人盘在甸子上的草垛,高高地山一般地矗立,突然,行在前面的大块头,他的坐骑长嘶一声立刻顿足不动,只见无数绿色亮点在四周闪烁。
“黑心皮子!”大块头掏出枪告诉随来的人,他十分冷静,面对的狼不是一只两只,而是一群。
尽管他们四人都有武器,但子弹却极有限,弹尽后难逃狼口,唯一的生路就是尽快到前面大草垛,爬到上面躲避,或许可免于殉葬狼口。他果断命令:“节省子弹,连子(马)靠近,杀出条血路,冲上草垛。”
狼大概看出胡子的打算,以其不顾生死的气概堵截。
大块头弹不虚发,狼哀嚎一排倒地,距离草垛还有段路程,狼再次更疯狂地猛扑过来。
这是一次生死搏斗。
花膀子队两匹马被狼咬倒,大块头即令没失去坐骑的人救起落马的人,他把腰间那颗自制的土雷狠命甩出去,巨响惊天动地,狼被突如其来的爆炸震慑住,四处惊散、逃遁,趁此空隙他们爬上大草垛。
坐骑不肯离去,大块头挥鞭抽下,驱赶马离开草垛,那两匹马昂首咴咴嘶叫几声后,逃走。
嗷嗷两声狼嗥,狼群重新聚集,将大草垛围住。开始再度朝上爬,未成功。
一只老狼带头叼草垛的草,数狼效仿,哧哧草垛震颤,逐渐降低。用不了多少时间,草垛低了,狼便可冲上来。
“咋办,炮头爷?”一个年纪小的人沉不住气啦,问大块头。
是呵,狼一口口叼草,草垛眼瞅着下落……喊吧,此处前不着村后不巴店,谁能听得见。朝天鸣枪,深更半夜谁会来救?
大块头一时也没了主意,他将所剩几颗子弹全推上膛,准备与狼决一死战,当然生还的希望相当渺茫。
生死攸关的时刻,一声冲霄的马嘶长啸,一匹马如黑旋风般地疾奔而来,月色中可见它长鬃直立,大口张开,冲入狼群连踢带咬,杀出一条血路到草垛下,它向大块头咴咴地叫,并将身子靠近草垛,等待主人骑上它。
“炮头爷,你快走吧!”三人异口同声催促大块头,并把自己的枪递给炮头,“带上吧,冲出去。”
“好兄弟们,我尽快带人来救你们!”大块头眼圈红了,他知道三个弟兄已经没救,在他手持双枪冲出狼群时,后面传来悲怆的喊声:“炮头爷,我们来世再见吧!”
返回老巢,卢辛率队伍赶来,狼群已散尽,除见了几块带血渍的破衣烂衫外,连块骨头都未找到……
天上一轮清月。
花膀子队老巢野狼沟燃起篝火,数支火把点燃,照亮张张酒醉的脸庞。最后,还差一道大菜尚未做好--烤狼肉。
五只肥狼架在篝火上,有人精心翻烤着,幽幽肉香飘溢而出,连守在外围站岗的人都闻到了诱人的香味,忍不住直咽口水。
大块头面前一溜放着五个鲜红的狼心。他先用刀子削一片,入口前叨念一遍被狼吃掉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后吞下那片狼心。
烤好的狼肉抬上桌,花膀子队分吃狼肉……
然而,一场悲剧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狼从各个角落涌过来,烂醉如泥的人刀枪抵抗,整整一夜枪声、狼嗥、哭喊声不断,到了黎明,这里一片死寂。
项点脚为掩护幸存的人,自己最后一个人离开的。他回望一眼野狼沟,见到一条浑身是血的狼叼着一把匣子枪,踉踉跄跄跑向荒原深处……
卢辛不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猜测到发生了什么。让一具具白骨复原,顺着时光隧道走回去,他们就是跟随自己横刀立马、冲锋陷阵的土匪兄弟。
一行泪水流下,索菲娅给他擦拭。
“他们一定还有活着的。”卢辛坚信。
索菲娅攥着他的一只手,感觉那只手在不停地颤抖。
“我们找他们去!”卢辛说。
一辆火车头沿着满铁线向奉天开去。
小松原坐上这个专门载他的火车,内燃机驾驶内空间并不大,小烧(填煤工)不停朝锅炉里加煤。他坐在副司机的位置上,怀里抱着液氮铁罐,一只狼眼珠在里边。
假若独眼老狼在天有灵,它会怎么想呢?自己曾经统率百多只狼,沿着铁路线走过,也遇到过开来的火车,它猜想过这个大铁家伙是不是也有内脏,在食肉动物眼里,鲜嫩的内脏可是好吃的东西啊!
独眼老狼还没机会爬上去,看火车有没有内脏。此刻,它身体的一部分,正替它完成梦想,登上了火车。它一定很失望,铁家伙根本没有内脏,倒有红堂堂的胸膛,火又是狼族的最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