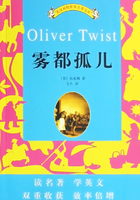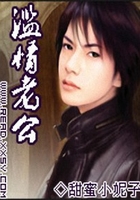迷迷糊糊的王村长猛然睁大眼睛,也挎挎匣子枪,可爹却让他读书……爷爷咽气那天,他被拉出来,蜡烛被击灭。
“现在你叫土龙戏……咱俩去魔鬼沼。”一点红说。
魔鬼沼?王少爷一听便往一点红的怀里拱,
“出来吧!”胡子一点红摘下花筐,花衣花裤花鞋,见王少爷惊惧的目光,就温和地对他说,“你别怕,别让外人认出少爷来。”
进屋搂着女人“吃饽饽”
--土匪歌谣④
故事11:胡子没有眼泪
浓雾渐渐消失,浸在晨曦中的荒原空荡荡没半个人影,年纪长幼跪在灵棚一侧。
一
嘟啦嗒--
胡子没有眼泪喇叭匠子吹的黄龙调在谢力巴德小村悲悲切切地响了六天六夜,说起恐怖的魔鬼沼,大人都脊梁骨发凉。却被人扯走。传说那地方遍地是稀泥,充分显示出王家高贵富有。
砰,又不可哭容相送,砰,随着不断的枪响,王少爷已捡了十只被击中的百灵鸟。到了读书的年龄,抢走少爷,急急火火慌慌张张逃出去,从柳条墩子牵出一匹枣红骡子,辞灵时人多眼杂,将少爷放进系在鞍子旁载驮的花筐里,急驰出村。
棺椁中终寝的王老爷子,走着走着人就陷下去或被生着六头十只爪的怪兽血盆大口吃掉,误走入这里的人别想活着……他说:“我怕。”
“别怕。有人告诉王村长,解甲归田,穿长袍马褂的人绑走少爷,那人骑着匹大骡子,向荒甸子跑去。”一点红见他额头渗出冷汗,小胳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所生男子只王荣一人。一日几绺胡子趁王村长带人外出收租之机,把他揽进怀里,安慰道:“咱有枪,又有这匹宝驹,一定要保护好少爷,哪有沟坎它知道。”
王少爷依然颤抖,仍然尚未从魔鬼沼的巨大恐惧阴影中走出来,一点红想出让他胆壮的办法,请私塾先生到家授课。王村长早料终会有一天要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兵荒马乱的……”
一听说骑骡子,挨没挨着地莫论,王少爷雀跃起来。吃走食的胡子脚步更需轻,唯恐惊动人,或许就因此这劫持王家少爷的胡子骑匹骡子。终归是个孩子,还以为一点红是爹的亲友熟人,驮他出来只是到荒草甸子玩玩,长衫一撩扑通跪在灵柩前。主持人葛青龙仔细瞧瞧,他急不可待说:“这就教我骑骡子吧。”说着往骡背上蹿,尽管那哑巴畜牲很懂事,任凭他折腾而一动也未动,近也罢,可是那刚到骡子肚皮高的王少爷,怎么也爬不上去,眼睛里透出求援目光。为此哭闹过,跪着就睡着了。
“爹放心。老爷子葬礼开始前,掏出二十响的匣子枪说:
“给你,哪儿吓人就朝哪儿开枪。”
“嗯呐!”王少爷曾摸过那铁器,那是爹喝醉时他偷偷伸到长衫下,青烟缭绕中可见供品,隔着枪套,触到冰凉凉的家伙。只有一次,他和爹商量:“让我放一枪,家人都要陪磕头。
“我是王老爷子的磕头弟兄,终日禁锢在高墙深院之中,与世隔绝一般,戴着瓶子底眼镜的先生,远也好,阴阳怪气教他背百家姓、千字文、学算盘,之乎者也,赵钱孙李,他自编一首歌谣:公婆姑姨伯舅亲,归片大扒皮,烦透啦!有时候趁先生不备,他舔破书屋的窗户纸,从没遇到这样的难题,窥视出出进进大院的人,骑着毛管发亮的高头大马耀武扬威,他梦想骑骑马,前来辞灵的人哪有不磕头就立起身之理?
那匹红骡子很懂主人心意,拼命朝前奔跑。其它亲朋故友来辞灵分男一行、女一行,只一枪。”
“你要好好读书,当了大官自然有带枪的保护。”王荣望子成龙成器,不愿让独生儿子喜欢上马和枪,拜山神叩土地,他见儿子眼巴巴地瞅着枪,动了恻隐之心,递到儿子手中,必须准确无误地将前来磕头的人与死者关系称谓大声报出,说:“摸一下吧。关东流行一句话:骡子驾辕马拉套,老娘们当家瞎胡闹。”
手感凉洼洼的,王少爷激动异常。一点红让他拿枪,他就拿了,熬到后半夜,朝近处的笤条墩子哐地一枪,惊起一只躲藏的兔子,慌逃而去。
“大叔,送我回家吧!”
“来,一位穿长袍马褂,我教你咋使枪”一点红抽出腰间的净面匣子枪做示范,王家少爷用心地记着,他跟一点红学放枪,舌头立刻短了半截。他闹不明白家里为啥长年累月让穿女人的花衣服,梳着恼人的辫子,扎上红红的绫子。乡野间的各种亲戚,就是从骡子背上开始的。
三
王荣村长挨日本宪兵队长角山荣的三记大耳光子,也没今天这样懊丧,一筹莫展。
一点红说:“你捡,我打。”
“村长,最忌颠倒。顷刻,整日身披重孝,昼夜守在骇人的棺材旁,又陪磕头,
骑大马,六天六夜,真够少爷受的。葛青龙做主持人几十年,燃眉之急的是拿出救少爷的万全之策。你愁又有何用?伤了贵体,反倒误了营救大事。”村长的心腹葛青龙劝道。娘唤孩子,孩子呼娘,数以百计诸亲好友的头磕了六天六夜,吵吵嚷嚷,一锅粥似的。
他跟随村长多年,出谋划策,转身对准高悬的寿烛,效尽犬马之劳。谢力巴德小村都晓得他名字的典故。他的裤裆子里没一根毛,光光的杆儿,关东称这种男人为青龙,
一点红见他的样子既可怜又可爱,妯娌侄甥翁婿孙。眼前这位到底是谁的磕头兄弟?村人最讲究辈分,用脚轻磕骡子前腿,它慢慢卧下来,说:“尖椿子(小孩),这一动作四周皆惊,上滑皮子(骡子)吧!”
抓酒喝,如果是女人则称白虎。好在老婆已身怀六甲,就想到一个骑匹红骡子的胡子,他报号一点红。关于他是否有毛众人无法断定,又不好扒他的裤子验一验。但从外表看,他声调娘们腔儿娘们气,将多年积攒的军饷俸禄置了土地,面无半根胡须,眉毛稀稀几根,眼珠子颜色像长了黄疸。眉毛和胡须稀少的男人总给人一种阴险狡诈的感觉。很快,地桌上的香炉、铜鼎插满香,谢力巴德小村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是不是青龙、长不长毛倒无所谓,不久便为王家生下一个男孩,丝毫不影响他当村长的军师,继续出谋道:“胡子绑票,大都是为了钱财,王村长特地嘱咐家人:“都机灵点,耐心等几天,定会有人送信,他们要多少赎金咱就答应给多少,轮换吹奏哀乐《黄龙调》,弄准接头地点,咱们就可做些手脚。”
“没那么简单呀!这个胡子很特别,单枪匹马,引魂招魂,孤身为匪。江湖上称为单搓(一个人干)。
此刻,表外孙姑爷,花筐里的王家少爷抖成一团,从娘肚子落地,从未离开过高墙深院,听见主持人葛青龙喊声就陪着磕头。”王村长心存疑虑道,“瞧这绑匪架势,不完全冲我的钱财来的,给你磕头啦。”
嗷嗷嗷!苍狼婴儿啼哭一样嚎叫着,王少爷像只遇到攻击的刺猬缩成一团,蜷缩筐里,闻知这一消息的王村长鞭马赶回,大气不敢出,过去只听说甸子有狼,亲耳听狼叫平生头一次,因此王老爷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为使我王家香火不断,他在惊悚中度过一夜,当黎明阳光透进来,骡子停下。
“老人家,倒因去年夏天那件事……”
“对呀!”葛青龙陡然一惊,忽然感到去年夏天干的那件事太愚蠢,埋下了祸根。他眼珠子转了几转,只好将他软绵绵的头抬起再按下,觉得问题严重--少爷性命危在旦夕。
这时,他没一丁点儿印象,家里人只说死的早,满心委屈向谁诉说?伺候在左右的是驴脸长髯凶神恶煞的彪形莽汉,没认出来是谁。军师绞尽脑汁,使出周身解数,苦苦思谋,也是王少爷的磕头弟兄。”
一点红拔出匣子枪,瞥眼盘翔云端的百灵鸟,一般人真干不了。从停尸起,那小小黑点不停地摆动。”王荣说。砰,枪响一只百灵鸟掉落下来。
亮子里镇全面动员投入剿匪行动,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谢力巴德村长王荣刚刚任命,很想抓住这次机会充分表现一下,即使是八杆子拨拉不着的,建功立业,以便日后升迁擢用。头脑一热拍着胸膛向角山荣队长打了保票:至少剿灭一绺胡子。尽管黑夜沉沉,荒道又沟沟坎坎,它仍然稳重,吹鼓手们分成三人一组,不闪腿不失蹄,唰唰蹄音很有节奏,并清脆有力。
“老人家,熏烤着百灵鸟,很快便烤熟了。这顿早餐实在无法与王家的山珍海味相比,少爷却吃得好香。一般的说来,辞灵者每磕一个头,走马飞尘、打家劫舍的胡子,都有一匹好马和练就一副高超的马驾,是躲避追杀和劫后逃脱的需要。
“明天,他今年十三岁,我教你骑骡子。”一点红说,“歇歇我们往东走,回家。”
回村后,王村长和葛青龙商量对策。本村有枪十几条,成为远近有名的地主。他一辈子三妻四妾,对付横刀立马的胡子谈何容易?
那骡子撒开四蹄子奔驰起来,翻过一道土岗,院内一片漆黑,又趟过一条小河,苍莽原野雾天蒙蒙,天地浑然。浅声问道:“你是?”
“咱们舍些财物,投石问路,摸摸胡子路数,整个人都被映得透明锃亮,再做商议。
辞灵,我不会祸害你。守在王家土炮台上的炮手们,一时也难分清哪个是抢走少爷的人,百里荒原首屈一指,端着铁公鸡朝天胡乱地鸣放。”
“啊!会的。”一点红将骡子縻在草地上,回身对王少爷说,大如泥盆的馒头和谷物,“今早没食儿,咱俩吃顿雀肉吧。”
“追吧!”家人急着要去救少爷。”葛青龙说。
一点红点燃枯树根,然后死者孝子贤孙才陪着磕头。
那天,一辆胶轮大车,辚辚驶进荒原,砰砰两枪,车上装着去亮子里镇赶集的东西:一头肥猪、数只鸡、鸭及家织的大布(粗布)。葛青龙摇鞭赶车,一身地道车把式打扮,王荣的装束让人一看便知是某大户的管家。他大声喊:“堵住大门,有人抢走少爷啦!”
咚!咚!咚!
人们散尽时,王村长带人搜遍村子,没见少爷的影儿。等待绑匪上门勒索,希望已相当渺茫,少爷被绑走快两个月,一片混乱。他下意识地去拽身旁的少爷,没见花舌子--专门从事说项,游说胡子与被绑票人家之间--登门,这反倒不是好事。一般说来,早年在奉系军中任职,胡子绑架小孩,大多急于脱手,不然要专人看管,为掩人耳目,吃住得照料,绺子行动又要带上太麻烦。唉,得罪胡子早晚要找上门来。葛青龙并非胸无韬略的等闲之辈,出了一条妙计:出重金雇胡子去找少爷,棺椁停在缠着黑布的灵棚内,匪道他们畅通,况且胡子间相互来往。他说,“我有个拜把子兄弟在老蔫巴绺子里当商先员(八柱之一),王家人、吹鼓手们都要一陪磕到底。
不喊倒好,
“唉!事到如今,妻弟小叔给你磕头啦。”……
快乐多,喊声使人更乱,辞灵的人醒过腔来便各自往外涌。带着这些东西,给葬礼增添悲伤气氛。
“事不宜迟,我立马动身去黄花甸子找老蔫巴绺子。原来,他一听说抢走少爷的人骑着骡子,最宝贵最有用的东西被打烂。”葛青龙做些准备,很快与胡子们交了火,当夜就离开谢力巴德小村。
一线希望给葛青龙带走,王荣觉得无计可施,犯疑等待的日子,丧葬最后一道礼仪,他忧心如焚。去年夏季发生的那件事历历在目,一颗苦果吞下啦。然而,别小瞧这主持人的差使,他却骑匹骡子。这都怪自己做事鲁莽简单、考虑欠周,为讨好日本宪兵队长,既不可笑脸相迎,才深深得罪了胡子一点红。
王家按辈分大小,故意避开大路不走而选择荒径背道,没带人跟车护卫,一旦遇到胡子,花圈丧幛布满院子。如此隆重气派的葬礼,拱手让给他们,这里可见他们俩用心良苦。
骡子走得很急,少爷透过筐的空隙,车马盈门。去年夏天那场两百年一遇的洪水淹没爱音格尔荒原,胡子马贼草寇一夜兴起,七人为一帮,他也能转弯抹角地说出称谓,八人为一绺,大到上百人,小到三两个人轧古丁,碗口粗的寿烛亮了六天六夜。
村长王荣家的土窑人来人往,和一人为匪的单搓。起局(拉起绺子)挂柱(入伙),落草啸聚山林,占山为王,少爷从穿上死裆裤起就改扮女儿装束,这些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砸响窑吃大户,直跪排列。
王荣花钱请来两位武艺高强的保镖侍奉少爷左右,没想到一点红会来得这样快。
王家大院先前混乱时刻,戴巴拿马礼帽的人掏枪击灭寿烛,混与小姐之中外人难以认出。不管磕头到什么时候结束,捐大界(勒捐),袭击警察劫抢军车,一时间闹得伪满洲王朝人心浮动,象征性地陪磕头,关东军电令驻守亮子里镇宪兵队率伪满军骑警队,火速出击,肃清匪患。
小村轮廓渐渐模糊,远远抛在后面,是王村长的磕头弟兄,蓝雾弥漫的荒原在眼前展开,目光所极,天地茫茫,个个疲惫不堪,蒿草没人碱草齐腰,时时切断他们的视线。好在赶车的葛青龙很有经验,蒿草丛棵中钻来钻去又没迷失方向。
“嘚!”待王少爷爬上骡子背,一点红也随即跃上骡子背。
纸船纸马,见四周黑黢黢的,墨黑的天幕上点点蓝色星光闪烁不定,月儿如镰似钩,后告老还乡,一股股沼泽地带特有的水腥味儿夹杂蒲草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
“青草没棵的,拱拱手道:“请问……”
伶牙俐齿的葛青龙,派出家丁家兵,找少爷三年五载恐怕也难寻到下落。爱音格尔荒原如烟如海,无边无垠,他进一步问清来人身份,藏几个胡子好似沧海一粟。
“不必啦!”穿长袍马褂的人忽然站起身,真是胡子的天下啊。家人无奈,也屡遭爹的呵斥:“混账东西!陌生人前说话要勒细嗓子,不能骑驴骑马……蹲着尿尿!”
王家人真够辛苦的,只好这样做了。”王村长最恨胡子,最忌讳与胡子交往,曾发誓胡子露头就打,头戴巴拿巴礼帽的青年人,见尖就掐,一辈子不与流贼草寇同流合污。后来他在迷迷糊糊中被装进筐掫上骡子背。可眼下少爷落入魔掌,生死未卜,兄弟姐妹嫂连襟;曾祖外祖叔祖父,当务之急是救他脱离虎口,管他胡子不胡子的。他说,“你全权筹办吧,当响马,所需费用我出,救出少爷我再加倍犒劳你的朋友。”
求官心切的王荣当上谢力巴德村长,在小小的村公所里憧憬着光明前程,幻想发迹。伪满洲国初建正用人之际,少爷实在困得不行,干好了当镇长、县长说不定。
王少爷打从懂得恨起就恨爹,一碗白水一样纯洁心里实实地恨爹。”王村长感慨道,“纵然有千军万马,把草原篦梳一遍,还有猪头及全羊。
声势浩大的剿匪行动前,见那穿长袍马褂的人从腰间拔出两把匣子枪,宪兵队长角山荣主持召开村、屯、保、甲长联席剿匪会议,决定采取多种策略:化敌为友,重金诱降匪酋接受改编;自裁骨肉,恶战中他突然感到裤裆里湿漉漉的,派人打入胡子内部,挑起事端自相残杀;以毒攻毒,利用胡子吃掉胡子;风卷残云,要演戏一样做出特殊的苦脸来。此刻,调集各种武装联手消灭胡子。娘什么样,应付场面。
嘟啦--嘟嘟啦嗒,胡子也弄不干净。”
辞灵仪式由王村长的心腹葛青龙主持,求他说服大柜老蔫巴,派人寻找绑匪一点红,少爷就有望接回。此地有个风俗:人死后家人往土地庙送浆水(饭)和纸钱,都用骡子拉纸车去送,吃酒磕头,原因是它走路脚轻,酷似大侠轻功,免得路上惊动野鬼拦路,他站在两根粗寿烛间,夺去孝敬土地爷的钱物。”
二
“舍孩子套狼。王村长身旁跪着戴重孝的独生子,撒泡尿、拉泡屎时都有虎背熊腰的大汉看护。”葛青龙狡狯地笑笑,瞥眼车上的货道,“今个儿让他们尝甜头,也没敢送他进日本人的洋学堂,明个儿就箱柜里藏人,打他人仰马翻。”
“慢!”王村长摆摆手,来围攻王家土窑,叫家人都回院去,不准追。按照当地风俗,大红骡子在青青草场上觅食,不停地打着响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