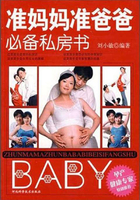通过网络认识的支教男孩尹鹏飞,就读于黑龙江省绥化学院中文系,2008年8月来到绥棱县绥中乡前五村小学,开始实习。他说他教的学生大都活泼开朗,只有女孩曲文玲落落寡欢,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
曲文玲个子不高,比同龄的孩子矮一头,写作业时总是站在地上或者半跪在凳子上。她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自顾自地安静坐着,望着别的学生玩耍,从不多说一句话。每逢老师上课提问,她也只是摇头不语。小文玲习惯直勾勾地盯着黑板,看得出她心里装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七八岁的孩子一玩起来就忘记天黑,而曲文玲的世界似乎永远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每到下课时,她基本上呆在学校操场里的那棵大杨树下,傻傻地看着操场上的同学们玩耍。微风徐来,轻轻吹起她破烂的衣角,弱小的她与身后的大杨树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怎样一个孩子呢?作为一个初执教鞭的新手,他绞尽脑汁,觉得应从语文课开始,必须让她开口大声说话。每次上课,他特意让她照着课本读拼音,开始时她总是摇头。她的同桌,一个淘气的男孩子说:“老师,她家可穷了,她在学前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这时,小文玲的眼里闪着泪光,小脸涨红,勾着头。他的心仿佛猛然间被刺痛了一下,他必须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找寻到快乐。
他向同事打听了她的情况。原来,小文玲的妈妈是弱智。因为众人的嘲笑使小小年纪的文玲产生了心理阴影,所以才不愿意和别人说话。他又进一步了解到,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弱智的妈妈,而爷爷一只眼睛失明,家里所有的活都靠没有文化且年事已高的奶奶。孩子的世界应该是美好而多彩的,不应该满是阴霾,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还她孩童应有的天真烂漫的笑容。
此后,他每天上课都尽量提问小文玲,课后把她带到办公室聊天。起初,她有些怯懦,站在很远的地方,低着流满汗水的小脑袋,小手不停地扯着她破旧的衣角。他问她话,她都用摇头和点头来回答。他并没有气馁,鼓励她,后来她依然话语不多,但眼神里却多了坚定的成分,不再羞怯和胆怯了。
半个月后的某天放学时,一场大雨来得突然,没有准备的他想一口气跑回一里地外的宿舍。跑到校门口时,曲文玲拦住了他。
“家里有人来接吗?”他拉起她的小手,“老师送你回家!”
她扬起小脸,一脸灿烂地说:“我在等你,我有雨伞,老师你可不要淋雨啊!”
他一把抱起小文玲跑了起来,因路面比较滑,一不小心和小文玲一起摔倒了。他俩一身泥水,小文玲笑得前仰后合,像花朵在和煦的风中尽情开放。这小小的改变,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他托父母买了一张拼音图,挂在了班级的墙上,学生们都显得很兴奋。上课前,他让每一个人都照着图画读一遍。轮到曲文玲时,她怯怯地站起来,支支吾吾地读。他耐心地鼓励道:“没关系,你发音很准确,再大一点声就更好了。”在他的鼓励下,她缓解了紧张情绪,声音一点点变大,21个声母她分了三次读完。他特别高兴地说:“对于曲文玲同学的进步,我们大家给她一点掌声吧!”在全班同学的一片掌声中,他看到她红红的小脸有些腼腆地笑了。后来,曲文玲上课时,慢慢地开始主动发言了。
教师节他要回家看看。就在他临走的前一节课,学生们整齐地坐在教室里,其中一个男同学带头说:“老师,祝您节日快乐!”他们一起唱了一首《北京欢迎你》,作为教师节的礼物特别献给他。曲文玲也加入了合唱队伍,他清晰地看到她小脸上笑容的灿烂,听到了她深情的歌唱。
后来,他找到了那几个平日里最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告诉他们,以后不许再嘲笑曲文玲。他还特意挑了一个学习成绩好性格也好的女生做曲文玲的同桌,帮助她学习。在他的引导下,班上的学生纷纷主动和她说话,和她玩耍。而她,也渐渐地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中,学习也进步了许多。
半个月后,他又一次来到曲文玲的家。瘦小的曲文玲正坐在小板凳上洗土豆。她的爷爷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老师呀……我们小玲呀……她会笑啦!”
孩子的潜质需要老师的挖掘,小文玲的变化,都源于尹鹏飞老师的爱,“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孩子。
在我们身边,因为种种原因,一些本应承欢父母膝下的孩子,却缺少父母的亲情呵护,以幼小的年纪、脆弱的心灵、稚嫩的肩膀承担着命运给予的重压。对于别的孩子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事情,在他们眼中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对于他们,充满爱意的老师目光,暖暖的同学情谊,孤独时,困难中,抬头就能看到的那种鼓励,就是心底最深的向往。这样,就需要老师更细微的情感付出。
尤其是,女孩对比男孩,更容易触景生情。她们心目中所需要的老师的爱,就是想哭的时候,出现的怀抱,是电闪雷鸣时,出现的房子。因为,在缺少父母之爱的日子,老师就是她们暗夜里的那缕月光,就是她们心情低落到地狱之时,最先遇到的那位天使。
河南留守儿童方治乾,叫阵八国《罗马宣言》
提到中国家庭教育问题,学生心理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都绕不过一个词:“留守儿童”。与国外的单亲家庭孩子问题一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2000万以上的越来越庞大的数字,成为近年中国农村最疼痛的铅字摆在那里,曾数度成为中国高层会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的焦点。为此,我曾走访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多省农村留守儿童。
但认识河南农村留守儿童方治乾,却是在调查走访结束后的2009年11月世界儿童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对外部记者易凌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其中对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我们有过深层次的探讨。易凌告诉我,同期选定的三位嘉宾,是与中国青少年教育问题相关的三方人物,与我们同期接受采访的,就是参加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青少年八国峰会,且敢于叫板《罗马宣言》的河南省信阳市罗山高中新校区二年级男生方治乾。
不能不说,今天的方治乾,是幸运的。
他的幸运,自2009年开始。中国选送参加“青少年八国峰会”的孩子,只有三个名额,而他是其中的一人。品学兼优的方治乾脱颖而出。
这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峰会每年与G8峰会同时同地举行,与会儿童有机会同出席G8峰会的各国首脑商讨国际问题。方治乾参加的第五届“青少年八国峰会”,于2009年7月3日至14日在罗马召开。除八国集团成员国各派4名代表参加外,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也应邀派代表出席会议。在罗马,54名年龄在14至17岁的各国优秀少年汇聚一堂,就经济危机对儿童的影响、气候变化和非洲发展3个主要议题展开广泛讨论,并制订本届的峰会行动计划。
可以想象,对于方治乾,一个从偏僻农村来的孩子,一个平时连与父母交流都少有机会的孩子,陡然有了机会代表国家,关心起世界各国的大事来,那是一件怎样神圣和令人激动的事情。当他迈步罗马会场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骄傲与自豪。或许还没等到罗马的那一天,就在获得参加活动通知的那一刹那,在北京天安门前,他的心中早已装下了有一个国家之大的神圣和庄严。
这应该是他在此之前所没有的,或者说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明晰的神圣与庄严。
那是一次怎样有趣的聚会啊!
那么多国家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风格,甚至不同手势,还带着一些顽皮和随意的孩子们,可以在一起学着各国首脑板着脸孔谈国家问题,还可以相互学习各国语言,将每一个话题谈到最好,最有趣,最理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他还可以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在欣赏罗马古建筑的同时,可以去畅想故宫,去寻找罗马与中国北京的任何一处古建筑群的区别。
罗马对于他,是一次难忘的盛会。
那些只能从电视上看到,从来没有想到能够见面的各国首脑,竟然可以同在一个会议活动空间。他可以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他可以问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首脑,或者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首脑,儿童在成人或者在国家面前,享有怎样平等的待遇和优越?首脑们所在的国家对待儿童问题上有哪些不足?如何改进等。他甚至可以问德国的女总统:“作为德国的首脑人物,你在处理国家事务的同时,你如何恪尽母亲职责,你怎样处理与孩子的关系?你的亲子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孩子现在学习成绩如何?母子关系如何?”
无论方治乾在走进会场之前,是一个怎样的留守孩子,可以说,八国峰会提供的这次活动平台,注定对他有所改变。改变了他的幼稚,他的腼腆,甚至一时充溢于心的少年激情会抹除他存留在心底淡淡的忧伤。在那样一种特别的场合,无论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孩子的大脑都会经历从紧张、胆怯、试探表达这一变化,经历种种稚嫩思想的优胜劣汰。正是如此,在这次峰会上,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他,尽管一直仍然免不了紧张、拘谨,但总算以较好的英语和外国代表进行了比较好的交流,他甚至利用平时学习的环境保护知识勇敢地谈到了自己的见解。
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有方治乾的坚持,青少年峰会通过的《罗马宣言》关于教育的那部分,增加了一句话:“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的一部分,我们要求八国集团领导人确保学校获得资金用于心理咨询以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他的一句话,赢得了各国首脑的赞许,写进了《罗马宣言》里。
如果说在参加罗马峰会之前,作为留守儿童的方治乾是孤单寂寞的,那么,自此之后的方治乾再也难得孤单寂寞。少年的身心,已经开始浸染太多的鲜花和掌声。
在我和易凌的连线中知道,对他的采访,易凌是找到他在河南的家里进行的。
因为出席罗马的会议,方治乾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媒体趋之若鹜,各类社会活动纷至沓来,因为这次机会,他得到了牵一而动全身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整根链条似的关注,他曾经的寂寞与孤单自从接到罗马会议通知那天起,已不复存在。
而更多的孩子却得不到哪怕是自己学校的特别关注。
“我不希望其他孩子有我那样的童年。”面对记者,方治乾坦诚道出自己的隐痛。
方治乾年仅3岁时,母亲谢奎娥离开他哥弟俩到沿海打工,12年来,母亲仅回家三次,与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到200天。7岁时,父亲方有平也到母亲工作所在的服装厂浙江桐乡,成为一名人力三轮车夫。方治乾和哥哥方朋交由年逾六旬的祖父母照顾,在此期间,他和哥哥无时不刻不在想着爸爸,也想着妈妈,但没有办法,爸爸妈妈如镜中月,水中天,有,但总是看不清,摸不着。
“我能想起来最愉快的记忆里没有父母。”采访中,方治乾说,童年是他不愿多谈的话题,因为“总是很孤单”。
可母亲能怎么办呢,别家孩儿都是这么过。方治乾的家乡,河南罗山县有73万人,近九成是农村人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外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母亲在养家糊口和照顾孩子之间,只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
小时候与母亲分离的场景,方治乾一直记得。母亲离开时,他和哥哥爬在地上抱着母亲的腿大哭不让母亲走,母亲是把腿别开,边跑边哭着离开的。
“我们老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就总说不好好学习就对不起他们,很少问我们怎么想。”方治乾说。在浙江打工的父母,除了十天左右一次的电话,几乎没有其他与孩子们交流的方式。在每次让他们既期盼又失落的几分钟左右的通话里,父母主要督促孩子好好学习。他们在成长中必经的每一种疼痛,无人问及,他们只能在没有父母的孤寂中自己面对自己的困境。甚至望眼欲穿,几年难得看到父母的踪影。
方治乾说,他最喜欢的,是过年放鞭炮时的味道。因为每到过年放鞭炮的时候,父母有可能回家,只因父母有可能回来,只因对父母团聚的揪心期盼,在常人眼里唯恐避之不及的刺鼻的硫磺味,在他的情感里竟变得格外珍贵起来。
而远在外地的父母却希望作为父母的威严能绵延千里依然有用,他们更期待孩子能感动于自己日夜的勤劳付出而自律自强。然而不在身边的父母在渐渐长大的孩子内心,却成了两个陌生人。
母亲谢奎娥接受采访时曾坦言孩子跟她“不太亲”,但直到兄弟二人第一次到浙江过暑假,方治乾常把她误叫做“奶奶”,她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称职”。“可我能怎么办呢,别家孩儿都这么过啊。”谢奎娥说。方治乾的班主任王世海说,这个群体的孩子比较容易识别,“绝大多数学习刻苦,但不善交流,习惯沉默,没有县城里的孩子那么活泼自信。”
方治乾对自己的“不一样”则更加直白:“我想我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比如胆小,见了生人就躲,有问题也不想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哥哥就更内向了,现在学习压力大,他一下子长了很多白头发。”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环境的影响,在罗马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就在同龄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或是英国首相布朗愉快对话时,方治乾一次次鼓起勇气,想请教德国女总理默克尔“怎样在做好工作的时候,扮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兼顾家庭”时,最终,他没有提出最想问的这个问题,哪怕他的英语没有障碍,能够与总理对答如流,但因为“心理上的障碍”还在,即使有了说话的最优环境,却还是不能适应过来。
因为“心理上的障碍”,男孩方治乾永远地失去了这次与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平等对话的机会。失去这次机会,也成为了他永远的遗憾。
他一定为此懊恼过,因为当时若提出这个问题,德国女总理默克尔一定会给他有趣而满意的答案。
留守的疼痛是刻骨的。也正是想到了自己刻骨般孤寂的童年,在这次峰会上,年仅16岁、看上去有些腼腆的方治乾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与自己有关的问题,与中国农村2000万以上的孩子相关的问题。也勇敢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方治乾作为留守儿童中极少数的幸运者,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获得这样的机会帮助自己,可很多孩子却是在孤独地成长。
易凌和我有同感。
全国妇联2009年5月发布的报告称,中国目前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几乎是2006年的3倍,达到5800万。而14岁以下的儿童就超过4000万。日益突出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2006年由国务院牵头成立了应对该问题的专题工作组,保护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措施也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教育部门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在中西部地区改建和修建了万余所农村寄宿学校,以确保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