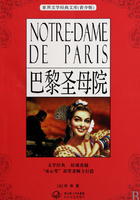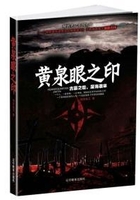秋玲仿佛忽然间变成了一只画眉鸟儿。声音那么脆亮甜润,脚步那么轻盈蹁跹,连穿过两个夏天的一身纺毛呢接待裙服,也显得飘飘逸逸,像孔雀张开的彩屏。
上午送走两拨内宾。一拨是广东那边来的,一拨是黑龙江那边来的。一南一北天涯相隔,语言、心态、询问和参观的内容,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之处。但两拨人都以满意和感激的心情离去了。下午一上班来了一拨外宾。据翻译说,其中有英国人,还有两个德国人。在河滨公园的八角亭上,秋玲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一番,接着又讲了几句德语。这使外宾兴奋不已。尤其两个德国人,伸出拇指连声叫着:“逊!逊!”“VieIeuDnak!”读过北京外语学院,又到国外实习过一段时间的翻译,也惊奇地询问秋玲是哪所专科学校毕业的。
回到接待处,表针指到三点五十分。秋玲打开收录机,一边听着歌儿,一边对着镜子梳头、搽珍珠霜;脚下还不由自主地和着曲调的节奏,轻轻挪着舞步。大桑园的接待员跳舞是必修课,秋玲的舞跳得尤其出色。
“咯……”几个接待员乐成一团。
秋玲觉得奇怪,“你们笑什么?”
“笑你呀!秋玲姐,你真成了歌里唱的:‘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眉毛弯弯眼睛大,眼睛大;红红的嘴唇雪白牙,雪白牙;粉红的小脸,粉红的小脸赛晚霞--’”
机灵调皮的姑娘们,扯着秋玲的裙子又唱又跳。唱完跳完,又是一层笑浪。秋玲要算是远东实业总公司仅有的几位与下属亲密无间的中层干部呢。
“哟!歌也不让唱,舞也不让跳,你们非让我当老太婆才行啊?”秋玲也笑着,笑得那么天真。纯洁,同一个十八岁的妙龄少女没有丝毫区别。
秋玲的变化确是引人注目。这种变化是昨晚与岳鹏程再次谈过之后出现的。岳鹏程不仅帮助解决了贺子磊户口迁移的事,而且答应以后两人以兄妹相待,不再做那种让人脸红心跳的事。缚在心灵上的无形的绳索解去了,从办公楼出来,秋玲觉得自己正像书上写的,成了一只出笼的鸟儿,飞上了高阔、辽远的天空。
与贺子磊建立起特殊关系的这半年里,秋玲一直被缠绕在一种沉重的、难以言喻的苦恼中。一方面,她担心自己同岳鹏程的暧昧被贺子磊察觉,影响关系的发展。
她从心里确实觉得应当对得起贺子磊,并且小心翼翼地中断了与岳鹏程的接触。另一方面,她又担心岳鹏程知道了自己同贺子磊的关系,知道了自己结婚的打算,会暴跳如雷妄加干涉,造成两人多年友谊的破裂。而从心里说,无论从个人感情或者从实际利害关系方面考虑,秋玲都决不愿意与岳鹏程翻脸成仇。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做到既与贺子磊美美满满结婚,又与岳鹏程继续保持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几个月里秋玲费了不知多少心思。那天决心找岳鹏程谈开时,她是设想了种种情况和办法,做好了应付的种种准备的。然而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她的一切目的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全部达到了。从此,笼罩在心灵上的无形的阴影消除了,她尽可以去幸福地生活和工作,尽可以自由舒展地去歌唱和翱翔了!秋玲的喜悦和轻松,是的的确确形同一只飞出樊笼的鸟儿。
因为岳鹏程,秋玲已经失去了一次爱情。那是羸官给予的。在羸官从技工学校回到村里和当上木器厂厂长的几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她常常可以遇到那个充满生气的小伙子投射过来的电火似的目光。那目光时常烧灼得她神思迷离。她喜欢这个小伙子,时常盼望见到他的身影。但她不敢接受那目光的召唤:她大他两岁,而且与他的父亲产生了暧昧。一次,秋玲无意中称赞了一句前来参观的一位客人穿的骗幅衫。一个月后,羸官忽然告诉她,他已经为她从广州买回了一件蝙蝠衫,比她称赞过的那一件还要漂亮、洒脱上几分。他约好晚上给她送到接待处来,说要亲眼看着她穿上跳一次舞。晚上她去了,他却失约了。她回到家中时,一件被剪得七零八落的蝙蝠衫出现在院门的扭柄上。她惊诧不已,但也很快猜到了因由。不久羸官与岳鹏程分手了。虽然任谁也没有透露这方面的信息,秋玲却明白,那儿子的决绝离去,与自己并非全无关联。羸官在小桑园干出了功业,两人绝无往来。偶尔碰面,羸官不是回避便是傲然睥睨。秋玲也只能低头匆匆而过,心中却总要泛起几多懊恼。
人生难得几知己。岳鹏程算得上一个知己,但她更需要一个可以相互依偎、共同走完生命航程的知己。她已经失掉了一次机会,决不能再失掉第二次!
一个女人即使浪迹天涯,终了也需得一个归宿。贺子磊便是秋玲的归宿。
秋玲急于见到贺子磊,正像一个久别的少妇急于见到自己的丈夫一样。昨晚从岳鹏程办公室出来,她直接跑到建筑公司。那间“工程师室”门上把着铁将军。人们告诉他贺子磊到烟台一号工地了。头午秋玲从电话里知道贺子磊回来了,正在休息。她不忍心去打扰他,拿定全意下班后再去。送走外宾后,她却等不下去了。
“有客人来你们接待一下。有人问,就说我马上回来。”秋玲向那几个姑娘说。
“秋玲姐,你就尽管走吧!”姑娘们笑嘻嘻地把她驱逐出门。对于秋玲与贺子磊的关系,她们早就心照不宣,等待吃喜糖的那一天了。
秋玲出门先奔宾馆,装作有事似地跟值班员拉了几句呱,这才当作顺路,朝建筑公司那边去。
贺子磊原是大连一个设计院的工程师。毕业于同济大学,据说在学校时就曾得到过着名土木工程专家李国豪教授的青睐。到设计院一年,他的才华便显露出来。
他设计的星洲住宅区、黄石会馆,在行业评比中连获“最佳”。党委书记看中了他,培养他人了党,提前晋升为工程师,并把毕业于师范大学、分配到一个研究所工作的“千金”嫁给了他。那“千金”在大学时有过一个情人,被拆散后仍然暗中卿卿我我。一次两人正在做爱,被贺子磊撞见抓获。他断然提出离婚。党委书记和“千金”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抢先行动,反诬贺子磊道德败坏,与女流氓勾结。仅三天功夫,贺子磊便被逐出了设计院和那座海滨城市。他在村里推了三年小车,前年岳鹏程闻讯后专程前往,张口月薪三百,把他聘了来。过去建筑公司出去,挣的只是个功夫钱力气钱。贺子磊来后,设计施工一揽子兜过,利润一下翻了几番。“请来一个坏分子,变成一个财神爷。哪儿有这种坏分子,你们尽管朝我这儿送!岳鹏程在外边时常夸口。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变成财神爷的坏分子,后来还会变成他的“情敌”!
秋玲与贺子磊真正相识,是在一次陪同外宾考察时。那是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建筑史的几位学者。因为专业性太强,只好请贺子磊一起陪同介绍。那几位学者开始没有瞧得起这位根子扎在泥土里的工程师。只谈了十几分钟,学者们就愕然了。流利的专业性极强的英语,古今中外南北东西乡村建筑的异同演变,以及贯串于这些介绍中的独到的见解,使学者们夸张地把他称为“中国未来一代的贝幸铭”。秋玲从那一次才知道,这位沉默寡言的“坏分子财神爷”,是一个远没有发挥全部才学的卧龙伏凤式的人物。
他们交往增多了。先是秋玲跟他学习英语。贺子磊德语和日语也懂得几句,秋玲也学。但真正弹拨起秋玲心弦的,还是另外一件事。那次因为工作上的事,贺子磊找到秋玲家中。当时彭彪子正倚在墙根的泥土地上,露着又脏又丑的肚皮晒太阳。
秋玲怕丢人,连忙要把彭彪子喊起来。贺子磊却上前尊敬地叫了声:“大爷,晒太阳啦!”在秋玲记忆中,见了爹的人只有捂鼻子。斜眼睛、吐口水和扔土坷垃的。
喊声“彪子叔”“彪子哥”的极少,而且算是极大的情面。叫“大爷”并且问候的,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这已经使秋玲受了感动。贺子磊讲完事情后,又特意过去与彭彪子拉了几句呱,让他保重身体,还拿过一块塑料布让他垫到身子下边。“大爷这一辈子也真是不容易。”离去时贺子磊对秋玲说。
这个在贺子磊看来十分自然的情形,在秋玲心田却播下一颗种子,一颗用敬重和爱戴浇灌的种子。一个晚上,当她听完了他平静地讲述的那段被开除还乡的往事时,那颗种子便萌生出了爱情的芽苗。这次是贺子磊感到惊讶,秋玲却觉得是再顺理自然不过的事了。建筑公司是宾馆的近邻,不过几分钟工夫,秋玲已经推开那扇“工程师室”的门了。工程师室由里外两间大屋组成,里间是两张单人床,外间摆着几张特制的斜面设计案。室内很静,一个腰身颇为高挺的身影正伏案在画着什么。
门是虚掩的,秋玲蹑步上前,那人丝毫没有察觉,便被突如其来的两只手捂住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