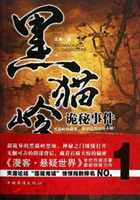米副这时很认真地看了一眼妇女主任,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喜欢上她了。她干工作是那样泼辣,与人为伴是那样大方,说话办事又是那样有礼有节,遇了问题又是那样聪明智慧,在乡下你到哪去找这样的女人?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对她的追求。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米副想出了一个游戏。他从路边上扯了一片草叶,说,主任,你认识这种草吗?主任说她不认识。米副告诉她,这叫做姻缘草,能测男女有无姻缘关系。主任很好奇地看了看那片草叶,说,它怎么测姻缘?米副说,我告诉你怎么测好吗?主任说,好啊!米副说,你我各执草叶的一头,使劲一拉,草叶就会从中间断开,如果是一个斩齐的断口,那就说明两人没有姻缘,如果是一凹一凸,那就是有缘分。妇女主任说,有这么神吗?米副说,就这么神!米副说着,自己捏了叶尖那一头,让妇女主任捏了叶柄那一头,然后,两人使劲一拉,草叶从中间断开,米副那一头是凸形,妇女主任那头是凹形。米副红了一下脸说,天让我们有缘啊!妇女主任也红了一下脸说,真的吗?我不相信!
此后,两人都不再说话,他们的思维世界像海洋一样,让他们游不到边,让他们挣扎,让他们拼搏,让他们激动,让他们疲惫,让他们茫然。他们默默地走着路,被今年的新叶片排挤下来的老黄叶在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把他们的脚步声放大得很响,很脆,但也很长,很韧。有鸟儿突然从树林里掠过,从这棵树到那棵树,像箭一样地快;一只螳螂突然飞落到米副的肩膀上,螳螂的翅膀像风摇树枝一样地叫,一副战无不胜的高傲!许多弯拐的山路和深绿色的微风使他们的心情又平静下来。爬上山坳,他们似乎从大海里伸出头来看到了海岸,他们是那样需要喘息。他们互相看见了对方,米副朝妇女主任笑了一下,妇女主任也朝米副笑了一下。他们的眼神在空中绞缠了一刻,但马上又撤开。米副收回眼神时,体内有一种东西膨胀起来,胀得他呼吸有些困难,有些粗重。
山坳上有一棵云雾喂大的老树,长得也那样地像云雾!树桠上有当地人用石头压上的香纸,不知是谁的小孩得了毛病,来求过这棵树爷爷,树上还贴着红纸写的咒语: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亮……树脚下四块石板封成一个土地堂,堂前烧了不少的香纸。前面有人在这里歇过脚,地上还丢有拗断的枝叶。米副想打破他们沉寂的世界,他打了声长长的呵嗬,呵嗬像一道巨浪滚过密密挤挤的山峰,在天脚下起伏。呵嗬也把风唤来了,于是,他们的衣服在风里拍打着身体,米副指着古树脚下专供过路人坐下来歇脚的石板说,我们坐坐吧。米副坐下来,把一块很光滑的石板往自己身边拉近一些,示意妇女主任也坐下。妇女主任把绷得过紧的裤脚往上提了提,然后往下坐,就在她屁股快落在石板上时,米副心里一紧,把石板抽掉了。妇女主任坐了空,仰天翻倒在草地上。于是,她红着脸张开双臂说,你要死的!
还不快拖我!米副此时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他马上抓住了妇女主任的手,两双手一下子扣紧。但是,妇女主任要往上起来时,米副却朝相反的方向使劲,把她往下压了。一种来自体内的膨胀使米副的脸开始变形,五官也开始变形。妇女主任马上觉得自己的判断错了,米副可能不仅仅是跟她开个玩笑,他是要超越玩笑的界线。妈妈教给她的男女知识让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此刻应该怎样应对,如果她急于反抗,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她很冷静地说,米副,你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吗?米副慌忙地在她裤头上和衣服里寻找着什么。妇女主任并没有使劲地反抗,她只是很冷静地点了一下米副的一个穴位,米副就实在忍不住,像狼嗥一样地叫过一声,一种东西突然从身体里跑了出来,他的脚手突然软了,仿佛一身筋骨全被抽掉。这是她妈教给她的绝招。米副软软地趴在妇女主任身上。妇女主任看着他说,米副,你好好看看你把谁压在下面了,你是莲花乡的副书记啊……米副立刻翻下来躺在草地上,双手捂住脸,死了好一会儿,连呼吸也听不到了。妇女主任使劲拉开他的手,他突然蜷缩着身子哭喊了一声,又把自己打了两耳光。
妇女主任同情他,可怜他,拉了他的手说,起来,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你坐起来,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米副坐起来说,主任,我对不起你!我鬼摸脑壳了!
妇女主任说,我理解你。一个三十岁的健全男子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怪你!
米副还是说,主任,你太好了!我真对不起你!我……妇女主任说,是我自己太不在意了。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你唱的那些山歌。于是,妇女主任轻轻地哼了两首:
清早起来懒稀稀,旁人门前望人妻。
人家骂我是傻子,饱人不知饿人饥。
郎唱山歌远扬名,惊动庙里众鬼神。
地里蚯蚓唱成蛇,路边石头唱成人。
妇女主任想把米副心情哼平静。米副见妇女主任还能这样跟他说话,心情真的开始慢慢地平静。
这之后,倒是妇女主任心情无法平静。刚才如果不是自己冷静,那就倒墙了。如果那样,要么委身于米副,无限期在乡里工作,连孩子也可能在乡里上学;要么告了米副强奸罪;要么,哑巴吃黄连……哪一种结果都让她不愿意!这里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乡政府,这里的日子,就像天边挂着的那片缺月。妇女主任想尽快恢复平常的心情,她说,米副,你以后不要给我唱山歌听了。
米副说,以后,什么歌也不会唱了。
妇女主任说,怎么不会了?
米副说,那些歌本就不是原有的,是我现想现唱的,现在没有了那种激情,怎么也想不出来。
妇女主任说,米副,你好肚才啊!那些歌唱得几好!我真想全都记下来。
米副说,主任,你别笑话我。那都是我唱出来的糊涂话。
妇女主任说,真的,那些歌真好。可惜我当时没有记全。
米副说,这些山歌,我们乡里二十几个大龄干部,谁都想得出。
妇女主任说,那以后,我要他们唱。
米副说,你千万不要他们唱。山歌无假戏无真。唱到一定时候,就要动真情。
妇女主任说,我真同情你们!
米副说,同情归同情,但你和他们要有距离。不然,还会发生像我们今天这事情。
妇女主任说,米副,我能不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很私人的事情。
米副说,你认为可以说的你就说。
妇女主任说,我来乡政府这么些日子了,从来没有跟谁说过。
米副说,不可以说的你就千万别说。
妇女主任说,你是被刚才的事情吓怕了?
米副说,是啊!我为什么就那样对你非礼了?
妇女主任笑了笑说,我说过,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米副,那我把这件私事说出来,你不要不好受啊!
米副说,你能不说吗?
妇女主任说,还是说出来好。说出来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米副说,既然这样,你就说嘛!
妇女主任说,其实我有男朋友了。
米副挨了一瓢冰水,从头顶一直冷到脚底。他慢慢站起来说,主任,我们赶路吧。他本想问问她的男朋友在哪儿干什么,但他不敢问,不想问,问出一个具体的人来,他觉得不好,为什么不好,他想不清。
但妇女主任继续说,我男朋友在市里的一个科研所工作,刚提了副处长。
米副不知道自己的脚腕为什么突然软了一下,一个趔趄扑到路下,一棵三月泡刺树刮伤了他的颈脖子,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印。幸好有一棵栎树让他撑住了。米副从路坎下爬上来,说,主任,你不是吓我吧?
妇女主任这时才非常认真地说,真的,我不骗你,也不是吓你!
米副说,你怎么不早说呢?
妇女主任说,为什么要早说呢?难道我一到乡政府就应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我有男朋友?宣布我的男朋友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我神经有问题了吗?
米副说,可是……可是,你来这么久了,也应该知道我们乡干部婚姻现状,你像一块肥美的猪肉挂在墙上,二十多只饿猫都在围着你打转,都想吃到你。
妇女主任说,可是,他们吃不到。你一个当副书记的都吃不到,他们谁还能吃到?我有办法对付任何突发情况。任何一个饥饿的男人向我扑来,我都只要在他身上点一下穴位,就会像冰水一样泼得他全身颤栗。我有我妈教的这绝招!
米副在内心里佩服了妇女主任的复杂、善良、智慧、冷静和深邃。米副渐渐地和她拉开了距离,她虽然仍是那样令他爱慕,但不再是此前的亲爱。米副说,主任,感谢你今天原谅我的无礼,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感谢你告诉我你有男朋友。正如你说的,这对我对你都有好处。你会幸福的,我要保护你的幸福!我会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乡政府那一帮馋猫。我要让他们在你面前退避三舍。
妇女主任说,为什么要那样呢?我请你不要说这些!一定不要!你要说这些,不就等于拿这个来吓唬他们吗?我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还可怜得不够吗?只要不跟他们发生那种关系,我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些快乐?
米副说,我们都该好好尊重你才是!你不会在这里待得很久。
妇女主任说,米副,你是一个当领导的好料子。你也不会在乡里待得很久。
米副说,我要是经济条件好一些,早就进城了。
妇女主任说,进城真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米副说,我们不说这个好吗?这个令人头痛。
妇女主任说,好,我们谈别的。谈什么呢?
米副实在不想再谈及妇女主任的婚姻问题,但又还是问妇女主任,你和你男朋友谈多久了?
妇女主任笑了一下,还是离不开要谈这事。她说,两年。
米副说,那么,那么是你在读大学时谈上的?
妇女主任说,是的。最后一年谈上的。他还在经济上帮助过我。
米副说,你们一定很谈得来吧?
妇女主任说,是的,很谈得来。他很有学识,也不迂腐。
米副一下子自惭形秽起来,但又给自己鼓足勇气说,什么时候能喝到你们的喜酒啊?
妇女主任说,今年你就可能喝到。
米副有些不甘情愿地说,那太好了。到时候我要好好敬你们一杯,祝你们美满幸福!米副说这话时,一股酸楚就像烈马跑遍了全身,把他的心蒂都踏得发痛。
自这次下村后,乡里干部发现米副和妇女主任的来往不大随便了,说话也有些躲躲闪闪。世上的逻辑是假事不怕别人说,真事就要避着别人了。仅是这样,大家也还不敢断定,现在是,如果这些馋猫调笑妇女主任,或者是跟妇女主任动手动脚,米副还要血红着双眼,恶狠狠地骂人,又总是不骂出个理由来。但是,妇女主任对这帮馋猫们还是很好,照常和他们开玩笑,照常和他们打打闹闹。这就让这帮馋猫们挨了米副更多的责骂。馋猫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米副这些日子不穿西服了,他本是最爱穿西服的;他现在穿的衣服都是高衣领,还一直把扣子扣得很紧。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啊!肯定有文章。饺子说,哪天我们想个法子,让米副把衣扣解开看看,如果他颈脖上有指印,那肯定就是那天他和妇女主任下乡在路上有事了。饺子长得也像个饺子,中间大两头小,没点儿看相,但他肚里肉馅儿多,是这帮馋猫里的鬼主意窟。两头尖,能通天!
长臂猴说,哪天我们干一场篮球,看他衣扣解不解!在这帮馋猫中,长臂猴有点异相,双手可以过膝,所以大家叫他长臂猴。水桶说,打什么篮球啊,为屁大个事儿跑得裤裆里流臭汗,得不偿失。水桶真长得肥头大耳,腰身脚腿都壮实,所以他最怕上球场流汗,他喜欢洗澡,一到夏天的夜晚,他就到溪里陪伴月亮,一直要把左边的月亮洗到右边去,他才回乡政府来。他说,天气热起来了,我们哪天把米副邀到溪里去洗澡,让他脱光,看他身上到底有个什么伤。毛子,石头,杨桃他们一帮人都跟在后面哄。他们都是农技员,经管员,文化辅导员,计生干部,团委书记,宣传干事,秘书等等。如果米副在,他是副书记,自然在这个馋猫队伍里,米副就是头儿;如果米副不在,水桶就是头,因为,水桶平日里坐的是第二把交椅。饺子和长臂猴是参谋。
后来还是按水桶的计划进行。蝉的叫声越来越长了,天边的火烧云也让溪水暖和起来。那天,这帮馋猫们相邀去溪里洗澡。他们怕米副不肯脱衣裤,水桶就站在溪滩上施口令说,今天,我们大家是新一年头次下溪洗澡,我叫一二三,大家就开始脱衣裤,脱在最后的,就到水里憋三分钟不许抬头!大家说,好不好?这本是他们安排好的,除了米副不知道内情外,其他人谁都明白。大家齐呼一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