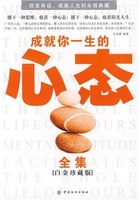梁平很清楚,真正作怪的是庞居士和净心。他接管《莲灯》等于断了庞居士的一条财路,庞居士先前虚报的那些开支,除了回扣都进了自己的腰包。幻空哪里晓得这些,只是一味相信庞居士,因为庞居士是他信奉和宣扬的果报教义的一个活证据。庞居士要照自己的所作所为给梁平抹黑,幻空丝毫不会怀疑。至于净心,则从一开始就把陈时雨和梁平看作了对头,看作了对自己权力的侵犯。
“这种地方你早就不该来。什么玩意!”
欧阳说。
“我哪晓得那迂子活到这把年纪了还跟先前一样迂腐。亏他还枉写了那么多什么教程、什么法语大观,居然敢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我看他比吃糠秕的还蠢。”
梁平真是气疯了。
在接引殿危机中第一个冒头的是陈时雨。
建接引殿的那个山头比设计要求多削了十几米,这样一来,如果接引殿按原设计施工,高度也就随着低了十几米,原来想象的夕阳落到后面起伏的山脊线上时,从山脚下的头道山门仰望,接引殿正好贴在夕阳的浑圆中间的景象,就不可能出现,除非把接引殿再加高十几米。
陈时雨解释说是他计算上的失误,他说话的样子很痛心,却不过是轻描淡写。
幻空站在一片翻出新土的场子边上发呆,脸色惨白,抡着念珠的手抖得“簌簌”响。他身边的净心斜了眼睛看着陈时雨,几乎要动粗。他早就提醒过幻空,应该多找几个更高级的单位和专家参与审阅接引殿的设计和工程招标,不能只信陈时雨一个人。幻空没有听。净心对陈时雨本能的排斥他是感觉得到的。接引殿说是“殿”,不过就是一个单体的小建筑,犯不着兴师动众。至于工程招标,事先就知道了是个形式,中标的是当地县委书记外甥的建筑公司,即便不是陈时雨主持,也是这个结果。净心只好缄口。过后他又知道,陈时雨跟那个县委书记的外甥私下是有交易的,挖空心思要增加工程投资,也就增加了利润和回扣。现在暴露的就是最初的一个事实。陈时雨说的“失误”,根本就是预谋的:土方量的增加和设计的改变,成倍地超出了工程的预算。
“时雨,你可以负我,不可以负佛啊。”
事到如今,净心的进言一一证实,幻空后悔莫及。
“你什么意思,你真的相信我是故意坑你吗?”
陈时雨向幻空叫屈,眼睛却恶狠狠地盯着净心。
净心也迎着他朝前迈了一步。
幻空伸出那只抓着念珠抖抖索索的手拦住净心,对陈时雨说:
“你去吧。”
“莫忘记我救过你的命。”
陈时雨叫起来。
“我如今也是救你。”
幻空仰面看着远处。
那时夕阳正在下山,余晖无力地照着这个被削平的小山头,近夜的风吹过满山遍野的树林,扬起僧人们宽袖长摆的海青。
接引殿还没有升起,就似乎已经沉落在一个陷坑里了。
最失败的还是陈时雨自己。他的日子好像就是由一连串失败组成的。大学毕业前,他独自跑去特区,找了几个单位,最好的一个是让他毕业后先来守两年电话。又找了许多关系想留省里,也没有留成。本来就很勉强的女朋友趁机把他甩了。后来分到市里,结了婚,生了儿子,老婆下岗后开了一家小店,事实上说不上什么小康人家,他却非要当中产阶级,买车养车的,穷装门面。总算在幻空这里得到一个可靠的兼职,却又让小聪明坏了事。他老是算计,老是异想天开,结果老是出丑。
他那天晚上开车把范勤勤带到县城,住进宾馆,他讪笑着进了范勤勤的房间。范勤勤很大方,他关门,坐到她的床上,她都没什么反应。他的胆子就壮起来,对坐在椅子上的范勤勤说,你不能坐到床上来吗?见范勤勤笑而不答,又说,你不能离我近一点吗?范勤勤忽然爆发出大笑,说:你觉得你对自己有信心吗?范勤勤没心没肺的笑声让房子都好像摇起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屁滚尿流夺门而出。
“我操,我还真没有信心。”
事后陈时雨悻悻地对人说。
比较起来,梁平对范勤勤的直觉就准确得多。
对莲灯寺来说,比陈时雨造成的损失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范勤勤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一则短文,质疑市长老婆给莲灯寺的几次共计上百万元的捐款。她天晓得从哪里不但知道了捐款的数额,还知道了市长老婆又要捐款又怕人知道,由此认定是因为其心机和来路都不便公开。并且声明,这件事她会像蚂蟥一样叮住不放。
范勤勤的文字真的就像蚂蟥一样刁钻而狠毒,字字见血,而且见肉就钻,连菩萨也不放过。短文的最后是凌厉的质问:
而今官场贪污公行,社会腐败成风,类似市长老婆这种人和事不足为奇。但寺庙若只顾敛财,并不问心机和来路,就是修起了接引殿,供起了接引大佛,又怎么能接引往生者去极乐世界?一个人生前造下恶孽,靠不法不义之财买死后的极乐,接引大佛若能遂其所愿,岂不是接受贿赂,成了同谋?如果接引大佛也是可以贿赂的,那他许诺的极乐世界不同样就是现世的花花世界,还有虔心追求的必要吗?
范勤勤当然不是只满足于在博客上发议论。传闻中的那个对市长穷追不舍、举报不休的人就是她父亲。关于他们与市长之间的恩恩怨怨有许多说法,其中包括范勤勤母亲不甘市长的欺骗和市长老婆的侮辱而自杀,有人曾经看见市长家里有个地方一直供着她的照片。总之公也罢私也罢,横直他们是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把市长扳到就是了。
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首先是范勤勤的父亲多年来积郁成疾,早已瘫痪在床。范勤勤的博客文章出来后不久,市电视台不止一个人收到了来路不明的信件,里面是一大叠范勤勤的裸体照片。
范勤勤不得已公开了她在这之前被绑架的事实,本来她咬紧了牙关在等着水落石出:
有天她下夜班回家,忽然被人蒙了头拖上尾追上来的汽车。天亮前被推在一个山沟里,等她扯下蒙头,那辆车已经绝尘而去。
绑架者先是用药物使她昏迷,然后把她剥光,再摆布出种种放荡的姿态拍照。他们唯一的不足是没有一张范勤勤清醒状态下表情正常的照片;另外还有一个不足是他们的过度聪明造成的--整个绑架过程没有更进一步的强暴行为。这至少证明了两点:一,主使者对事件的绝对控制;二,他们的目的只在警告要挟,不想过度强化罪行,避免复杂化。这恰恰排除了这次绑架的非偶然性。
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舆论大哗,上上下下的有关方面已经无法坐视不问,正式的专案调查终于展开。
市长老婆对莲灯寺的捐赠自然是调查的要点之一。但专案人员下来之前,掌握莲灯寺财政的核心人物净心却忽然蒸发了。用他个人名义在省城银行立户的捐资存款户头上只剩下了区区几十元,其他数百万巨款早已通过多次现款提取和一再转账而不知去向。一切原是有过精心准备的。可怜幻空连小小的念珠手镯都亲自保管着,却把一座寺庙的命脉交给了一个道貌岸然的骗子。
有关的调查暂时搁浅。但市长夫妇并没有因此轻松,他们面临了天谴。
市长的胃癌恶性发作,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最后的那一刻,情形有些让人不忍,他紧抓着妻子的手怎么也不肯松开,充满了乞求和绝望的眼睛怎么也不肯闭上。
而他们曾经是那样诚惶诚恐地相信和指望过菩萨的接引。
莲灯寺接引殿奠基的那天晚上范勤勤请教幻空的所有有关修行的问题,其实都是市长老婆问过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阿弥陀佛在接引往生者时,必会以祥光加持他,使他一心不乱,欣然如归,从而获得更为殊胜的往生果报。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临终时还是会害怕而不敢随佛接引往生佛国?
幻空回答:这是因为是他对这世间依旧心怀贪恋,也就是常人所说的贪生怕死。他以为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死亡,故而临终时就心慌意乱,不能保持专一的正念,不能感得阿弥陀佛对他往生佛国的接引。凡念佛者一定要深明此理:不贪生怕死,不贪恋名闻利养,要具备发自内心的真信切愿,方能与佛感应道交而得到究竟圆满的快乐。自来高贤,悉皆蒙佛接引。如果平时只是表面上做求生功德,而没有发自内心的信念,大限来临时就难免业障现前,恐怖惊惧,因而错过佛来接引安养佛国的机会,以至于堕落恶道。
那时候幻空未必知道,他这番话真的会应验在他的大施主身上。而范勤勤当时重复市长老婆的问题,多少有一点调侃、有一点恶作剧。
所有这些消息,都是欧阳带来的。他为给莲灯寺做的那几个高立柱广告催款先后跑了好几趟。幻空每次都再三请求谅解,竭尽努力分了好几次才还清了全部费用。
莲灯寺存在县银行的捐资一开始就被县政府不断挪作他用,说是借,还却难。净心把存在省城银行的捐资大部卷走,莲灯寺财政一时告急。已经开工的那些工程的民工唯恐到时拿不到工钱,天天拿着登了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文件的报纸围住幻空,逼他按天付钱。幸好县内外、省内外乃至海内外善男信女的捐款多多少少总在继续进账,分解了幻空的燃眉之急。
让梁平刮目相看的是幻空。原以为他嬴弱单薄,不堪大任,想不到面临这么大的劫难他会如此镇定。在当年的一个佛七法会讲开示的时候,针对莲灯寺现状,他一字不漏地引用了弘一法师李叔同《律学要略》中的一段话:
“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以为中国僧众很多,大有达致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找出一个真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
一个人怀了这样沉痛的清醒,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单是这份悲壮和执着就足够动人。
梁平的手上,当时正拿着刚印好的莲灯寺彩色单页的《接引殿疏》,他离开莲灯寺前定稿付印,这是他为幻空做的最后一件事。成品出来,他让省城承印的那家印刷厂直接用车给莲灯寺送去,自己则不肯再见幻空。幻空好几次托欧阳转达他的歉意,梁平不作回应。他对幻空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心里却不由生出几分敬意。幻空自己起草和定稿的《接引殿疏》上这样讲到所谓“佛心”
……观经云:“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
梁平想,这段话,用于幻空,也颇适当。
原文载于《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