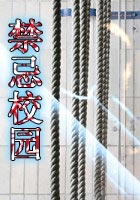当即雇了两辆人力车,子和与如静乘一辆,玉珠带小乃乘一辆,直奔听音寺。留秉奎看家。
山腰上有一道残垣,依稀可见几个石灰水刷的字:照明佛法,开悟众生。
从未油漆过的院门仅剩一半,院子里有两株老态龙钟的罗汉松。铺地的青砖缝里,青草袅娜。正殿不大,低矮晦暗,有案有炉,只是巳蒙尘。
四处弥漫着一股积年深久的音响,似有若无。哪有什么香火,哪有什么菩萨,哪有什么真身。人呢?小乃拽着爸爸的衣袖,再不肯到悠深的背后去。跨门槛时,没当心绊了一跤。
太阳疏疏朗朗地照过来,又被一株肥壮的阔叶树挡回一多半。退了出来,如静抱怨,事先也不问清楚,白跑这么远了。子和说,听信了瞎子的。如静说,瞎子的瞎话如何信得。玉珠说,这山却静得好。子和说,没料得还有这许多大树。
既然来了,子和想到林子里去转一转,寻一寻,没准还能寻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来。玉珠的眼里也有这种意思。
如静却没兴味,要走。小乃愿随妈妈回去,说这里连个小店子也没有。小乃想吃东西。
于是留下一辆人力车给子和与玉珠。
下山前,如静盯着玉珠道,好生照顾先生。她把先生两个字咬得格外重。
玉珠眼里,有倏然的一暗。
八月天气,日头辣辣的,子和带着玉珠,专寻人迹不至的浓阴处走。
玉珠穿一件暗红短褂,早已沁汗。她说,没料得先生竟会爬山。
子和说,他喜欢山胜过喜欢水,因为山比水丰富。在杭州,他对西湖无甚兴趣,倒是玉皇山登得多。
他说,如静喜欢水,她会游泳。这一点上,我同她老不合拍。玉珠问,那平日出去玩,谁听谁的?子和一笑,先玩水再登山呗。
到底是你先让了她。玉珠低了眉道,我也是喜欢山的,从小在山上打柴。
子和没介意她的神情,说,你是能吃苦的,不接触不容易看出来的。
藤梨!玉珠忽然叫道。一根长藤,四处婉蜓,挂满硬实的果子。子和摘下一枚看看说,什么藤梨,是猕猴桃。玉珠说,我们这里就是叫藤梨的嘛。还是生涩的。子和说,要到秋后才好摘。玉珠说,那时候,只怕早被人摘光了。过一阵子街上就有卖的,用竹筒子量,一毛钱一竹筒。
他说,这地方不会有人来的,等熟透了我们来摘。她说,怎么不会有人来,我们不是来了么。他回过头来,发现她回避的目光有些慌乱,不由有些心动道,我们来的地方,别人未必会来。话一出口,蓦然有些脸热。她却大方道,下次一定再来嗬。
下山来时,人力车已经不见了。想必是等得不耐烦,转身去了。
只好步行回家。又累又饿,回到家里两人均已疲惫。子和告诉如静没乘车。如静说,就那点路,也不必走到现在。子和说,下山晚了。如静说,就那么一座小山,那样好玩!
见她一副猜疑,玉珠心里好没意思,道,是我走得不快,连累了先生。
不知怎的,玉珠鼻腔里有些发酸,顿时到厨房去了。子和愠恼道,你耍什么态度!见他生气,如静不再吭声了。
日后,子和发现她虽不明言,却有一些防备。比如玉珠在同他说话时,如静总要找个机会蹭过来,要么就把玉珠叫过去做事。
这一来,子和与玉珠的接触,彼此都生出越抢,那尴尬又不免生出一种别样的情愫。这情愫在子和暌违已久,重新品味便感受到一份温馨、一份激动。
子和是有身份的人,子和当然需要克制。但那一段时间,无论看什么书,子和总有一点意乱神迷。
那日,玉珠说她父亲五十寿辰,买了一只寿饼、几样糕点,回家去了。
原本说第二天就回来的,一连三天都不见她回来的。如静说,这样的人,原来是不守信的!子和说,大概是家里有事呢。子和到底有些不放心,第四天,骑车寻到她家去。很破败的一片住宅。见先生来了,玉珠不好意思,赶紧收拾东西,揩了椅子请他坐。
玉珠的父亲受疾病折磨,看上去比五十衰老许多。这些日咳喘得厉害,玉珠所以没及时过去。
她父亲强打精神坐起,执着子和的手说,我玉珠回来,总讲你的好。以前呢,我对她出去做事,总有点不放心。现在没有她那几个钱,还真不行。玉珠遇着了善人。她年纪小,不大醒事理的,先生要多原谅。
子和说,玉珠是很懂事的。她父亲要留先生吃饭。玉珠却说,他家里还有事呢。父亲就骂她不懂事。子和就说,还要赶去上课的。
玉珠送他出门,默在路边,说了句,不留你,你不要怪我。子和揣度着她那层心思,说,怪你什么呢!骑了很远,子和发现她还默立在那里。
连着几个月的薪金扣欠,学校里更加人心浮动,巳陆续走了几个教师。
校长把子和视作知己,也知道他家中殷实,同他谈话,希望他眼光放远,切不要有其他想法,因他的举动,在同事中还是有影响的。
只要学校不散,子和暂时不会有择枝另栖的念头。故里已经沦陷,子和连去两封电报,没有回音。母亲的安危康健以及家产的祸福得失,都是他日夜萦系于怀的。路途不太平,往来都无可能。
那日闲极无事,细致削了五十根竹签,用《易经》箅卦,得到的是咸卦:
亨,利贞:取女吉。
看着这卦辞,子和不禁哑然失笑。一旁观看的玉珠敏感,追问这卦辞的意思。
子和说,这一卦,下卦“艮”是少男,上卦“兑”是少女:象征少男虔诚追求少女。“咸”是感的意思,阴阳相互感应而相爱,所以亨通,坚贞有利,娶妇吉祥。
玉珠说,先生不是早已娶了师母么,怎么还会得到这样的卦呢?
玉珠欲言又止:会不会是……
面颊已沁出一抹红来。
门边已站着如静,叫玉珠去淘米做饭。
玉珠低着头,从她身边走过。
如静走到子和身边道,你们在干些什么?
子和无心,收拾着竹签说,算卦呢,明明是给我母亲问安危的,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卦,你说怪不怪?
如静拿起那本翻卷着的《伊川易传》,看了片刻,眉头立刻浓浓蹙起。
子和来到窗前,将一握竹签全部抛撒窗外,苍然对天发问,娘啊,你到底怎么样了?天际莽然无光,无言。子和泪水夺目而出。
一个月过去了,家中仍无讯息。
这夜,如静对子和说,家中接济巳断,物价已见上涨,细水方能长流,必须将雇工辞掉。
听她语气,不像是突然的决断。子和一愣,片刻才知道,怎么辞,秉奎可是从家里带出来的!
如静马上接言,那就留秉奎好了,厨房里的事我能做。子和心下又是一愣,这么说只能辞玉珠了。子和婉言,玉珠在我们家做得不错,小乃也喜欢她。再讲,她家正是困难,这时候辞她,总有点开不了口。
如静说,我对她印象也还好,不过,当家才知柴米贵,我不能不做钱财上的算计。若是你拉不下这个脸,由我来跟她说好了,我知道你是面皮薄的。
听她语含机锋,子和觉得多说无趣,反倒让她多了猜疑。只是想到玉珠从此离开了这个家,不由得怅触难已,一夜不得安眠。
第二日结束,子和思忖着不能让玉珠太感突然。于是趁如静出门的那阵,把玉珠叫到里屋,把如静的意思透露给她。玉珠望着子和,一张脸顿时刹白。
那一刻,子和心里很不好受,说,我再跟她谈谈,缓一缓再说,你别难过。
默了片刻,玉珠说,师母有这样的意思,先生你也别和她矛盾。想想又道,师母的心里,未必是为钱财算计的,这先生你也应该知道。
一对黑眸里,已然有怎样难言的情愫。子和心里,陡然涌出无边的怜爱,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玉珠道,先生你别为难,一切由我来处置好了。她好像下了某种决心似的。
一连几日,如静没提辞玉珠的事。这日星期六,玉珠说,想回家看看。如静把她叫住了,叫她坐,然后又给她沏了杯茶,这才绕着弯子提出了辞退的事。如静除了多给她结算一些工钱之外,还送了两块布给她。
玉珠没接东西,站起来说,我和秉奎已打算中秋结婚。在秉奎没找到职业以前,我想只能在你们家继续呆着。如静和子和都愣住了。
玉珠当即唤秉查。秉奎进来了,一副手足无措。玉珠站到秉奎身边说,工钱呢,由你们给好了,给一份也行。好一阵,如静问秉奎,你看呢?秉奎说,我听她的。一脸喜悦。
玉珠结婚前一星期,子和才接到家兄来信,说母亲六月初八已去世,人一下子就倒了,后来分析可能是中风。看看发信日期,不知在哪耽搁了一个多月!
婚礼自然简单。子和与如静送了几样家具给他们。他俩在不远处租了一间房子。
玉珠很快就怀孕了。她跟如静说,原本不想这么早要孩子的,但是没法子防,秉奎把蛮。
两人仍在子和家做事,吃也在,只晚上回家,那是他俩的家。子和后来跟如静说,秉奎其实配不上玉珠。如静说,半斤八两,你说他配不上她,谁好配她着?子和无言。
学校即南迁,与另一分校合并。思想到这次再不可能将玉珠与秉奎带走,子和及时给玉珠请了一个裁缝师傅,为的让她日后有门饭吃。秉奎这时也在外头做些泥瓦活。
这日,玉珠独自在案台边锁扣眼,子和在一旁看着,有心逗她乐一乐,便说,解缙有次看一女子身上用了九重纽扣,当即做诗戏谑道:一副绫绡剪素罗,美人体态胜桓娥,春心若肯牢关锁,纽扣何须用许多。
玉珠默然无声,片刻抬起头来,但见泪水承睫。子和一时也有些动情,赶紧避开了。
临分手,给什么玉珠都不要,她只要了子和案头那块刻着龙凤呈祥的铜镇纸。
迁到广西以后半年,子和接到玉珠一封信,说阴历九月初九子时生了个儿,请先生起个学名。
子和思谋半天,写了两个字:承汝。意即应有母亲的继承。子和一直觉得,玉珠这女子的禀赋很不一般,只可惜生不逢时。
以后是二十年的音信杳然。学校早已回迁,子和已是这东南形胜之地的知名学者。
1960年5月这天傍晚,子和正在家里喝一碗羹汤,门被急遽敲开,一个身材虽大,形容却瘦的后生站在他面前,身上一只布袋又脏又破。
我叫承汝,我从贵州来。说着他掏出了那块龙凤呈祥的铜镇纸。
子和仔细盯了他看。半天才问,你爸你妈,还好?承汝说,我爸前年给公家砌食堂,从屋上摔下来摔死了。我妈一身病,却也经拖。
承汝吃饭时,一副狼吞虎咽。他后来打着饱嗝说,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饭了。他说他们那里现在什么都吃,不包括观音土。
子和搜寻有些地位的学生,给承汝找了份事做。承汝很自在,乐不思蜀。
子和念他母亲病弱,数次催他回家看看,他一拖再拖,直到拿了子和给买好的车票,这才动身。带了一笔钱、一袋米。上车以后,承汝眼巴巴地说,我马上就回来。果然到家打个转,他就回来了。子和问他母亲近况如何,他说很好很好。那日吃饭,已经大学毕业的小乃问承汝,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承汝说,我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我妈讲我最像一个人。像谁?
承汝看着小乃父亲,有点得意道,还看不出来么?小乃一愣道,果然很像我爸爸!承汝笑道,你爸爸未必不是我爸爸!
一旁,已然病态的如静顿时脸色发青,一双眼愤怒地看着子和说,我看他也十分像你,难怪!连名字也是你给的么!
子和一惊之后,怒不可遏对承汝道,你在胡说什么!当即给了承汝响亮一巴掌。
承汝捂着脸,委屈地退一旁说,又不是我说的,是我妈说的。子和心气难平,拽了承汝要去贵州找玉珠。承汝不肯去,他说他死也要死在这里。
第二天,子和带几分温恼,匆匆去贵州。不到半月返回。如静见他疲倦、消瘦,默默为他炒了几样他爱吃的菜。是夜,两人躺在床上,月色清朗,子和两眼凝视窗外。如静轻轻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默然良久,子和收回目光,慢慢地说,权当我们曾生过这个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