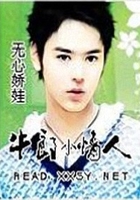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一大早,安委会主席拉贝就早早起来了,事实上,他一晚都辗转反侧、不曾睡好。尽管昨晚他就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刮净了胡须。早晨起床,他还是再用一柄圆圆的胡须刷涂了满唇肥皂,快速而又细致地用德国带来的刀片刮了一遍。他穿上头天佣人熨烫得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左臂上戴着一只印有醒目纳粹标志的袖章,用一柄黑色的密齿梳子篦篦头顶,抿抿鬓角。他的佣人懂点英文,但是不懂德语。那天,她给他扣上呢子礼帽的时候用中文道,你身体挺好,就是头发早谢了。
1882年出生的拉贝,今年整55岁。从1911年到中国,他都二十五六年了。他当时摸摸头顶,茫然问道:什么是早谢?
佣人连讲几句都没表达清楚,拉贝说,你是讲我早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想早泄也泄不了了!顿时把佣人闹了大红脸,拉贝却哈哈大笑着到他的西门子洋行上班去了。拉贝是一个平时很喜欢开玩笑的人。今天要去迎接日本人进城,他想,要是日本人不一本正经,喜欢开开玩笑,事情就好办了。他接过佣人递上来的印有安全区徽章的小旗子,微微一笑道,这个顶重要,没有这个东西,我哪里敢上街。佣人说,你还有这个呀。指指他的纳粹袖章。拉贝不仅是纳粹党党员,而且从1931年起,担任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佣人的提醒,使他顿时觉得自己遏制日本人进城之后胡来的底气更足了。
下得楼来,委员们早在此等候了,包括比他小四岁的美国老朋友魏特琳,两人对视微笑。魏特琳身边是安委会的副总干事费奇,后面是史迈士、贝茨、威尔逊、汉森、梅奇、史密斯、李格斯、希尔兹……一一握手之后,一行透迤而肃穆地来到大街上。
他们刚来到汉中路,冷风呼啸,加上心理上的畏惧,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苍白的。四顾之中,一支日本军队已经过来了。拉贝率先摇起了小旗子,其他委员也赶紧挥动手里的小旗子。拉贝举起双手,第一个迎上去,用英文问好。日军有点好奇,既对这个古城的风景好奇,更对战乱之中,有这么二三十个金发碧眼、高矮胖瘦的西方人站在寒风呼啸的大街上好奇。
一个日本人忽然发现了拉贝袖章上的纳粹标志,惊呼,啊,啊,纳粹!
拉贝微笑着伸展胳臂,为的是让他们看得更清楚。
大概是一个少佐过来了,翻译紧随其后。少佐拿出地图,费奇趋前指点安全区的方位,并清晰地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在战乱地区成立国际安全区,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另一个意思是,安全区很好辨认,区内的每一条路口,都插了红十字旗作为识别。
少佐一挥手道,放心吧。
费奇退下后,不无忧虑地对拉贝说,他们的地图没有安全区的标志。
拉贝立即上去,热情洋溢道,你们渴了,我们可以送热水过来。安全区里全是良民,可能有一些军人,也脱下了军装,放下了武器。
少佐顿时行紧了眉头,道,军人是不可以的,要出来,统统地登记!
魏特琳说,战争受害最深的就是妇女,现在很多妇女都在安全区里,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惊吓她们,她们都是孩子的妈妈,或者,妈妈的孩子。
少佐笑道,孩子的妈妈,妈妈的孩子。妇女不是军人,我们不动妇女。
拉贝强调,我们既希望不伤害妇女儿童,也不伤害放下武器的军人。带有武器的军人都走了,一个都不在南京了。
少佐点头,都走了,都被皇军打跑了,是不是?
拉贝有些馗她道,是的,都跑了,他们打不过你们。
少佐举起了拳头道,皇军是不可以战胜的,谁要是敢反抗皇军,格杀勿论!他说着做了一个劈刀的动作。但是,只要听话,乖乖的,做良民,皇军不但不会打他们,还会奖赏他们,懂吗?你们要告诉他们,统统做良民才好。
拉贝等一起点头道,知道的,知道的,都是良民。很快的,拉贝就发现,日军进驻之后的表现,和少佐的允诺判如云泥。
当少佐在汉中路口与拉贝一行西洋人周旋的时候,池岗大佐乘着一辆军用吉普在谨慎地巡视。路过汉中路的时候,他的车并没有停下来,他不想和这些一天到晚想缠着他们提条件、讲道理的西洋人交谈。战争就是战争,他不想也没办法做出何种承诺。心底倒是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在蒸腾,他想见见慧敏,多年未见了,他想象不出慧敏剃度出家、身披袈裟,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车过一家工厂,烟囱早已熄火,只有一只瘦猫在围墙上惊惶地张望。池岗伸出左手,车子戛然停在颓败的大门口,他刚推开车门,一只脚才落地,忽然从斜前方射出几发子弹,激溅在车门上。池岗被部下搡了一把,迅速收脚关门,叫道,有残军!
很快地后面赶来了一支小队,以吉普为依托,四下扫射、投弹。
轰响过后,一片死寂。
池岗再度下车,发现墙根和大街上已经有几具尸体,那只瘦猫却不知窜到哪里去了。他朝工厂竖起一根手指,士兵们立刻踹开虚掩的大门,又是无目标地一顿扫射。池岗发现那只瘦猫未来得及逃跑,血肉模糊地躺在墙根下。
池岗记得在士官学校,老师说过,战争的定律就是这样,要么进攻,要么逃跑,既不能进攻,也跑不了的,就是死路。而皇军的词典里,只有进攻,没有逃跑二字。这条定律在中国领土上得到验证了,逃跑的是中国军人。不能逃跑的老百姓和猫一样,难有活路。因为军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识别,无辜遭戮,那就不可避免。进城之后,他原以为会有的近距离巷战,并没有发生,刚才这样的冷枪,他进驻后是第一次碰到。
池岗相信,中国军队大多数已经渡江逃跑,散兵游勇如刚才在暗处打冷枪的,不足为惧。话不能说过,试想刚才要是下车快了点,或者暗射者更沉着一点,他那在家日日茹素念经为他乞求平安的奶奶,收到的就只有他的一帧遗照了。奶奶知道他到了中国,托信见见慧敏那姑娘,奶奶对慧敏是一百个中意。池岗为奶奶这辈子可能娶不上这么好的孙媳妇惭愧,奶奶从小对他的爱,真是历历在目啊!他的皮夹子里,就有一张全家福,还有一张和慧敏的合影。慧敏站在路边的石头上,一只胳臂压着他的右肩,显得比他还高出半个头,一脸灿烂的笑容,任何一个男子怕也过目难忘啊。这么好的女子,怎么说出家就出家了呢!
池岗决定,次日找个理由,去栖霞寺拜会法师。第二天,阴霾如晦。池岗刚吃罢早点,少佐就来电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地告诉他,发现了大批中国士兵。池岗心头一紧,忙问,在哪里?他们手里还有武器吗!
少佐说,在城北的幕府山附近的一个学堂操场上,全都缴械投降了。
池岗立刻喝了碗里的汤饭,驱车前往。往东十来公里车行半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学堂,主楼是哥特式的尖顶,猜想原本是一个教会学堂,条件应该不错,到底是首都。绕过来,到主楼后面的空地,池岗惊住了,黑压压一大片,全是缴械的军人!
这些自行放弃武装的士兵,肯定也有一些下层军官,或站或坐,穿着蓝色棉布军服,又脏又破,臃肿不堪。有的戴着帽子,有的用军毯裹着头以避风寒,还有的是一条麻布口袋随便往脖子里一围。既是害怕,也因冻饿,全都精神颓丧。
少佐一声喝令,数千人一起肃立,原本挂在肩上的五花八门的袋子哗啦啦落地。
池岗抬起头看,两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挂满了白色的饰物。后来检查,这些昭示投降的白色,有白旗子、白床单、白衬衣、白窗帘、白手帕、甶纸,甚至,还有白短裤!天哪,他们想得到,找得出这么多白色的物件在两棵树上开投降展览,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离奇与最壮观的投降展览了!
这么多人后来经少佐组织清点,共七千余人、不说拼死反抗,就是蠢动起来,也是一股洪流啊!池岗眼里掠过一丝深刻的鄙夷。
他走过去,掀开一个孩子模样的盖头,那孩子相的军人本能地退缩。池岗问他今年多大,他怯怯回答道,十四了。池岗重复了一句,十四?还有你一般大的?孩子答道,还有更小的。池岗问,更小的是多大?孩子答,十二三岁吧。
池岗捉住他的手,忽然擎起,检查他的虎口和指头,端枪训练,该有茧子的地方,这孩子手上都没有,遂问,打过枪吗?孩子答,打过一次。
池岗心里骂道,胡闹!
此时,他心里没有同情,只有懊丧,混杂着羞愧与厌恶。说实在,进入中国以来,他们和中国军队遭遇过激烈的枪战乃至可怕的肉搏,但也碰到过闻风而逃的部队;碰到这么一个大军阵,相当他们的军团力量,束手就擒,甚至把能想到和找到的所有白色物件高高系在树上以示投降的,这还是首次。
他们还有这么多人,尽管许多士兵可能是第一次拿枪参战,但人多势众啊,为什么不还击?军人在战场不知有何羞耻,唯一羞耻的是投降。在日本军人的训诫中,就是死战、再死战。如同日本飞行员得到的都是一把剑,而不是降落伞。他们的军官哪里去了?
池岗忽然想到了他的大学中国同窗张晖,这里应该没有张晖的部下,他是不会弃士兵而逃跑的。中国军队里有很多出色的军官,譬如张晖;但却有太多窝囊的士兵。全怪罪士兵也不对,譬如这时他们的头儿呢?
池岗觉得进人中国之后,被扑面而来的许多互相矛盾的问题搅得脑子有点乱。
少佐忽然低声问,我们准备怎么处理这些俘虏呢?
这倒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原本想到的问题,是准备巷战,是大量军人伪装成百姓进行游击战,现在一下子就捡到这么多俘虏,他也想不到怎么办才好。只说,给上面报告吧,看他们的意见如何。
少佐犹疑地看了一眼上峰,响亮地答是。池岗大佐后来知道的消息是,这投降的七千军人,和另外在乌龙山等地投降俘虏的军人一道,全部枪毙了。事先当然不能告之处死他们,一点消息也不能透露,只说将他们转移到战俘集中地看守,这个集中地在江中一个小岛,名八卦洲,他们将在那里获得俘虏待遇,等待处理。
所有俘虏都异常听话地接受搜身与双手反绑,为的是防止逃跑。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绑者和被绑者都疲惫不堪,这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才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军人捆扎完毕,开始沿山丘西边转移。
走了一个多钟点才到大江边的洼地,但却看不到任何渡江工具。有些年纪较大的军人发现了问题,但一切为时巳晚,所有军人都被赶进一个月牙形的口袋地形里。当早巳潜伏的机枪射出第一串子弹之后,所有的机枪都随后吐出了浓烈的火舌。距离太近,天空中立刻下起了稠密的血雨,万千的惨叫就像放开了地狱的大门,撕裂耳鼓。一个小时之后,前面的机枪手艰难地爬起来,他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血人,除了一排惨白的牙齿,头脸与一身军装全被血雨湿透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催使得所有人都勾头呕吐。清尸的过程更令人厌烦。
十几桶煤油浇上去,点燃;火熄灭,才烧了个半熟。一个背部着火的尸体倏然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朝江边走去,他的背部燃起了一朵朵灿烂的梅花。梅花一朵一朵绽放、然后凋谢。尸体扑通一声栽进江河的刹那,梅花见水即跳,一朵朵升腾起来。
烧尸烧到手软的日本军人,惊耗之余获得启发,何不把这么多尸体扔到江里去呢,去喂鱼,江里的鱼吃不了,再顺势流迸大海,喂大海里的鱼。于是他们用卡车运来几车劳工,都是城里的百姓,在刺刀的环侍之中,他们只有卖命地将一具具半焦的尸体运进长江。他们整整运了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有些体弱的劳工,在运送途中就一头栽在江边,再也爬不起来了。
池岗在得晓这么大的屠杀俘虏的事件之时,也有过暗自的心惊。两军交战,不斩使者,也不杀俘虏,这是古今的惯例,而且是这么多的俘虏!他没来由地从挎包里擎出奶奶交给他的一只檀木镇纸,上面是一句良阶的偈语:渠今正是我。奶奶告诉他,此行出去多凶,要常常诵经。
快速而重复地念了十几句南无阿弥陀佛,池岗心中稍稍安定。这时候,他想见慧敏的情绪更强烈了。他知道自己不对,这是在战场,不能有太多悬想;但他克制不住自己的年头。
他万万没料到的是,在那样一个尴尬的场合,见到了久久不曾释念的慧敏。
魏特琳这两天忙坏了,也愁坏了。
金陵女大一下子涌进了几万难民。几万难民的吃喝拉撒病就是大大的问题,更何况她们当中还有因战争及家人遭受杀戮而精神错乱者。更要命的,虽然这里是安全区的范围,日本军人仍然时时进来寻找中国军人,更寻找花姑娘。
按照魏特琳原来的意思,女子学院应该作为妇女的保护地,最多,加上孩子和老人。可是眼下,女人进来了数万,男人也像潮水裹挟的枯枝败叶,涌进来不少。
一个男人激愤地冲魏特琳挥舞拳头,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学堂里头,你叫我到哪里去!要死,我们愿意死在一起。孩子,多大叫孩子?老人,多老叫老人?他的唾沫星子溅到了魏特琳的脸上。
魏特琳没有委屈,只有无奈。他讲得对呀,一步之隔,就可能生离死别。
一些混杂进来的男人,穿着女人的花衣裳,裹着红头巾。那些年轻些的女人,根本不洗脸,头发蓬乱,脏乌道道。这是什么时候,怎么丑怎么好。原来的厕所根本就不够,学院里弥漫着尿騷屎臭,有些妇女当众就解裤子在沟沿里撒屙。
魏特琳更担心的是一些军人,日本人会找到你们的,他们很容易从你们的手看出你们是军人,你们在里头就会殃及其他人的!她眼前是一个头缠布帕的士兵,布帕脏得看不出底色。士兵阳光呆滞地看着这个穿白裙的外国女人,这个学院的代理校长,伸出一双指甲里满是黑垢的手去解头上的布帕。一圈又一圈,结着黑痂的绷带,其实是断断续续地粘连着。士兵把绷带一条条叠放在膝盖上,然后又去脱鞋子,右脚并没有鞋子,用杂布包裹,解开之后,臭气熏天,已经有白生生的蛆虫在伤口进出。魏特琳双眼一闭,忙在胸口划十字。缺医生,缺更缺药品;缺粮食,也缺房屋。魏特琳匆匆转了一圈,赶回办公楼。电话线两天前断了之后又在安委会的幹旋下,接通了。她连拨了几次拉贝的电话,都没有人。忽觉天地旋转,助手赶紧过来扶着她坐下,她示意给她拿药和要一杯热开水。助手说开水没有了,一壶开水早上就拎给外面的几个病人了。她就着凉水吃了两片药。高血压和神经衰弱,这是老毛病;战争与紧张,加重了她的病情。这几天,她没有过一夜的安眠。
她让助手再给拉贝电话,终于通了,正是他。电话里,拉贝也是气喘吁吁的,说一早就出去了,街上一直在杀人,他根本阻挡不了,这里阻止了,那里又举起了刀枪。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当人看,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要赶紧给德国报告啊……拉贝呼吸也急促了。
魏特琳说,你再忙也是主席,我顶不住了,你过来吧,带医生来,带药品来,带粮食。
拉贝说,明天行不行?我的宝贝。拉贝希望缓和她紧张的情绪,这时候,是铁人都会疲软,何况一个日理万千杂务、头上悬着战争利剑的女人。
魏特琳喃喃道,带医生来,带药品来,带粮食来……拉贝不再说话了,道,好的,你等等,我就来。慢慢放下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