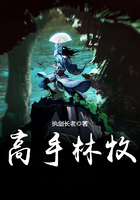她说她没上过庐山,景浩就推迟行期,陪她在山上逛了两天。当他和她那晚躺在一间农民的草屋里时,听着涧水淙淙以及她热情的呢喃,他奇怪自己的心情竟是那样平和安静,他更强烈的感受到:他的激情,巳经非聂枫莫属了。景浩返回学校,已是新历10月了。
聂枫生了一个儿子,刚满月。因是在娘家坐月子,景浩去探望,就觉得方便许多。
屋里有人的时候,他不便说什么,只说孩子很白,肤色和眉眼都像她。她看了他好一阵,说:“你瘦多了。”
待人出去以后,他迅捷地给她一个吻说:“都是因为想你。”她一笑:“恐怕还是因为你的艺术吧!”他说:“我的艺术和你,哪能分得开呢,没有你就没有我的艺术!”
她奶孩子的时候,他感觉得心中的激情在蔓延以至翻腾。他转过脸去问:“你没请个奶娘?”
她说请过一个,但她觉得那人脏兮兮的,于是找了个理由把她辞了。她说,孩子吮吸母乳那一刹那的感觉是很深刻的。但她仍想及时找个奶娘,因为她不能不为自己的体形着想。她想过些时候就外出找点事做,这几个月呆在家里都快闷坏了。他问:“张通宝会让你到外面去做事么?”她鼻子一哧道:“他管不了我。”
他问为什么,她告诉他,张通宝逛窑子,她派人盯了梢,取了证。以后她怕他染病,不乐意与他同床,他就索性以此为理由,频频出入窑子。现在他已转业到警察局,职务好像还高了些。
她说:“我早就以生孩子为由住回来了,他也不闻不问,生了孩子以后他倒是几乎每天都来。”
正说着话,张通宝一身警服回来了,他上下看看聂枫,又上下看看景浩,开玩笑似地说:“哦,是聂枫的小情人来了,我说聂枫今日的精神怎么特别好呢。”
话刚说完,聂枫冷不防将一杯残剩的牛奶朝他脸上泼去,骂道:“畜生,你给我出去”
张通宝发作不得,悻悻道:“我,我走,你不要后悔,臭婊子!”
聂枫的父母闻声过来了,既说聂枫,又责张通宝,更用嫌怨的目光,看着景浩。
景浩面子上下不来,扭头走了。
回到家里,天平和张倩已经做好了午饭,正在等着他。张倩随景浩返城以后,天平领着她东奔西跑找事做,很偶然的机会,听报馆老板说一个英国人想找个家庭音乐教师,前去应聘,那英国人很满意,薪水定得高,张倩意外得之,满心欢喜。
景浩情绪低落,天平当然看得出来,待张倩出门以后,天平就问:“是不是在她家受了气?”
景浩把那边一幕,大略说了,愤愤道:“张通宝当面羞辱我倒没什么,看见聂枫心中不痛快,我又爱莫能助,心中就难得安宁。”天平说:“我看你对她很痴迷了。”景浩痛快地点头。
天平说:“张倩对你有心,你未尝看不出来吧,若是把她与聂枫做个比较,除了出身不及聂枫,其他未必不如她!”
景浩说:“我在张倩面前,与在你面前一样,没有激情。”天平扑哧一笑说:“怎么会呢!无论怎么说,聂枫总是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呀,起码在这一点上,她没法同一个姑娘相比。”
景浩连连摇头:“这是皮相之见,老弟,以我这段时间的经验和感受,确实有这么一种女人,她能以她内在的天然潜质,给你一种永恒的激情和激励……我觉得我已经不能没有她了。”
望着他那痛苦兼渴望的表情,天平不由笑道:“都怪我,本不该带你去看《荒江怨》,又哪承料当晚会碰到她呢。”景浩喃喃道:“这就是所谓缘分吧!”
天平在家乡给聂枫满月后的孩子找了个奶娘,这奶娘既干净又能干,聂枫很满意。天平借着跟奶娘闲聊的机会,在聂枫和景浩之间传递着信息。为了安全起见,天平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俩幽会。每次分手景浩都陷入祈盼的痛苦之中。
终于一次,景浩哀求道:“我们结婚吧,枫,我要娶你,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你!”
聂枫倚在他身边说:“我这人做朋友谁都喜欢,做妻子却未必是很合适的。”
景浩说:“你对所有的人可能都不合适,惟独对我合适。”
聂枫说:“我这人好玩,性喜动,不能受拘束。”景浩说:“这正是我喜欢的!”
“这些特点,一般男人都不喜欢,而且我喜欢享受,努力为自己创造各式各样的享受。”
“我也要尽我之所能为你创造。”
“一时半刻你受得了,时间长了你就受不了。”
“受得了受得了受得了。”
“时间长了你就会后悔的,景浩!”
“不会后悔不会后悔永不后悔!”
四目相对,聂枫直言:“我的缺点,不结婚你是感受不到的。”
“这些话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不想听。”景浩叹道:“我知道,你同张通宝分手不容易,他有权也有钱。”
“只可惜,他不像你这般爱我,所以在情感上我对他已没有一丝丝留恋,我很清楚,他其实巳经另有新欢,只是碍于情面,他不会先提出与我分手,既然你……这样,那就由我先提出来好了。”景浩愣了片刻,紧接着笑了。她说:“问题是孩子……”
“没问题,孩子我们要了,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他应答极爽快。
她伸出纤长的五指梳理着他浓密的黑发说:“你呀,自己就是一个大孩子。”
她又问:“万一张通宝不同意离婚又怎么办?”景浩一愣:“他不是另有新欢么,何必缠你!”
“说不准的,不能不提防他可能要横。”
“那我们就私奔。”
“最好不要走这一步,我还是喜欢这个城市的生活,再说外面的世界固然阔大,我们却举目无亲。”景浩痛苦道:“那又怎么办呢?”聂枫说:“让我跟他谈谈看吧,但愿能顺利。”
景浩催她明日就谈。聂枫说他性子太急,他说时间拖久了保不准会得神经病的。分别的时候,景浩又把聂枫一把拽回,紧紧地拥抱在怀,生怕此一去而再难见似的。聂枫轻声说:“实在不行,就只有应了你,私奔,你这个痴子呀!”景浩双泪沾睫。
张通宝的态度,有些出乎聂枫的预料之外。那天吃饭的时候,聂枫平静地问他:“你晚上如果没有要紧事的话,我想同你谈一谈,行不行?”
张通宝说“你不用拐弯抹角,想离婚是不是?”
“既然你明白了,我也就不多说了。”聂枫想,他其实早有思想准备的,说不定早盼我说这句话呢。“是和那个小画家吗?”
聂枫承受不了他那多少有些轻蔑的口吻,冷淡道:“这以后的事,你管不了,正如同我也管不了你一样。”
“好,管不了我就不管。”张通宝微微一哂。“既然你提出离婚,我来提几个并不过分的条件,一是孩子归我;二是由我登报声明离婚;三是由你交一万块钱离婚损失费给我。”
聂枫气道:“这三个条件,我一个也不能接受,孩子归我,我不要你一分钱抚养费;离婚是双方同意的事,不存在谁给谁损失费的问题;登报声明你固然可以登,但不许有贬损我的文字。”
“孩子决不给你,给一万块钱我可以不做登报声明,如果少一个子我一定登,内容措辞你管不着!”张通宝的语气很决断。聂枫叫道:“你若登了贬损我的言辞,我一定反击!”
“你要知道,你是演员,名声对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再说,本埠报馆,还没有哪一家想同警察局过不去的!”
聂枫咬牙道:“我怎么以前没看出你的这一份险毒来!”张通宝轻松地玩味道:“其实这都是你逼的。”聂枫心想,这桩事如不同意,就不知会拖成什么样子,真正拖苦的是她和景浩。于是说:“小武是我俩的骨肉,你一定要就必须把他带好,不许受后娘欺侮;带不好我随时会要回来。我一个也不会给你,我也没有钱,更不用说一万块!”
“那我可就要登报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聂枫再次来到景浩宿舍,刚说了一句:“小武属于他了”,就已泪流满目。
景浩拥着她在床边坐下,听着她哽咽和诉说,心中十分不忍,宽慰道:“不出一年,我俩再创造出一个来,是男儿跟我学画画,是女儿跟你学演戏,怎样?”
聂枫止住了哽咽,摇头道:“不要也罢,有了孩子总不免牵肠挂肚的。”
景浩说:“以后生与不生,都依你。”
“不生了,”她的态度好似很坚决,“再生,我的体形一变,就要显老了。”
“你哪里有权说一个老,字,在我眼里,你是永远不会老的。”
“你愿你二三十年后,再说这句话。”她的神态有点儿悲凉。这在景浩看来,却更有一种撩人的气质。他让她就那样坐着,端着一块画板,站在那里勾勒起来。“一个痴子。”她说。“一对痴子。”他说。
没等他画完,她就扑了过来,她说她忍受不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他扔了画板,迎接着她的热吻和拥抱……
正当两人傭倦地细语时,猛然响起敲门声。景浩一听就知道是天平。
收拾了片刻去开门,天平玩笑道:“把哪个女人锁……”猝然看见聂楓,吞下半句话。
他身后站着张倩,景浩发现张倩的眼神倏然一暗。待得四个人都坐下来时,局促之中,两个女人间还多一份尴尬。张倩喜欢景浩,景浩全给聂枫说过。聂枫说,你何不就娶了她,她跟了你,你会有个平静和满的小家庭。景浩说,张倩没哪不好,可以做永远的朋友,却总没有娶她的愿望,或许正是想逃避那一份平静与和满罢。聂讽说,那你以后有苦头吃的。他说,如果是命中注定,那就无法逃避,即使做不到甘之如饴,也会从容对待。
此刻,虽然聂枫每每牵起话头,张倩那边却是时时中断,弄得轰枫淡了趣味,就起身告辞。张倩只到门口,并不外送,景浩和天平送聂枫到校外返回,天平说:“真不凑巧,冤家路窄。”
景浩问,是不是把他同聂枫的关系都说与张倩听了。天平说透露过一些,不然她天天要来,看你景浩还怎样同心上人缠绵。景浩点头:“跟她说了好,我是多么不想伤害她呀。”天平摇头:“这是没法不伤害的事。”景浩认真说,这里不能用伤害这个词,充其量只能用伤心。“伤害也好,伤心也罢,总之你老兄艳福不浅,你去同她谈谈吧!”说完,天平掉头朝大门外去了。
景浩望着天平的背影,蓦然觉得天平今日的语气神态都不大对,连想到好几次都是天平陪张倩来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不是天平对张倩有意呢?如果这样,正是自己与张倩从容解脱之机。回到小屋来,张倩似乎已经平静,正看他的画稿。景浩问:“阿倩,泰勒一家对你怎么样?”
“还可以。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要寻一份不受男人干扰的好事做,总是难的。”
景浩察言观色问:“你不是说泰勒不错吗?”
“他是不错,有绅士风度,对音乐也很通晓。但是两人呆在一间屋里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担心,尤其不敢看他那双很深的眼睛。”
“他可问过你有没有朋友?”
“他从来不问我这些。”
“那你就主动跟他说,有。”
“可我没有呀。”她眼睛里蓦然闪亮起来。
“阿倩,我觉得天平不错。”景浩温情地说。“是不错。”她的眼光倏然暗了。“我觉得他也很爱你……”
“不要说这个。”
景浩不语了。
她忽然问:“你相信你同她会幸福?”
景浩没料她会如此直接,默了片刻说:“我会尽力给她带去幸福。”
“那么你呢,你难道不考虑谁给你带来幸福?”张倩有点咄础逼人。
“阿倩,我生命中需要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包含幸福也可能包含痛苦,这种激情我发现只有她才能给我。所以,不仅是她需要我,而且更是我需要她。”
“好吧,既然你如此自信,我祝你们幸福。”张倩的话语里含着调伲的意味。
送张倩出门,景浩抬眼见聂枫站在一棵冬青树下,神色灰颓。景浩忙迎上去问怎么了。聂枫说,张通宝把门锁换掉了,她回不去了,若是回父母家,一时也没法解释,所以仍旧上他这来了。要么上朋友家去住也可以。景浩哪里肯放她,挽她回到屋里。一夜温情,决定了第二日去江西九江。次日上午,景浩上车站买票,聂枫趁张通宝上班的空子,叫奶娘开门,收拾了一皮箱的日常用物,吻吻熟睡中孩子,凄然而别。她走后,奶娘也含泪打点行装。因张通宝交待过,若是给聂枫开了门,就立即将她解雇。一路风尘到九江。
景浩的父母见儿子带回来这么一个高雅漂亮的媳妇,都很高兴,只怨他为什么不提前打封信回家,以便到码头迎接。
坐在马桶上聂枫没法解手,街巷上的公用厕所脏得令她恶心欲吐。聂枫问,这么大的住宅里怎么不弄个卫生间呢?景浩父亲立即着工匠在后院里砌了一个。
景浩对她说,“爸妈都很喜欢你呢?多住些时候如何?”聂讽来到小城,也觉得处处新鲜。景浩无意中透露出她演过电影,来一睹演员风采的人就更多。一家私立小学的校长请她去讲课,当地演员剧团聘她去客串。繁杂之余,聂枫心中的荣耀感和自矜感也得到了满足。
聂枫尤对庐山留连忘返,两人在山上一住便是半个月。这时候尽管是深冬节气,然而放眼依然是一派悦目的深绿。那日下了一夜的雪,清晨出门,但见山壑间银装素裹,气象万千。聂枫甩了手套,摘了口罩,忘情地张开双臂奔跑呼喊。那喊声在冷寂而博大的山谷里清脆地翻滚晶莹地跳跃,惊动了万年松上的积雪,飘飘洒洒,缓缓如羽,轻柔似云,剔透像玉。
两人在山上盘桓,兴味正浓,家中却派人传话来叫景浩从速下山。两人不知出了何事,大雪封山,车辆不行,只得雇了几个轿夫抬下山来。
原来是艺专蔡先生寄来厚厚一函,被家人拆看了。随信附来沪上一张大报,载有张通宝的离婚声明,对聂枫诋毁得十分厉害,连带也诋毁了景浩。蔡先生的信中,对景浩的做法也很愠恼。
景浩一字也未向父母吐露过这些事,猝然被揭了底子,而且又被张通宝丑化得不成样子,景浩父亲顿时觉得颜面尽失,气得挥杖打碎了一只半人多高的古窑花瓶。父亲责令他立即与聂枫分手。景浩说,他与她已经生死不渝父亲说他鬼迷心窍。景浩说,惟对她魂牵梦绕,毫无办法。父亲举杖欲打,母亲扑过来紧紧护着儿子。景浩父亲的态度伤害了聂枫的自尊,加之张通宝在报上的诋毁,更令她怒火中烧,于是决不肯在九江多呆,当即就要往回去。景浩只得差人去买来船票。
这日傍晚,客船缓缓离开码头,父亲自然不会来送,景浩看着渐远渐小的母亲,不由得泪湿双眼。
回到上海,两人索性就快捷而简单地结了婚。聂枫企望登一则结婚启事对张通宝有所反击,尽管措辞绵里藏针,大小报馆居然都以体例不合为借口婉然谢绝。
聂枫想起《新闻报》的吴志安曾采访过她,于是求助于他。吴志安风华正茂,意气方刚,看了张通宝的那则声明,很为聂枫打抱不平,无奈用尽心机,这则结婚启事也还是没有登出去。
一直到聂枫与景浩结婚那日,吴志安才在本报写了篇杂文《读一则离婚声明》。文章虽未指名,对张通宝却挖苦得十分厉害。警察局寻隙上门,吴志安交游广泛,找得要人从中斡旋,方才摆脱滋扰和危险。
聂枫对吴志安的鼎力相助,自然心存感激。从此吴志安成了她家的常客。
新婚后,在虹湾路租了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经聂枫精心布置,十分髙雅舒适。
房租不低,日常生活的开销也大。聂枫不肯在生活上委屈了自己,但同她的过去相比,她的生活水准还是降了不少,穿戴上尤其不能高攀。那次在商场门口,碰到她民立中学的老同学,一身的珠光宝气,小轿车接送,说起她丈夫在东亚银行做高级职员时,满脸的炫耀。
待她乘车走后,聂枫鄙夷道:“当年班上学习最差的就数她,读初三的时候还不会解二元一次方程,和8分不清,男生给她取了个绰号叫038”。她哧哧一笑,放低声告诉景浩,这是“大傻屄”的拼音缩写。
聂枫父母尽管对张通宝不大满意,对无权无势的景浩却更加反感。所以从九江返回以后,景浩一次也没上她家去过。她家自然也不肯再接济违悖时尚的女儿,经济上就自然捉襟见肘了。
所幸这时艺专改成了艺术大学,蔡先生做了系主任,破格任命景浩为讲师,月薪较先前翻了一倍多。